王石的擔當與奮進
胡舒立
王石以他2000年以來的經歷成書,囑我作序。我與王石并不相熟,不過,其人與其治下的萬科,確是我多年的關注對象。此次有機會完整閱讀了他13年來的文札,我了解到不少新聞事件的臺前幕后、來龍去脈,分享了他的企業管理思想,還有他對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問題的思考。從文中看,這是一位有擔當的、奮進的企業家的自白。
王石是中國最大房地產企業的掌門人,首先是位企業家。在本書文章中,我格外喜讀最后幾節,這是作者書中所思所想的高度濃縮與總結。文中坦言:“今天,中國企業家就面臨一些困惑和迷茫,面臨社會的曲解和丑化。……我們不必抱怨,也不要消極對待中國社會的不確定性。企業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冒險精神,在不確定情況下,才更需要企業家。我們贏得了財富,我們積累了經驗,這個時候不該逃避。”“企業家向這個社會輸出的正能量,是現代的管理制度、組織機構、溝通技巧。……企業家不僅僅為社會提供就業與財富,企業家精神更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這正是作者的自我期許與定位。“不抱怨”尤其難能可貴。后人不會對這一代企業家受到多少羈絆感興趣,只會對面對種種約束他們做了什么努力、取得了什么突破感興趣。在《建筑補習班》一文中,作者說,“在我的閱讀體驗中,不管是經典的著作,還是日常的紙媒,房地產總是和‘貪婪’、‘暴利’、‘驅逐市民’、‘破壞城市記憶’聯系在一起,這與我的自我期許相去甚遠。”多年來,他不懈地用個人和企業的行動與這種“刻板印象”相抗爭。他向往的是榮德生、張謇那樣的氣度。無論他最終能達到什么高度,這樣的追求本身即有理由贏得鼓勵和認可。
也許是不經意,書中通過他人之口,對王石做出了總結和品評。有人將他的人生經歷比喻成3座山峰:創立萬科、攀登珠峰和哈佛游學。在李連杰邀請他出任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執行理事長時,提出了幾項要件:是一個好的管理者;口碑好,正直;有公眾性,有影響力;熱心公益,認真做事;擅長時間管理,能夠為壹基金拿出時間。勇于接納壹基金的深圳地方官員則認為王石是一個有良知的企業家,為了社會公益、為了一些正確的事,愿意承擔風險和責任。在我看來,更簡練的表述是王石自己的認知,董事會主席需要做3件事:第一,戰略;第二,用人;第三,擔當。而這個“擔當”容量極大。
擔當體現在把一家企業做精、做強。書中不乏篇章講述萬科的經營戰略,如何進軍各大城市,如何通過制度選賢任能,如何提出并身體力行住房產業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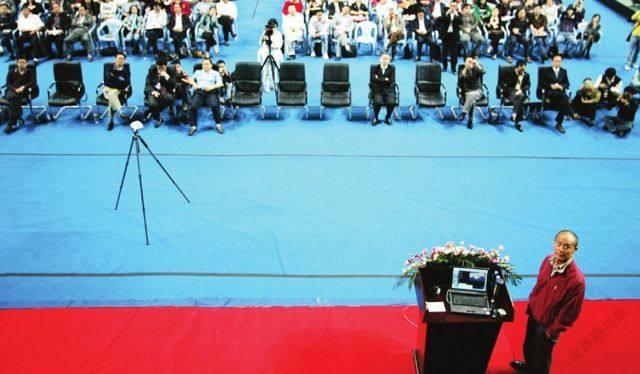
擔當尤其體現在危機時刻,所謂“疾風知勁草”。萬科的成長中,經歷了數不清的艱險,書中對中南巴士風波、武漢垃圾場事件和安信木地板事件,還有汶川地震中的“募捐門風波”,都做了生動的描述。王石說,“當負面新聞出現,一些公司是用掩蓋的方式解決問題。但可惜的是,他們一旦擁有了掩蓋的能力,就失去了其他能力。這不是萬科的做法,萬科需要的是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對客戶、媒體和自己都坦誠相待,就為企業確立了明確的標準與價值。”作為媒體人,我贊賞這種態度。只有這樣,“客戶是萬科存在的全部理由”,“衡量萬科成功與否的最重要的標準,是我們讓客戶滿意的程度”,這些萬科企業核心價值觀的組成部分才能得到真實、生動的展現。
擔當體現在作者熱心公共事務。這遠遠超越了狹義的公益事業,雖然作者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作者高度重視“阿拉善生態家園基金”(英文簡寫為“SEE”)的議事規則,顯然,有深意存焉。SEE上企業家對議事規則從開始不適應,到后來才接受和掌握,其間有爭執,有妥協,最后才有共識。作者說得好,“治沙能不能有結果?我覺得已經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過程體現了民主的氣氛和精神,這可能對社會進步的意義更大。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大自然荒漠的改造,更是對我們自己內心荒漠的改造。”
由此,我聯想到不久前關于企業家社會角色的論爭。表現形式或有不同,但是,在當今中國,哪一位優秀的企業家能做到悶聲發大財?他們不能不對中國向何處去有著自己的思考。
企業家自有其性格、氣質與行為方式。與創新與冒險相聯系的是好奇與學習,即作者自況“聽從好奇心,一往無前,永遠不滿足于現狀。”作者準確地把entrepreneurship理解為奮進,這比“企業家精神”之義更為本源。
他深信“學習是一種生活方式”。這一點,體現在他多年的日常工作中,如對日本建筑業的傾心學習,尤其體現在他的哈佛求學中。他作為“高齡學生”,放下老總身段,生活自理,謝絕應酬,潛心學習,一般很少能在凌晨3點前睡覺。這顯然需要強烈的求知欲作動力,堅強的意志力作約束。“登珠峰當然難,但沒有我想象的難。哈佛游學也難,比我想象的還要難”,確是甘苦自知。而從作者選的課程,如資本主義思想史、城市規劃與投資管理和新能源經濟政策,我們再次領略到作者的視野與志趣。
中國有心撰述的企業家不多,能文的企業家更少,此書言之有物、文筆曉暢、簡練生動,讀此書常有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之感。此書值得企業家同仁一讀,也為MBA教師與學生提供了許多難得案例,關心產業發展和中國改革的人士也會獲得不少啟發。讀者不需要同意作者的所有判斷或預測,如對于其2007年的“拐點論”。書名《大道當然》給人無限遐想,“作者之心未必然,讀者之心未必不然”,如何分解,讀者諸君讀后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