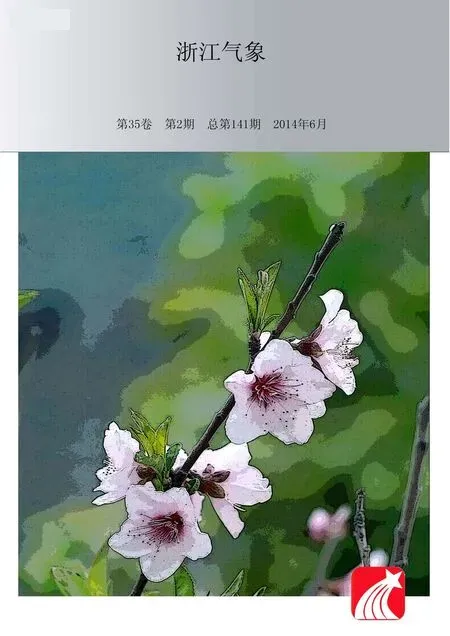高分辨率區域海-氣耦合模式:短期氣候預測新的春天
馬 浩 雷 媛 毛燕軍 張小偉
(浙江省氣候中心,浙江杭州310017)
0 引言
短期氣候預測是氣象部門開展的核心業務之一,它以月、季、年時間尺度上的氣象要素平均變化趨勢為預測對象,著重研究氣溫和降水的變化趨勢。短期氣候預測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是由于氣象災害預報的提前量與災害損失之間具有顯著的反比關系。對重大氣象災害而言,預報提前得越早,則采取的應對措施就會越充分,從而災損越小。與短期天氣預報相比,短期氣候預測具有較大的提前量,因此往往在氣象防災減災中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據國內外氣象部門統計,氣象災害平均每年導致的損失約占GDP的3% ~6%;短期氣候預測如果報準,可使受災損失減少1% ~2%,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1]。因此,對國民經濟生產各部門而言,短期氣候預測與短期天氣預報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當前,開展短期氣候預測主要有經驗統計、動力模式和動力統計相結合3種方法。經驗統計方法注重考察天氣氣候的相似性,通過尋找持續性較好的預報指標來進行氣候預測。當前,短期氣候預測中使用的統計方法主要有多元分析、時間序列分析、經驗正交函數(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EOF)分解、灰色系統、聚類分析等幾類,其中的逐步回歸、EOF分解、相似方法等是短期氣候預測中應用最廣、效果最好的方法[2]。動力模式預報始于20世紀70年代[3],近年來取得了蓬勃的發展。它以數值模式結果為依托,通過研究模式積分輸出的要素場和環流場來進行氣候預測。動力統計相結合是一種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方法,其核心是怎樣利用模式結果產生更為可信的預測結論。具體來說,動力統計結合法主要有模式輸出統計量(Model Output Statics,MOS)和完全預報(Perfect Prognosis,PP)兩種方法。MOS方法是利用模式回報資料與氣象要素建立統計模型,在此基礎上利用模式預報產品進行預測;PP方法是利用歷史資料與氣象要素建立統計模型,進而利用模式預報產品進行預測[3]。
盡管短期氣候預測方法眾多,然而目前來看,預測效果總體上并不盡如人意,“報不準”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我國實際業務中,降水的短期氣候預測水平僅保持在60% ~70%(采用國家氣候中心的實況解釋檢驗結果的準確率(PS)評分),長江流域降水的預測準確率僅達到50%以上[4],失敗的例子相當多(如 1999、2003 年等)[5]。這一現象是值得深思的。概括而言,短期氣候預測效果欠佳,既有問題本身的困難性,也有方法的問題。從機理上來說,我國處于東亞季風區,而基于模式預報的降水可預測性基本上局限在熱帶地區,熱帶外總體上是很難預測的,在東亞氣候區更是如此[6]。從方法上來說,經驗統計方法常常演變為單純的數學游戲,缺乏物理內涵的相關系數用得過多過濫,使預測失去了科學基礎;數值模式對地球氣候系統中的重要物理過程刻畫過于粗糙,使模擬結果時好時壞,導致預報員在模式結果的使用上游移不定、把握不足;沒有好的數值模式,動力統計結合法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也是動力統計結合法未必能取得良好預測效果的關鍵原因所在。面臨著如此之多的困難,我們不禁要問:“短期氣候預測的出路在哪里?未來的發展道路在何方?”
1 短期氣候預測的未來發展道路
關于短期氣候預測未來的發展道路,其實涉及的是以經驗統計方法為主還是以動力模式方法為主的問題,這是兩條不同的道路。為了闡述這一問題,我們首先來討論一下兩種方法各自的優缺點。
1.1 經驗統計方法
經驗統計方法最大的優勢在于其易操作性。目前,幾乎所有的統計方法都可以用計算機程序方便地實現,與動力模式方法相比,經驗統計方法容易上手,可以在短時間內作出預報結果,從而保證了短期氣候預測的時效性。同時,預報員通過自身的經驗對統計結果進行調整,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預報的準確性。因此,經驗統計方法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各級氣象部門進行短期氣候預測的主流方法。然而,該方法也存在很多問題。
首先,面對著具體的預測問題,我們并不知道哪些統計方法是真正有效的。在統計工具眾多的今天,在何種情境下應該采用何種方法?我們并無把握。各種方法似乎都有效果,又都沒有足夠的可信度,這正是短期氣候預測的困難之處。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取舍?這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其次,經驗統計方法的成敗取決于所選取預報指標的好壞。丑紀范院士指出,前蘇聯在開展長期天氣預報時,通過歷史資料分析找到了一些預報關系非常好的指標,可是應用于預報實踐效果不行;于是重新尋找預報指標,在實踐中預報效果仍然不好[7]。長期重復這一過程,預報水平就很難提高。為何在歷史資料分析中效果很好的指標卻無法應用于實際預報呢?這實質上反映了一個問題,歷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指示未來?一旦氣候系統中出現了以往從未發生過的氣候變異現象,歷史經驗分析就失去了作用。預報指標的可靠性與其所處的時間段密不可分,當氣候系統發生轉型或者突變、進入新的氣候階段,則預報指標的失靈在所難免。在全球變暖的背景下,一些原本非常牢固的統計關系紛紛“失效”,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鮮活例證。
第三,預報員的經驗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證預報的準確率?預報員的經驗是進行氣候預測的重要基石,然而客觀來說,預報員的經驗僅僅是局部經驗、而非全局經驗,即預報員往往僅對某些氣候異常現象有深入研究(這與預報員的知識結構和研究興趣有關)、而不可能對氣候系統的各種變異行為都有精深的把握,從而導致有時報得準、有時報得差。由于預報員的經驗并不總是能夠有效地修正統計結果,有時還可能使預報效果進一步惡化,因此,如何合理使用預報員的經驗,也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
最后,經驗統計方法的客觀化程度不高。經驗統計方法歸根結底是一種主觀方法,預報員的取舍和判斷在進行預測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人為訂正與人為修改實際上是預測中的重要環節,這種業務流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短期氣候預測的制作效率。
1.2 動力模式方法
動力模式方法是一種客觀化方法,它通過對描述大氣運動的方程組進行數值積分,以獲得未來時段的氣候狀況。簡潔性、直觀性和客觀性是動力模式方法的突出優點,同時,由于模式預報不受歷史經驗的制約,對于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特殊氣候現象,模式的預報能力往往優于經驗統計方法,這在短期氣候預測實踐中已經得到多次驗證。然而目前來看,動力模式方法的預報效果不夠理想,甚至弱于經驗統計方法的預報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如前所述,目前,短期氣候預測理論尚不成熟,而我國氣候又受到青藏高原、東亞季風、熱帶太平洋、熱帶印度洋和中高緯度大氣環流的綜合影響,氣候成因極其復雜和特殊[1],很多氣候現象形成的機理尚不清楚,從而給數值模擬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第二,模式動力框架的缺陷。我國由于受到青藏高原大地形的影響,因此,適用于中國的氣候預測模式應當突出青藏高原的作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國外大多數先進的氣候模式均未充分考慮青藏高原的影響,因此直接用來對中國氣候進行預測有著天然的缺陷。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和國家氣候中心研制的動力模式開發伊始即注重考慮青藏高原,從動力框架而言更適用于進行東亞和中國氣候的預測[1],有著較好的發展前景。
第三,模式性能的制約。模式方程組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客觀真實的物理世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模式的預測效果。在模式研究中,一個簡潔的判定模式性能的方法是“平均態法”,即模式模擬的氣候平均態與真實的氣候平均態之間存在多少偏差。如果模式連氣候平均態都模擬不好,則進行氣候預測只能是一種奢望。目前,就氣候模式的發展水平而言,幾乎所有的模式僅能“大致合理”地模擬出基本氣候態,區域偏差十分顯著,這是模式預測的一大瓶頸。此外,模式對氣候系統其它因子(如海洋、冰雪圈、生物圈等)的作用考慮不夠全面、分辨率過于粗糙、參數化方案不夠合理等也是預測效果不夠理想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經驗統計方法與動力模式方法各有優缺點,預報效果都不夠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走什么樣的道路呢?從長遠來看,如果以經驗統計方法為主,則預報員經驗的建立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隨著年代際氣候轉型的出現,經驗的“失效”也會發生,因此又會經歷新經驗的重建過程,因此經驗統計方法是一種經驗建立—經驗失效—經驗重建的循環往復過程,且因人而異,傳承性很差;如果以動力模式方法為主,盡管目前動力模式的預報效果并不理想,然而隨著模式框架的不斷改進、模式性能的不斷提高,模式預報效果也會得到穩定的提高,這種提高建立在牢固的物理基礎之上、且具有較強的繼承性和沿用性,在業務實踐中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國家氣候中心也認為短期氣候預測應當從以物理統計方法為主的階段逐步過渡到以動力數值方法為主的階段[8-9]。無疑,動力模式方法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將會成為未來短期氣候預測的主流方法。只要我們摒棄急功近利的思想、經得起時間的等待,動力模式方法一定會大有作為,為最終實現準確度較高的客觀化預測奠定堅實的基礎。下面,我們針對動力模式方法進一步展開論述,著重分析在各種數值模式中,什么樣的模式才真正切合短期氣候預測的業務需求?我們應該如何選擇?選擇的依據在哪里?
2 高分辨率區域海-氣耦合模式對于短期氣候預測的重要意義
2.1 為何要選擇海-氣耦合模式?
談到氣候模式,我們先要澄清一個問題,即什么叫氣候模式?在國外,習慣于把耦合模式(Coupled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CGCM)稱為氣候模式(Climate Model),其余的氣候分析和診斷模式一般統稱為大氣環流模式(Atmospheric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AGCM)。這種界定是十分科學的,即氣候模式應當是氣候系統模式(至少包括大氣和海洋兩個成員,更為完善的氣候模式還應當考慮冰雪圈、陸面過程、天文強迫和生物圈的作用),而不僅僅是單純的大氣環流模式。這是由于氣候變異往往受制于外強迫的作用,即氣候變異(特別是低頻變異)的原因來自于大氣圈之外[10],而不是來源于大氣環流自身,這就是為什么用AGCM來進行氣候預測效果往往不佳的重要原因。我們以海洋-大氣相互作用為例來簡要說明這個問題。在海洋-大氣相互作用中,海表溫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SST)變異是大氣環流調整的重要原因。在AGCM中,SST預先給定,之后在積分時段內保持不變,相當于用定常的海溫來強迫大氣環流;而在CGCM中,海洋和大氣之間通過通量交換發生相互作用,從而導致SST也隨時間發生變化。顯而易見,“變化的海洋”比“不變的海洋”更加接近物理真實,耦合模式中的各種動力學和熱力學過程更加符合實際,因此是進行短期氣候預測的理想選擇。正如王紹武[11]所指出的,開展氣候預測必須使用海-氣耦合模式。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可以先用AGCM進行預測;然而從長遠來看,真正可靠的預測必須借助于CGCM。事實上,在發達國家的短期氣候預測業務實踐中,海-氣耦合模式已經日益成為核心預測工具[12]。
2.2 為何要選擇區域模式?
相較于全球模式,區域模式有兩個突出的優點。第一,同等分辨率條件下,區域模式的運算效率比全球模式高。氣候預測對時效性的要求極高,如果模式運行緩慢,遲遲無法得到運算結果,則模式預測也就失去了意義。事實上,在當前各種全球海-氣耦合模式中,運行效率最高的是由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和美國阿拉貢國家實驗室聯合開發的快速海-氣耦合模式(Fast Ocean-Atmosphere Model,FOAM)[13],在 32 個CPU并行的情況下,FOAM的運算效率一般為24 h積分80 a。這是全球海-氣耦合模式中的一個特例,在FOAM之外的諸多模式運行效率遠不能與其相比。以舉世公認的優秀耦合模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地球物理流體動力學實驗室(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GFDL)開發的氣候模式(Climate Model)2.1版(CM2.1)[14]為例,同樣是 32 個 CPU 并行,CM2.1的運算效率一般為24 h積分10 a左右,如果將分辨率提高(GFDL已經研發出最新的高分辨率耦合模式CM2.4),則運算效率往往呈指數下降,CM2.4的運算效率僅為24 h積分幾個月。如果考慮到需要開展集合預報以保證模式預測結果的可靠性,則如果沒有大量CPU支持,借助全球模式開展集合預測將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從而使氣候預測的時效性得不到保障,難以滿足業務需求。與全球模式相比,在同樣的分辨率條件下,由于運算區域相對較小,區域模式的運算效率大大提高:在同樣的運算時間內,如果全球模式僅能達到低分辨率運算,區域模式卻有可能達到高分辨率運算,其優勢顯而易見。對具體的預測問題而言,氣象部門一般不需要對全球氣候作出預測,而僅僅關心某個區域內的氣候演變情況,在此意義上,區域模式已經足以滿足需要。
第二,相對于全球模式而言,區域模式的調整與改進顯得相對容易。這是由于,從物理上來說,全球模式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性,即某個區域內某個物理參數的微小調整可能導致遠程氣候出現顯著變化,這也為全球模式的物理歸因帶來了困難:如果某區域的氣候要素預測效果不好,應當如何采取措施來加以改進?在全球模式中,區域氣候要素的變化往往是由多個因子在不同時間尺度上發生相互作用而導致的,調整單因子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區域模擬效果的改進在全球模式中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也是氣候學界共同面臨的難題。舉例來說,當前大多數全球氣候模式對季風區降水的模擬效果很差[15-16],其原因極其復雜,盡管氣候學家針對這一問題開展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顯著的學術成果,然而究竟應當如何改進全球模式來提高模擬效果,我們仍然難以給出明確的回答。根本性的困難在于,季風降水是一個海洋-大氣耦合問題,而區域耦合問題的偏差往往來自于區域以外的多尺度相互作用。問題本身的復雜性以及模式框架和機理的復雜性使得模擬效果的改進殊為不易,往往花費了很大力氣卻收效甚微。然而,區域模式的物理歸因卻相對容易。對區域模式而言,邊界強迫至關重要。邊界條件的調整可以使區域模式性能獲得顯著的提高[17-18];換言之,如果在區域模式中,模擬區域內氣象要素預測效果不佳,往往可以規避復雜的物理歸因,通過邊界條件的調節來達到目的,這種“任爾幾處來,我只一處去”的處理思路為區域模式的調試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因此,考慮到短期氣候預測的業務需求,區域氣候模式是較為實用的一種選擇。
2.3 高分辨率的重要性
自從20世紀60年代末Manabe和Bryan[19]研發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海-氣耦合模式以來,氣候模式的發展已經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漫長歲月,模擬能力不斷增強,模擬效率日益提高。在氣候模式的發展歷程中,曾有很多學者指出:模式的改進應當注重內部動力學框架的完善,而不是一味提高分辨率。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我們斷然不能將模式分辨率置于無足輕重的位置。這是因為,如果模式分辨率長期沒有提高,我們就無法獲得區域氣候特征的精細結構,我們對區域氣候的認識也會長期停留在“霧里看花”的模糊水平。在全球變暖的氣候背景下,區域響應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沒有高分辨率的模擬結果,我們就無法知曉區域響應的具體型態和內在動力學過程,進而為區域氣候變化評估帶來巨大的障礙。從某種意義上說,模式分辨率的提高推動著氣候認識水平不斷提高。今天,幾乎所有的氣候模式研發人員都相信,就氣候模式本身而言,高分辨率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模式分辨率的提高不僅意味著網格加密,更重要的是模式內部次網格參數化方案的調整,大量原先適用于大尺度問題的參數化方案將進一步細化,從而使模擬能力得到提升。當模式分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則有可能將原先的大尺度海-氣耦合模式升級為中尺度海-氣耦合模式,從而展現出嶄新的模擬能力。世界氣象泰斗松野太郎(Taroh Matsuno)曾經指出,日本的地球模擬器將熱帶地區的水平分辨率提高到10 km×10 km,這一分辨率的誕生意味著熱帶氣象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氣候學的研究現狀來看,今天,氣候學家們已經認識到海洋中尺度渦旋和大氣中尺度渦旋在氣候系統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20-21],中尺度波動過程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氣候平均態、調制著氣候變率,而大尺度氣候模式無法刻畫中尺度過程,從而容易產生較大的氣候偏差。從大尺度模式走向中尺度模式,既是科學發展的必然,也是精細化氣候預測的需要。如果我們選擇大尺度海-氣耦合模式,則很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被時代淘汰;著眼于未來,我們必須順應時代潮流,選擇能夠刻畫和表達中尺度過程的高分辨率氣候模式,在更高的精度上進行短期氣候預測。
3 結語:現狀與前景——機遇與挑戰并存
盡管高分辨率區域海-氣耦合模式為短期氣候預測帶來了新的希望,然而由于這種模式對計算平臺的要求較高(至少需要幾百甚至上千個CPU),且研制過程中涉及的參數化方案和算法十分龐雜、模式運行的穩定性不易得到保證,目前在世界上成功的范例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得克薩斯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張平教授領銜的研究小組已經成功構建了高分辨率大西洋區域海-氣耦合模式[22],該模式在大西洋展現出驚人的模擬性能,不僅能夠較為準確地模擬出海溫等要素的空間分布(精度較大尺度模式大大提高),且對一系列區域尺度的海-氣相互作用現象(如臺風在海洋上的移動和發展)都有相當水平的模擬能力。
張平教授研究小組的成功讓學術界感到鼓舞,目前,中國海洋大學已經開始構建太平洋區域海-氣耦合模式,其它研究機構也開始著手構建印度洋區域海-氣耦合模式。從大尺度走向中小尺度,從全球走向區域,海-氣耦合模式展現出日益旺盛的生命力,在氣候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氣候動力學、氣候預測、氣候變化、氣候評估等,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于氣象部門特別是省級氣象部門而言,引進高分辨率區域海-氣耦合模式,是一件機遇與風險并存的事情。從機遇而言,此類模式針對性強,可以有效地提供區域尺度的高分辨率預測結果,對于精細化預測大有裨益;不僅如此,面對氣候預測并無靈丹妙藥的現狀,高分辨率區域模式的物理框架貼近客觀實際,可靠性較大尺度模式而言也有一定保證;此外,模式運行結果對于區域尺度的氣候分析也是良好的素材,可以有效地彌補觀測資料時間長度的不足。從風險而言,高分辨率模式對計算平臺的要求很高,運行和計算成本也很高;同時,由于高分辨率模式的物理架構復雜,模式的選擇、性能判別、移植與調試需要經歷相對較長的時間,我們能否經得起時間的等待?此外,邊界強迫是決定高分辨率模式預報性能的重要因素,如何處理邊界強迫考驗著我們的智慧和能力。當前,氣候預測的很多機理性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影響因子和預測對象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物理聯系?影響因子之間的相互作用對預測結果的不確定性影響如何?在氣候系統演變規律尚未得到完全揭示的前提下,邊界強迫的處理就顯得更加困難和復雜,需要我們結合海洋-大氣相互作用和氣候動力學的基本原理進行仔細甄別、推定和改進,在大量樣本實驗的基礎上得到最優化的邊界強迫方案。良好的機遇伴隨著較高的風險,但也蘊含著巨大的收益。對省級氣象部門而言,誰掌握了高分辨率區域海-氣耦合模式,誰就攻占了短期氣候預測的橋頭堡,誰就在新世紀的氣候預測創新中領先一步。跨越這一步,需要巨大的勇氣,需要非凡的魄力,更需要艱苦的探索。
高分辨率區域海-氣耦合模式研制成功為最終實現客觀化氣候預測帶來了信心和力量,它昭示著短期氣候預測新的春天即將到來,讓我們張開雙臂去迎接這個春天,做勇于開拓、與時俱進的氣象人,將氣候預測水平不斷推向前進。
[1] 丁一匯.我國短期氣候預測業務系統[J].氣象,2004,30(12):11-16.
[2] 楊舵.短期氣候預測方法綜述[J].新疆氣象,1996,19(5):1-6.
[3] 魏鳳英.我國短期氣候預測的物理基礎及其預測思路[J].應用氣象學報,2011,22(1):1-11.
[4] 趙振國.我國短期氣候預測的業務技術發展[J].山東氣象,2001,21(3):4-7.
[5] 王會軍,張穎,郎咸梅.論短期氣候預測的對象問題[J].氣候與環境研究,2010,15(3):225-228.
[6] 王會軍.試論短期氣候預測的不確定性[J].氣候與環境研究,1997,2(4):333-338.
[7] 丑紀范.短期氣候預測的現狀、問題與出路(一)[J].新疆氣象,2003,26(1):1-4.
[8] 趙振國,劉海波.我國短期氣候預測的業務技術發展[J].浙江氣象,2003,24(3):1-6.
[9] 李維京.現代氣候業務[M].北京:氣象出版社,2012:480.
[10] 周家斌.關于短期氣候預測的幾個問題[J].甘肅氣象,1998,16(4):1-13.
[11] 王紹武.短期氣候預測的可預報性與不確定性[J].地球科學進展,1998,13(1):8-14.
[12] Saha S,Moorthi S,Pan H-L,et al.The NCEP climate forecast system reanalysis[J].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2010,91(8):1015-1057.
[13] Jacob R.Low frequency variability in a simulated atmosphere-ocean system[D].Ph.D.dissertation of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a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Madison,USA,1997:155.
[14] Delworth T L,Broccoli A J,Rosati A,et al.GFDL's CM2 global coupled climate models.Part I:Formulation and simulation characteristics[J].Journal of Climate,2006,19(5):643-674.
[15] Wang B,Kang I-S,Lee J-Y.Ensemble simulation of Asian-Australian monsoon variability by 11 GCMs[J].Journal of Climate,2004,17(4):803-818.
[16] 張莉,丁一匯,孫穎.全球海氣耦合模式對東亞季風降水模擬的檢驗[J].大氣科學,2008,32(2):261-276.
[17] Lynch A H,Cullather R I.An investigation of boundaryforcing sensitivities in a regional climate model[J].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Atmospheres,2000,105(D21):26603-26617.
[18] K?ltzow M A ?,Iversen T,Haugen JE.The importance of lateral boundaries,surface forcing and choice of domain size for dynamical downscaling of global climate simulations[J].Atmosphere,2011,2(2):67-95.
[19] Manabe S,Bryan K.Climate calculations with a combined ocean-atmosphere model[J].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1969,26(4):786-789.
[20] Seo H,Jochum M,Murtugudde R,et al.Effect of ocean mesoscale variability on the mean state of tropical Atlantic climate[J].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2006,33,L09606,doi:10.1029/2005GL025651.
[21] Kug J-S,Choi D-H,Jin F-F,et al.Role of synoptic eddy feedback on polar climate responses to the anthropogenic forcing[J].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2010,37,L14704,doi:10.1029/2010GL043673.
[22] Patricola C M,Li M K,Xu Z,et al.An investigation of tropical Atlantic bias in a high-resolution coupled regional climate model[J].Climate Dynamics,2012,39(9-10):2443-2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