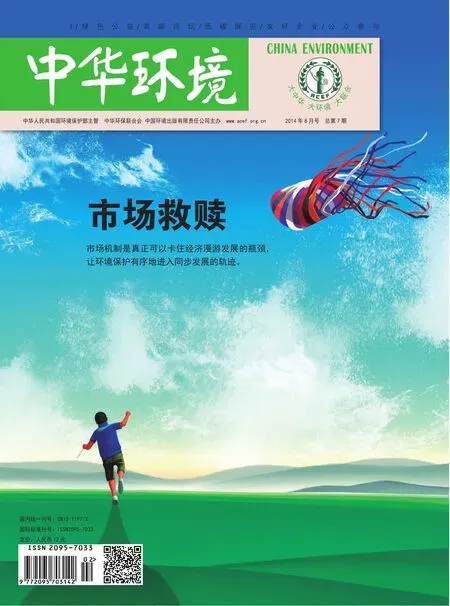環保經濟的熵定義
環保經濟的熵定義
費米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參加一個全國性的環保會議,會上一個專家建議大家都去讀一讀舒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沒多久我讀到了這本書,感覺這里頭有西方的陰謀。我們的改革開放才開始,四化建設剛起頭,祖國城鄉馬達轟鳴濃煙滾滾,鄉鎮企業四小工業方興未艾,我們的好日子這才要開始,而西方的經濟學家卻在那里聒噪什么小的是好的,企圖讓我們在小農經濟格局里徘徊,這是萬萬不能答應的。與此同時,我也讀了同樣來自于西方的《環境經濟學》,看了一張張邊際曲線,一個個數學模型,于是就更有把握了:除了多了一些環保詞匯外,理論和方法跟傳統經濟學沒什么兩樣,這更印證了舒馬赫的說法很不專業,沒有曲線和模型,基本屬于信口開河。
不得不說人是有差別的,多年后地產大鱷潘石屹讀到舒馬赫的書后無比激動,他從書中讀出了圣雄甘地的影子;又過數年潘總再讀此書,境界再度提升,他為再版的舒馬赫作序道:“在美國發生的災難性的9·11事件,是西方工業化發展帶來的仇恨與城市建設中追求高大、標志性兩條道路相交帶來的結果。而這兩條道路的指導思想與《小的是美好的》背道而馳。如果我們的發展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像9·11這樣的悲劇也許還會重演。”潘總的意思,如果美國都是潘總家鄉一樣的土坯房,或者像陜北的窯洞,恐怖分子就不會去撞紐約和五角大樓。按潘總的意思進一步延伸,他在建外的SOHO開工前是有先見之明的:決不能蓋得比紐約的雙子塔高。當然,作序歸作序,蓋房歸蓋房,潘總后來很多房子蓋得都很高大很標志性,或者說他在追求高大和標志性。
還得說說人的差別,我自忖沒有人家那么高大上,也沒有資本去開曼群島注冊地產公司,再讀了潘石屹序版的舒馬赫,環顧霧霾的天空和污染的大地,不禁為環境經濟研究和運用的嚴重缺失和滯后感到悲觀。我感覺能做決策的人基本都讀凱恩斯而棄舒馬赫于不顧,工科出身的人大都比較迷信分析曲線和數學模型。然而即便是我這樣一個半吊子理科出來的人,也想提醒他們注意一下理論的完整性和學科的均衡性:物理學的熱力學部分有個熵定律,說的是在一個封閉系統中,分子的熱運動最終將歸于停頓,也就是熱寂。有人或許會質疑:熱力學跟經濟學有什么關系呢?當然,你從傳統經濟學的表面是看不出這種關系的,不過有人看出來了,比如羅馬俱樂部的一批人,還有就是舒馬赫:“最大的那部分資本是由自然界而不是人類所提供的,而我們竟然不曾認識到這一點。這較大部分的資本正以令人擔憂的速度在消耗,因此,篤信并奉行生產的問題已經解決這一信念,乃是一種荒謬且自食惡果的錯誤。”
全部的傳統經濟學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除了人力生產和開采出來的生產資料之外,其余的一切自然資源都是免費的,并且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幸,這個觀點現在已經證實是非常錯誤的,在好多人驚呼水資源枯竭、土壤嚴重污染的時候,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已經在考慮給陽光標價出售,不得不說這些長官的意識非常超前和充滿喜感。同樣在上世紀的80年代末,我受國家環保總局委托為央視寫中水技術科普片腳本,就已經感覺到了即便是較低的環保標準,中水成本也已很高,更遑論目前在運轉的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廠。依照我們目前的國情,這部分成本估計不在GDP計算之列,即便是有,那也是大大低估了。而這一塊,經濟學沒有作任何重大的基礎改動,只要凱恩斯主義還在盛行,環境經濟學就一直會被邊緣化。
目前有關部門在考慮用經濟手段來制約環境問題,并呼吁大力發展環境經濟學的研究與建立。這方面不是沒有過嘗試,當初綠色GDP的提出,就是為給脫韁的GDP至上勢頭套上籠頭。只不過,如此一來很多經濟學家勢必得補課甚至回爐,再要憑老本在經濟學界混恐怕不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