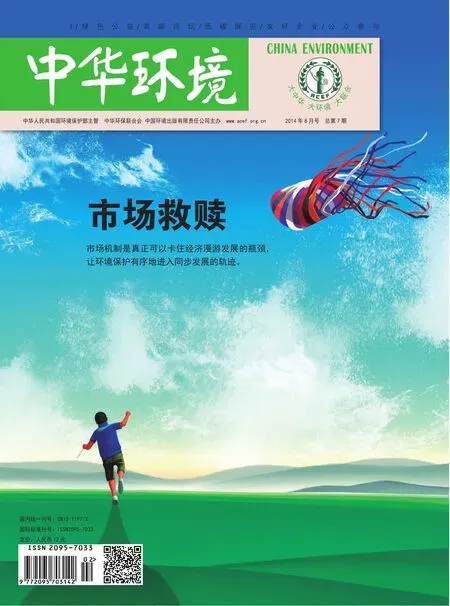重罰之下為何頻現“勇夫”?
閆海超
重罰之下為何頻現“勇夫”?
閆海超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骯臟的東西。”這句話,套用在剛剛認領了一張4.1億元巨額罰單的19家企業身上,恐怕再合適不過了。尤其是當我們把這些上榜企業的身家背景一一悉數攤開來看的時候,你會發現,包括五大電力集團華能、國電、華電、大唐和中電投在內的19家企業幾乎清一色的都是大塊頭的央企國企,這些本該在環保領域起帶頭作用的排頭兵,往往卻翹起了二郎腿當起了大佬,在環境形勢嚴峻的當口不免成就了一番笑話。
4.1億元,被稱為環境保護部開出的史上最大罰單,起因則是這19家企業因脫硫設施存在突出問題,被罰脫硫電價款或追繳排污費。
要知道,4.1億元只是一個合計數字。按照19家企業來核算的話,平均每家企業僅承擔2000余萬元,而這對于這些資金雄厚且年收入大多在數百億元乃至數千億元的行業巨頭來講,區區2000萬元罰款,顯然只是九牛一毛。
現實生活中的環保罰單并非鮮見,然而卻難以打破“污染企業不斷交錢,交錢之后繼續污染”的環保怪圈。事實上,涉案中的一些企業也并非首次遭罰。早在去年5月份,五大電力集團就曾因脫硫問題被公開處罰過,卻沒有達到預期的懲戒效果,依然是屢教不改,從中足以看出這些企業對罰款的不以為然。
那么,重壓之下,想要練就出這樣一份淡定自若的功力,大佬們靠的又是什么?
當然,“毛多”不怕拔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大佬們能夠我行我素的另一原因恐怕還是要倚重這獨特的體制:不管環保部門開出的罰單有多大,都可以由單位照單全收,左兜進右兜出,都是國家的錢,影響不到個人一分錢。
如此一來,這些企業便習慣了不按規矩出牌,只要環保成本一“節約”,經濟效益一準能變相提高,負責人就可以依據效益規定獲取更多的工資和獎金;一旦出了事,被部門逮個正著,責任也是全由單位給扛著,個人為此付出的成本僅為零。
所以說,這樁對他們而言只賺不賠的買賣,誰不想從中撈上一筆?
如此看來,這種只靠經濟手段的“環保罰單”,無法對“不差錢”的企業達到預期的懲罰目的。
治亂需用重典。環境保護部此次開出的史上最大罰單,無論對于涉罰企業,還是其他企業顯然都有足夠的威懾力,彰顯出對污染行為嚴懲不貸的態度,對于提升社會治污信心,也可以起到強心劑的作用。
但是,通過結果反饋來看,效果并不理想。當下有人提出,在國有企業中推行“環保罰單”追償制度,即當國有企業收到環保罰單后,監管部門應介入調查,對屬于故意而為的,比如技術上明明可以達標卻不去做,或降低標準、數據造假等,必須讓負責人承擔一定數額的罰款。
除此之外,還應給予其負責人相應的行政處分,甚至亮出“紅牌”,采取降職、免職處理,只有讓他們真正感受到切膚之痛,才能喚醒他們對環保的重視,而不再以一副不以為然的態度自居。
比照發達國家的治理經驗,重罰當然是一個重要方面,更關鍵的是,要讓違法者付出更多的道德和法律代價,并因此而寸步難行,面臨生死考驗。
億元罰單的背后,一方面暴露的是涉事企業的不負責,另一方面還暴露出了當前環保工作面臨的困境:監管責任的尺度過寬以及“對單位不對個人”的環保法規處罰理念,這是最讓環境執法人員頭疼的硬釘子。
加強環境保護,轉變發展方式,必須形成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雙重約束”,讓“最大環保罰單”不僅僅由相關的污染企業來領取,還得讓那些環境違法的決策者來領取。
今年4月,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獲得通過并將于明年施行,根據法律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新環保法中有關刑事責任的規定,亟待相關法規或司法解釋加以說明,指導實踐。其中,如果規定偽造監測數據、毀壞環保設施等不法行為的當事人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其震懾作用相信要遠大于這億元罰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