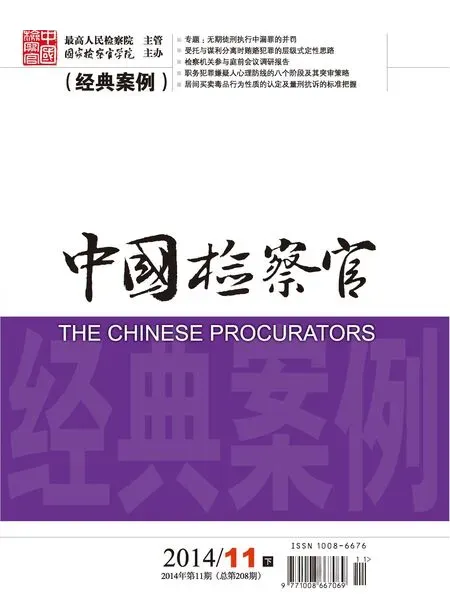取保候審期間發現余罪逃跑又投案的認定
文◎鄭敏
取保候審期間發現余罪逃跑又投案的認定
文◎鄭敏*
本文案例啟示: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強制措施針對的是人,不是罪行,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審期間逃跑后又投案的,既違反取保候審的規定,也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自首成立條件,不能認定為自首。
[基本案情]2011年10月10日,孫某某伙同劉某某等人受雇在寧波市B區故意傷害徐某致其輕傷,同日,B區警方對該案立案。同年12月2日,孫某某又伙同劉某某等人在寧波市Y區非法拘禁邱某。次日,Y區警方對孫某某等人非法拘禁邱某一案立案,同日對其刑事拘留,同月31日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2012年6月3日,徐某向B區警方反映將其打傷的有孫某某、劉某某等四人,并提供了孫某某等人的手機號碼。B區警方經調查發現孫某某因非法拘禁被Y區警方取保候審,便請Y區警方協查此人。6月4日,Y區警方到孫某某暫住地找孫,孫因事先得到風聲,得知在B區故意傷害一事已被發現,便溜走并逃到外地。同月11日,劉某某被B區警方抓獲歸案,其交代了伙同孫某某傷害徐某的事實。同月19日,B區警方決定對孫某某刑拘,并列為網上逃犯。Y區警方沒收其1萬元保證金后,于同年7月9日將孫某某非法拘禁一案移交給B區警方。之后,其同案犯陸續被判決。2013年11月3日,孫某某到B區公安分局投案,供述了故意傷害和非法拘禁的犯罪事實。
一、司法實務分歧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能否認定孫某某具有自首情節。對此,司法實務中主要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應認定孫某某具有自首情節,且適用于非法拘禁和故意傷害二個罪,主要理由是孫某某在取保候審期間逃跑,在被通緝期間向警方投案,符合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的自首成立條件,全案應定自首。第二種意見認為,應認定孫某某故意傷害罪具有自首情節,主要理由是孫某某系因非法拘禁被取保候審,但其脫保后在被通緝期間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了伙同他人故意傷害的犯罪事實,對其故意傷害犯罪可視作自首。第三種意見認為,不能認定孫某某具有自首情節,主要理由是其在取保候審期間逃跑,既違反了取保候審的規定,又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自首成立的條件,如認定其具有自首情節的話,是變相鼓勵犯罪分子在取保候審期間故意脫保以換取自首。
二、法理評析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能否認定孫某某具有自首情節,必須考量其行為是否符合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自首成立的條件。《刑法》第67條第1款對自首所作的定義是:“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條對“自動投案”作了明確界定:“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可見,適用《刑法》第67條第1款的前提條件是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孫某某投案時,其本人及其所實施的非法拘禁和故意傷害的犯罪事實均已被發覺,并且已因非法拘禁一案被采取強制措施,受到過警方的多次訊問,故適用上述條款的前提條件已不存在。那么其若要成立自首,必須符合《刑法》第67條第2款的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孫某某投案時的身份應屬于“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如實供述的必須是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但他前往B區公安分局投案時,交代的故意傷害事實是已被警方掌握的,同案犯也早已指認其系共犯,所以對他也不能適用該款的規定。綜上,其行為不符合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自首成立的條件,不應認定其具有自首情節。
持第一種意見的人認為,孫某某投案時,取保候審期限已過,其已無任何強制措施在身,所以應對其適用《刑法》第67條第1款的規定。那么按照這種觀點,就會得出“逃得越久越劃算”的結論,一旦逃了,就算想回來投案,也要等到一年的取保候審期限過了再回,否則就不能認定為自首,這樣的結論顯然是荒謬的。何況,因其脫保潛逃,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已無法繼續執行,警方才決定對其刑事拘留并上網通緝。《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59條規定:“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變更為拘留、逮捕的,對原強制措施不再辦理解除法律手續。”所以孫某某投案時并不是沒有任何強制措施在身,而是有刑拘的強制措施,其身份還是屬于“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持第一種意見的人還將孫某某與犯罪后被上網通緝、追捕的犯罪嫌疑人相提并論,認為其是在被通緝過程中主動投案的。筆者認為,雖然《解釋》第1條規定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但這應是指犯罪后從未到案也從未被采取過強制措施,取保候審期間脫保潛逃與《解釋》規定的“犯罪后逃跑”是有本質區別的。被采取強制措施后逃跑然后再投案的,相對于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而言,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但對新犯之罪仍能成立自動投案。例如,甲犯搶劫罪后被逮捕,脫逃后又投案的,只成立脫逃罪的自動投案,不成立搶劫罪的自動投案。又如,乙犯盜竊罪被取保候審,逃往外地時又犯搶劫罪,然后向司法機關投案,只成立搶劫罪的自動投案,不成立盜竊罪的自動投案。
持第二種意見的人認為,警方是因非法拘禁一事對孫某某采取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沒有對其故意傷害一事采取強制措施,所以其在故意傷害一案中應屬于“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同樣是錯誤的,因為強制措施針對的是人,而不是罪行,對同一犯罪嫌疑人,不能因其有多起犯罪事實而對其重復采取同種強制措施或分別采取不同的強制措施。
即便孫某某未脫保,在警方已掌握其故意傷害的犯罪事實但尚未就該事實對其進行訊問之前,其主動向警方交代余罪,也不符合《刑法》第67條第2款規定的“以自首論”的要件,那么將其脫保長達近一年半之后才向警方交代余罪的行為認定為自首,無論法理上還是情理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有人將取保候審后逃跑再投案與交通肇事后逃逸又投案相提并論,但交通肇事罪的這種自首是以法定較重刑為基準,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也有人提出,孫某某的投案在客觀上節約了司法資源,應當將這種行為認定為自首。從表面上看,其投案貌似節約了司法資源,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不能無視孫某某是警方已抓獲歸案的犯罪嫌疑人且已被采取了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這一事實,其必須遵守取保候審的規定。就算其沒有未交代的漏罪,在取保候審期間逃跑,也違反了取保候審的規定,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應當沒收其保證金,區別情形,重新交納保證金或者監視居住、予以逮捕。如果他不逃跑的話,警方根本就不需要為將他重新抓獲歸案而付出額外的精力;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本可以將他和同案犯一起審查起訴和審判,而不需要因其脫保而分案。因此,從孫某某脫逃的那一刻起,司法資源被其浪費的后果已客觀存在,之后投案所節約的司法資源與之前已被其浪費的司法資源是不能相抵的。并且如果將這種情形認定為自首,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鼓勵已被取保候審但苦于沒有自首情節的犯罪嫌疑人脫保潛逃再投案以換取自首情節,這必定會造成司法秩序的嚴重混亂和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與自首制度設立的初衷是相違背的,而且對被羈押脫逃機會極少的犯罪嫌疑人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浙江省寧波市人民檢察院[31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