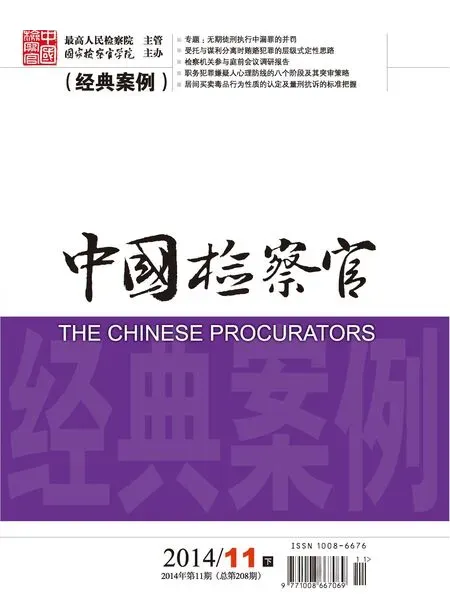論共犯中騙搶手段交織的案件定性
文◎徐劍鋒萬善德
論共犯中騙搶手段交織的案件定性
文◎徐劍鋒*萬善德**
本文案例啟示:詐騙、搶奪行為手段交織的共同犯罪案件的定性從尋找引致法益侵害緊迫性危險的行為是較為有效的途徑,但同時也不能忽略共同犯罪、因果關系、犯罪停止形態等方面的探討,以及被害人主觀認知因素在案件定性量刑上的意義。
在司法實踐中,大量侵財案件的作案手段是通過“詐騙”、“搶奪”手段相互交織、配合來實現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不法目的。既然實現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手段既有“詐騙”又有“搶奪”,那么,就有可能以詐騙罪或搶奪罪入罪。加之共同犯罪情形,這類案件的定性更是艱難。此類案件的處理若不能透過現象抓本質,鎖定影響定罪的實行行為,必然會導致司法實踐中同案不同判的結果,進而影響司法審判的公正性、權威性。本文以案例為基礎,從犯罪行為人和被害人兩大維度為切入點,分析、探討此類案件的定性問題。
[基本案情]被告人陳某偶遇馬某,閑聊中馬某提出去搞輛摩托車,陳某表示同意。后馬某去尋找目標,陳某在一加油站等候。當晚8時,馬某雇請被害人王某駕駛其三輪摩托車到上述加油站,并約好與陳某碰頭,馬某以等人為由讓王某下車等候。期間,馬某趁被害人下車未拔鑰匙之際,當著被害人的面迅速將摩托車開走。王某急于追趕,陳某以陳某臨時用車為由穩住被害人,之后陳某又以找馬某為由讓被害人原地等候,自己借故溜走。
該案件就是本文要探討的集“詐騙”、“搶奪”手段于一體的共同犯罪。陳某與馬某事前共謀去“搞”輛摩托車,且不論這里的“搞”字是搶奪還是騙取,其概括故意必然是共謀侵財。縱觀該非法侵財過程,由佯裝“雇請王某”到“馬某趁其不備將車開走”再到“陳某以臨時用車為由穩住王某”最后是“陳某借故溜走”,該過程經歷了“詐騙”、“搶奪”、“詐騙”。此外,被害人對被侵財物在認知上也存在變化,即從認為“摩托車被搶”到“摩托車被借用”再到“被騙”。在罪刑法定應有之義下,只能是詐騙罪或者是搶奪罪,筆者認為應定搶奪罪,具體理由將在下文闡述。
一、從犯罪行為人維度正向遞推考察
(一)共同犯罪與因果關系維度考察
犯罪行為共同說認為,共同犯罪是數人共同實施了行為,而不是共同實施了特定的犯罪,而部分犯罪共同說回答了“共同犯的是什么罪”是沒有實際意義的。[1]顯然,行為共同說側重從客觀描述,對主觀上共同犯罪故意的明確性要求較低。但是,司法機關運用該理論處理此類案件必然會遭遇案件的定性難問題。本案中馬某和陳某就是基于一個非法侵財的概括故意而共同實施了一系列“搶奪”和“騙取”行為,雖然在共同犯罪認定上不存在障礙,兩個參與人對法益的侵害結果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各參與人的行為在形式上是“搶奪”和“騙取”相互交織、配合,那么,對于該案的定性就不無疑問了。
共同犯罪理論應首先著重從客觀違法層面上解析共同犯罪,它要處理的問題是將已然出現的違法事實歸置于犯罪參加者的行為。本質上是為了解決各個參加者的行為歸責問題,即將已然出現的法益侵害結果歸責到各參與者的行為之上。具體到本案,就是如何將王某喪失了對摩托車占有這一法益侵害結果歸責到“詐騙”或者“搶奪”上,又或者是歸責到兩個行為上,即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因果關系的證明過程。本文案例中,危害結果是被害人王某對摩托車占有權的喪失,有待考究的是危害行為。危害行為,是指由行為人的心理活動所支配的危害社會的身體動靜,是犯罪構成的核心要件。[2]危害行為一般具備有體性、有意性、有害性三大特性,[3]有害性才是危害行為實質性要素。案件的定性就可以歸結到一個點上,那就是將造成法益侵害或侵害危險的結果歸置到具體的危害行為之上。本案中,馬某和陳某的行為存在有體性和有意性自不待言,在有害性方面,即法益侵害性方面有待進一步考究。
(二)實行行為——法益侵害緊迫危險性維度考察
危害行為雖然在客觀上表述為法益侵害可能性之行為,但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各參與人實施的行為都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司法裁判者需要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從多個危害行為中遴選出直接影響案件定性的一個或幾個危害行為,即對法益造成最為直接的、現實的、緊迫性危害的行為。我國刑法理論將危害行為區分為實行行為和非實行行為,關于實行行為的定義理論界未有一致定論。但一個法律概念的合理表述必須準確完整的描述此概念區別于彼概念的本質特征。實行行為區別于預備行為的本質特征在于著手開始實施實行行為就標示著實行行為所指向的法益面臨緊迫的、現實的侵害危險,表明侵害危險性已經無限地趨近現實的侵害結果,而預備行為則只是創造著手實施實行行為的各種條件。
馬某和陳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馬某和陳某共謀去搞一輛摩托車,然后馬某去尋找目標,陳某在加油站等候,之后馬某雇請被害人王某駕駛其摩托車至一加油站,這一系列行為都是基于一個概括犯罪故意之下的行為,是在為實現非法侵財目的創造各種條件,即為犯罪預備行為,其中馬某的雇請行為是欺騙行為。雖然這些預備行為的共同指向都是占有他人財產,都有法益侵害的可能性,但都不足以使法益產生現實的、直接的、緊迫性危害。因此,不能就此認定陳某和馬某構成詐騙罪。在詐騙罪的邏輯結構中,只有當受騙人基于欺騙行為產生錯誤認識而處分其財產時,受騙人的財產法益才存在現實的、緊迫性危險,馬某實施了具有欺騙性質的“佯裝雇請”行為,但是被害人王某并沒有就此欺騙行為作出任何財產處分行為。因為,此欺騙行為遠不足以使得被害人王某的摩托車產生現實的、緊迫性危險。
馬某趁其不備開走摩托車屬于搶奪行為,完全符合搶奪罪的構成要件。在傳統定義中,搶奪罪一般有“趁人不備而奪取”的特征性描述,此特征性要素在很多情況下不適用,因為即使是在被害人處于高度防備狀態時搶奪,只要搶奪行為的暴力不是直接針對財物持有人且暴力程度未達足以壓制財物持有人反抗的程度,不影響搶奪罪的成立。因此,搶奪罪應當被表述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公然奪取他人緊密占有的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4]不論“乘其不備而奪取”是否是必備要素,本案中,馬某的行為都足以構成搶奪罪。首先,馬某“趁被害人王某未拔鑰匙之際”,顯然符合“乘人不備而奪取”這一特征;其次,“當著被害人的面迅速將摩托車開走”,顯然符合“公然性”特征;再者,王某雖然已經下車,而馬某仍在車上,但摩托車仍然由王某緊密占有,即使是王某臨時有事暫時離開加油站,也不能否認王某對摩托車的事實支配,而事實摩托車持有人馬某充其量只是占有輔助。從法益侵害的緊迫危險性角度觀察,前述提及“雇請王某”這一欺騙行為只是犯罪預備行為,對法益的侵害尚不具備現實危險性,那么,馬某“趁王某下車未拔鑰匙之際啟動摩托車”的行為已經使得被害人對財物占有的法益產生了現實的、緊迫的危險,而摩托車啟動后被馬某迅速開車則是法益侵害已然變成現實,即搶奪罪犯罪即遂。
二、被害人主觀認知維度的反向考察
這一部分著重從被害人主觀認知角度考察,補強說明前述搶奪罪定性的正確性。在侵財類犯罪案件中,被害人主觀認知對于案件的定性和量刑不無意義,當謹慎處理,區別對待。
(一)被害人認識錯誤維度考察
認識錯誤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主體特定性,即犯罪行為人,二是認識錯誤的內容特定性,而被害人的認識錯誤則不在討論之列。司法實務和理論一般認為被害人主觀認識因素對于出入罪沒有或者至少沒有實質性影響,這導致了在出入罪時忽視被害人主觀認識因素的考量。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主觀認識因素盡管對出入罪意義不大,但是對于案件的定性不無意義。
在奪取類侵財犯罪中,盜竊罪較為典型。詐騙罪重要的一環是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其財產,這里的處分行為須是被害人認識到自己將財產交付給行為人或者第三者,否則只能成立盜竊罪。如甲在某超市購物時,偷偷將一個數碼相機藏在一箱礦泉水中并封裝好前往收銀臺付款,收銀員沒有發現數碼相機而只收取了一箱礦泉水的貨款。收銀員根本不曾意識到其處分一箱礦泉水中藏有數碼相機,即其不具有處分意識。行為人獲取數碼相機的方式實質上是最為傳統的盜竊類型及秘密竊取他人數額較大財物,故成立盜竊罪。很顯然,此類案件中被害人的認知錯誤直接決定了案件的定性。
(二)被害人虛假瑕疵意思維度考察
被害人虛假瑕疵意思主要影響案件的量刑,具體體現在影響犯罪停止形態進而影響量刑。在交付類侵財犯罪中,以詐騙罪和敲詐勒索罪為代表。在詐騙罪邏輯鏈條中,被害人是否基于錯誤認識交付其財產決定了案件的量刑。如果只是基于憐憫或其他原因將財物給付給行為人,則只成立詐騙罪未遂。敲詐勒索罪中,被害人是否基于恐懼心理交付其財產決定了案件的量刑,若被害人同樣只是基于憐憫或其他原因交付財物,則只構成敲詐勒索罪未遂。搶劫罪中,行為采取脅迫手段逼迫被害人交付財物的,被害人事實上非基于恐懼心理交付財物,同樣屬于搶劫罪未遂。根據刑法第23規定,未遂犯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被害人虛假瑕疵意思對于量刑的影響至此不待多言。
綜上,在侵財類案件中,被害人主觀認知因素對于案件的定罪量刑的影響不容忽視,尤其是在盜竊罪、詐騙罪、敲詐勒索罪等案件中。筆者認為以類型化思維梳理被害人主觀認識因素對于案件定性量刑的影響以增進司法實務和理論界對于案件判斷的準確定和便捷性尤為重要。立法者的任務便是去描述各種類型,立法的成功與失敗,端賴立法者能否正確地掌握類型。[5]目前我國刑法類型化思維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刑法的章節設置、犯罪構成要件、罪狀運用以及刑法解釋等方面。[6]但就侵財類案件而言,其類型化注意點大體有三:
一是嚴密的邏輯鏈條,行為人制造虛假、脅迫等不利信息致被害人產生瑕疵意思,被害人基于瑕疵意思而處分財產,結果是行為人非法取得被害人財產。前述關于詐騙罪、盜竊罪、敲詐勒索罪等論述足以證明這一點,并且也充分說明了被害人認知因素在刑事責任上的意義。
二是前述刑事責任意義上的不利信息須在犯罪既遂之前,否則對于法益侵害結果的出現毫無意義。該要點其實已經內含于第一要點,給予重申是因為有些案件中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數個行為人為實現犯罪目的共同或各自制造數個不利信息,此時就需要甄別出刑事責任意義上的不利信息。
三是不利信息須是各實行行為應有之意,是犯罪實行階段的不利信息。[7]
三、結語
司法實務中,我們通常可以憑借實行行為——法益侵害緊迫性來直接對案件進行定性,本文探討的主題——共同犯罪中“詐騙”“搶奪”手段交織的案件定性問題研究,案例中“搶奪”行為直接引發法益侵害緊迫危險進而正常地實現了法益侵害結果,藉此可徑直定性搶奪罪。而筆者從犯罪行為人正向維度(共同犯罪、因果關系、實行行為、犯罪停止形態)和被害人主觀認知因素反向維度(被害人主觀認識錯誤、被害人虛假瑕疵意思)綜合探討共同犯罪中“詐騙”、“搶奪”手段交織的案件如何準確定性,這樣的探討方式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案情。
注釋:
[1]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58頁。
[2]馬克昌:《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8頁。
[3]同[1],第145頁。
[4]張明楷:《盜竊與搶奪的界限》,載《法學家》2006年第2期。
[5][德]亞圖·考夫曼:《類推與事物本質——兼論類型理論》,吳從周譯,臺灣學林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版,第115頁。
[6]馬榮春:《刑法類型化思維——一種“基本的”刑法方法論》,載《法治研究》2013年第12期。
[7]犯罪預備階段的不利信息雖不能對案件定性產生影響,但應承認其可以成為酌定量刑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310004]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檢察院助理檢察員[2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