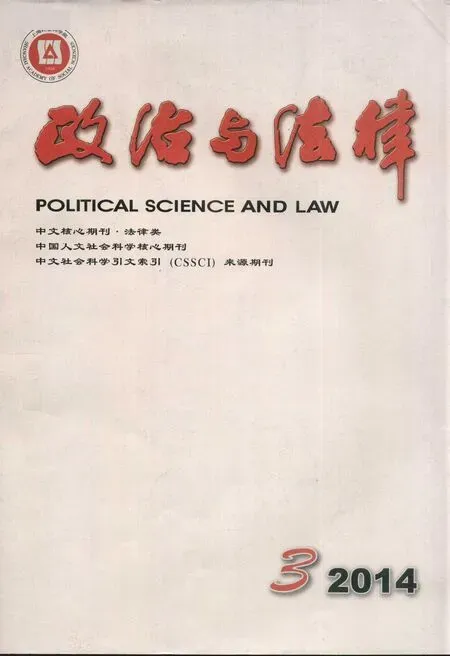責任主義與量刑規則:量刑原理的雙重體系建構*
姜 濤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責任主義與量刑規則:量刑原理的雙重體系建構*
姜 濤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量刑乃內在體系與外在體系的統一,前者由理念、立場等組成,以確立量刑的內在根據,而后者是由概念、規范等規則所組成,形成法官量刑的外在邊界。量刑固然以責任主義這一內在體系為基礎,但德日刑法規定的“行為人之責任為量刑之基礎”、“量刑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等一句話宣言,并不能對法官恣意量刑形成強有力約束。有鑒于此,量刑原理的建構應以責任主義為基礎,并重視量刑規則的合理建構。其中,量刑規則中的原則、概念、規范應實現制度理性與技術理性的統一,以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
責任主義;量刑規則;量刑基準
隨著我國量刑規范化改革的深入,量刑問題已經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如何在防止量刑恣意與量刑偏差中實現量刑公正,這是學界與官方大致認可的量刑規范化之建構目標。然而,學界目前大都把精力投放到對量刑規則的詮釋、兩高司法解釋的評析、基層司法機關實踐的推介等領域,量刑原理作為一種最為基礎也最為重要的理論建構,卻并沒有引起學界的應有重視。同時,在有限的量刑原理問題研究上,①參見張明楷:《責任主義與量刑原理——以點的理論為中心》,《法學研究》2010年第5期。仍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從哲學意義上的內在體系與外在體系出發,②法律規范乃是由外在體系與內在體系組成,前者體現為具體的規范建構,而后者則通過法律觀、原則等予以反映。參見姜濤:《社會管理創新與經濟刑法的雙重體系重構》,《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6期。建構一種責任主義與量刑規則相結合的量刑原理,以期能指導中國量刑規范化的改革實踐。
一、單一責任主義量刑原理的疑問
責任主義在目前中國學界是一種有力的學術立場。“刑罰以責任為基礎,沒有責任就沒有刑罰”(nulla poena sin culpa,Kiene Strafe ohne Schuld)的責任主義原則要求,行為人對其不法行為所產生的一切結果,應無條件地承擔責任。這里的“責任”與作為犯罪成立條件之一的有責性(也稱為責任)并非完全等同,而是由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組成的犯罪性,或者說是違法性與狹義的有責性相乘。也因此,這種責任不僅能夠確證刑罰適用的正當性,而且是適用刑罰時確定刑種、強度及其極限的根據。根據責任主義原則的要求,刑罰既然是作為有責的違法行為的抵償,就必須保持責任內容、責任程度與刑種、刑度的適當的比例或者均衡關系。除非基于預防的需要,國家不得基于任何功利主義的考慮,超越責任程度所容許的刑罰上限,適用與罪行及其罪責不成比例的刑罰。③參見梁根林:《責任主義原則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觀處罰條件的考察》,《清華法學》2009年第2期。為此,刑罰必須與違法性、有責性相適應,其中,違法性是指客觀的法益侵犯性,有責性是指主觀的罪過性,二者的統一體(罪行的輕重)就是責任刑的根據。④參見張明楷:《結果與量刑——結果責任、雙重評價、間接處罰之禁止》,《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堅持把責任作為量刑的根據,其意義體現在:能夠為法官公正量刑提供基準,防止法官恣意量刑,從而保障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實現。
如果說責任是量刑的最終根據,那么,明確責任的內涵就是第一要求。對此,古典學派與近代學派之間存在對立。古典學派主張應該根據犯罪本身的危害程度決定刑罰的程度,特別是應該科處與客觀的犯罪結果之大小相適應的同害報復的刑罰,強調刑罰的量定應與客觀行為及其實害相適應。而在近代學派看來,刑罰只有在實現一定目的即預防犯罪的意義上才具有價值,因此重視犯罪人的社會危險性,認為應該進行與其社會危險性相應的處分,因為不可能通過預測實現改善、教育犯人這一目的。⑤參見張明楷:《新刑法與合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不難看出,一旦具體到量刑根據以及刑罰制度的取舍問題,就會發現古典學派與近代學派的主張各自都有利弊,并且雙方的缺陷均需要另一方的優點來校正。同時,由于它們是從不同角度說明刑罰正當化根據以及量刑需要參考的標準,故二者并不完全相斥,可以結合成為合并主義所主張的相對報應刑論。在采取合并主義的刑法規定中,一般將行為責任作為量刑的首要根據,將預防犯罪目的作為次要根據。⑥同上注,張明楷文。正如德國學者毛拉赫所指出,量定刑罰的基礎不是與報應對立的預防(Vorbeugung neben Vergeltung),而是處在報應中的預防(Pr?vention innerhalb Vergeltung)。⑦轉引自[日]大冢仁:《刑法概論(總論》(第三版),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0頁。既然如此,犯罪的輕重必須根據該犯罪的具體違法性的輕重和責任的輕重來確定。違法性的輕重必須根據行為和行為人的侵害法益或者危害法益的程度、違反國家社會倫理規范的程度來確定。而確定責任的輕重時,必須考慮責任能力的程度、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的程度、決定故意和過失各種要素具體達到什么程度。確定刑罰的輕重必須以責任的輕重為核心。⑧[日]大冢仁:《刑法概論(總論》(第三版),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0頁。其實不只是學者的主張,立法對此也有明確規定,比如,《德國聯邦刑法》第46條規定:“行為人之責任為量刑之基礎,且應該考量刑罰之效果是否符合社會上對行為人未來生活之期待。并應斟酌之。”《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條第1項也規定:“刑罰應當根據犯罪的責任量定。”從而明確了責任在量刑中的基準意義。不可否認,使刑罰與行為人責任的大小相適應,從而使刑罰更加人道,克服了殘酷的刑罰,因而具有重大意義。
問題只在于,“量刑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或“刑罰應當根據犯罪的責任量定”的一句話宣言,能否成為法官公正量刑或避免量刑失衡的制度保障呢?筆者對此深感懷疑。
其一,量刑是由理念、技術與規則所確保的法官活動,它既非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結果,也非完全像自動售貨機一樣刻板得出,而是法官依據量刑規則和遵循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結合案件中的量刑情節,甚至是基于司法之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考慮而得出的。有學者在主張責任主義原則時指出:“在整體上回答了刑罰的正當化根據,也就在具體的量刑問題上回答了刑罰的正當化根據。”⑨同前注①,張明楷文。這一觀點值得商榷,因為責任主義原則主要是為法定刑設定提供依據,其雖然也影響到量刑,但仍因其過于理論化、抽象化而缺乏可操作性。或者說,責任主義原則只是為量刑提供了必要的理念:沒有責任者,不得定罪判刑;有責任者,也需要適度量刑。但是,如果我們寄望于這種理念的確定就可以確定最終的宣告刑,則又犯下了最常識性的錯誤,因為量刑涉及責任刑與預防刑,司法實踐中需要突破責任刑的情況也十分常見,而且在理論上也有學者主張宣告刑可以突破責任刑的限度,比如,德勒赫(Dreher)教授就指出:“根據德國刑法第46條第1款前段,責任只不過是量刑的基礎,只要刑罰的中核仍然處于責任刑,就必須允許以對行為人的效果為理由,擺脫上限與下限。”①同前注①,張明楷文。
其二,責任主義原則旨在限制刑罰權的不當發動,并不能為宣告刑提供明確依據。量刑的任務在于依據法定刑得出宣告刑。那么,責任主義能夠圓滿完成這一任務嗎?歷史地看,早期學者把責任定位為心理責任,認為責任就是“行為人對于行為的主觀心理關系”(Schuldbesteht in der psychischen Beziehung desTaters zurTat)。②轉引自林鈺雄:《新刑法總則》,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79頁。根據心理責任論,行為人在具備責任能力的基礎上,必須具有罪過(故意或過失)才能被處罰。后來,規范責任論替代心理責任論而成為通說,但這一學說也只是將“無責任能力、無違法性意識可能性、無期待可能性所形成的無非難可能性之行為”與“無故意、無過失”等一同視為刑法中不可處罰的行為。③參見陳子平:《刑法總論》,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02頁。可見,責任主義原則只是解決是否處罰的問題,④⑩在日本學界,關于責任主義有消極責任主義與積極責任主義之分,其中,“沒有責任就沒有刑罰”是消極的責任主義的經典表述;而“有責任就有刑罰”則是積極的責任主義的表述。(參見[日]平野龍一:《刑法總論I》,有斐閣1972年版,第52頁以下)。不難看出,積極責任主義和消極責任主義雖然表述不同,但都是著眼于以是否構成犯罪來判斷是否處以刑罰。正如日本學者所指出:“‘沒有責任就沒有刑罰’的消極責任主義,是與‘有責任就(必)有刑罰’的積極責任主義對置的。可以說,消極的責任主義的旨趣在于,沒有責任時不應科處刑罰。不僅如此,即使在有責任時,從一般預防、特殊預防的觀點來看,其他制裁或處分適當時,就應當控制刑罰的適用。”⑤[日]西田典之:《新版共犯と身分》,成文堂2003年版,第284頁。甚至有學者否定責任對量刑的價值,如井田良教授曾指出:“與不法不同,責任并不為處罰提供根據,只是單純地限制處罰,其自身并不具有獨立的分量;具有分量的,僅僅是違法性的程度。當在違法性階段存在10個不法的基礎時,在責任階段的問題是,對其中的哪個不法可以進行主觀的歸責(例如,可能得出歸責被限定為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結論)。”⑥[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學》(總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156頁。盡管對責任之于量刑的價值存在爭議,但沒有分歧的是:責任在限制過剩或殘虐的刑罰上作用十分有限。而過剩或殘虐的刑罰恰是當前量刑不公的“重災區”,也是我國量刑規范化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其三,責任主義原則也存在例外。梁根林教授論證了這種例外,他指出:“責任主義原則并非沒有任何例外的教條。客觀處罰條件是基于刑法以外的目的設定即控制風險的公共政策需要而設置的犯罪成立條件,是責任主義原則的例外。現代刑法體系中刑事責任基本原則與刑法例外規范共生共存的現象具有規律性。”其實,客觀處罰條件只是例外的一種,刑事政策、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和解等也會影響到法官量刑,這是另一種例外。學界的主張也大抵如此,張明楷教授指出:“即使承認責任為刑罰提供根據,也只是意味著責任是成立犯罪和科處刑罰的前提條件。”⑦同前注①,張明楷文。即量刑除了考慮責任之外,尚需考慮特殊預防的需要。因此,量刑涉及量刑情節等規范性要素和理念、技術、民意、法官自由裁量權等非規范性因素,這就不是“刑罰應當根據犯罪的責任量定”等一句話宣言所能完成的。更何況,量刑公正并非唯一依據行為人的責任即可得出,它是權威、倫理、制度和程序諸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實現需要在倫理認同的基礎上構建制度和程序,并使量刑獲得其權威性。①參見姚莉:《司法公正要素分析》,《法學研究》2003年第5期。
其四,從奉行責任主義原則的德、日等國家刑法規定來看,責任主義原則也只是量刑的標準之一。《德國聯邦刑法》第46條第2項規定:“法院于量刑時應權衡一切對于犯罪人有利與不利的情況,尤其應注意下列各項:犯罪人之動機與目的,行為表露的心情及行為時的意志,違反義務的程度,行為的實施形式與可歸責的結果,犯罪人的生活經歷,其人身的及經濟的關系,以及其犯罪后的態度,尤其補償損害的努力和實現與被害人和解的努力。”《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條第2項規定:“適用刑罰時,應當考慮犯罪人的年齡、性格、經歷與環境、犯罪的動機、方法、結果與社會影響、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態度以及其他情節,并應當以有利于抑止犯罪和促進犯罪人的改善更生為目的。”在這里,無論是德國刑法規定的“應該考量刑罰之效果是否符合社會上對行為人未來生活之期待”,抑或日本刑法規定的“應當以有利于抑止犯罪和促進犯罪人的改善更生為目的”,都是責任主義原則之外的標準。理論上對此也有支持,比如,有的理論(也可稱:點理論)認為,與責任相適應的刑罰只能是正確確定的某種刑罰(點),而不存在幅度。在確定了與責任相適應的具體刑罰(點)之后,為了考慮預防犯罪的需要,可以修正這個點,但不能過于偏離這個點。②同前注④,張明楷文。因而,這是一種對責任刑與預防刑綜合考慮的觀點。
總之,責任主義原則雖從總體上明確了量刑的“基準”,需要以行為人的不法與責任程度相適應,但責任主義原則乃屬于理念性規定,它提供的是比較抽象的、理念性的“基準”,因此,僅有這種理念性的量刑原理建構還不夠,尚需以量刑規則的建構給法官公正量刑提供一個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準。
二、量刑規則對矯正量刑失衡的制度績效
責任主義原則可以被視為量刑原理的內在根據,屬于量刑的內在體系,而依據責任主義原則建構的量刑規則則對法官具有直接制約意義,屬于量刑的外在體系,它們都構成了量刑原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量刑失衡:量刑實踐所不能承受之重
欲要明確量刑原理如何建構,以及其基本內容,需要結合中國司法實踐,確定中國量刑實踐所面臨的問題是什么,這是建構量刑原理的源動力或理由。
長期以來,量刑失衡是一個困擾刑事司法的焦點問題,解決這一難題也被學者稱為刑法學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美國參議員埃德伍德·M·肯尼迪(Edword·M·kennedy)曾對美國量刑之亂象作過如下評論:“今天,量刑是國家的丑聞。每天,不同的法官對被指控有類似罪行的被告科以截然不同的刑罰,一位可能被判緩刑,而另一位罪行相似的被告則可能被判長期監禁。”③[美]克萊門斯·巴特勒斯著:《矯正導論》,孫曉靂、張述元、吳培棟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頁。把問題切換到中國,則不難發現,中國當前的量刑規范化之所以被提倡并啟動,乃是因為法官量刑中的亂象,即重罪輕罰與輕罪重罰等量刑結果的差異,而不是基于對有罪不罰或無罪懲罰之責任主義原則的違反。這在基層人民法院的量刑規范化改革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等中得以集中體現。比如,江蘇省姜堰市人民法院作為全國最早進行量刑規范化改革的試點單位,乃是基于本院中法官對三個交通肇事案件的量刑差異入手進行改革。④這三起交通肇事案均造成一人死亡且都負事故主要責任,同時也均有自首與賠償被害人損失的從寬量刑情節,但三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一年與一年半。參見湯建國主編:《量刑均衡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而《意見》則更為開宗明義地指出:“為進一步規范刑罰裁量權,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增強量刑的公開性,實現量刑均衡,維護司法公正,根據刑法和刑事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結合審判實踐,制定本意見。”這就直接表明了我國量刑規范化改革的目標是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以實現量刑公正,而不是德日刑法語境意義上的超越責任主義原則量刑的問題。
歸納來看,司法實踐中的量刑失衡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1)重罪輕判,即在不具有法定或酌定從輕或減輕處罰情節的情況下,由于缺乏具體、明確的量刑規則,對重罪判處一個輕的刑罰;(2)輕罪重判,即在不具有法定或酌定從重處罰情節的情況下,對輕罪判處一個重的刑罰;(3)相似案件沒有特殊預防的需要而判處差異較大的刑罰;(4)濫用緩刑與死緩。這些亂象并非主觀感受,而是一個可觀察并由統計數據說明的特征化事實。如,在均沒有自首、特殊動機且均坦白的情況下,張某某盜竊他人財物價值6萬元,被XXX基層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宋某某盜竊他人財物61萬元,被XXX中級法院判刑11年。此外,在姜堰市人民法院對2000至2003年內所審結的刑事案件量刑狀況進行的檢查中發現,900多件刑事案件中,同類案件、性質相同、情節相近的,量刑相差1年以內的占50%,量刑相差1年以上的則占30%,而量刑接近的只占20%。①參見丁國鋒:《江蘇姜堰法院量刑“五步曲”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法制日報》2009年4月13日。
造成這種量刑亂象的原因主要有二個方面。一是立法與司法之間存在的緊張關系。由于刑法分則部分對具體個罪法定刑設置的幅度過大,不少罪名的法定刑設置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加上刑法有一定數量的情節犯、結果加重犯,并對死緩與緩刑等的適用條件使用了諸如“罪該處死,但不需要立即執行”、“確實不至于再危害社會”等抽象語言,這就會造成立法與司法之間的緊張關系。二是司法腐敗或司法創收導致量刑上的人為差異。由于司法腐敗的存在及法官面臨著創收的任務,也導致量刑中的人為差異,比如,法定、酌定從寬量刑情節的從寬幅度最大化,形成寬大無邊,或者以“認罪態度好”、“退清贓款贓物”、“被害人寬恕”等理由予以大幅度地從寬量刑。此外,法官的認知與目標差異也會導致量刑偏差。經過法定程序制定的刑法仍然是不完全和抽象的,實施過程中必然有其他一系列因素的介入,其中,人們的認知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法官完全可能由于自我知識、經歷等差異而導致量刑結果上的差異。
因此,尚需追尋能夠避免立法與司法之間緊張關系并能夠有效預防司法腐敗的量刑規則。
(二)量刑規則:矯正量刑失衡問題的出路
如何看待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是實現量刑公正的大前提。從法律實施的角度分析,當代學界不會再否定這種觀點:當法官素質高且司法權威得以有效確立的情況下,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這不僅不會導致法官恣意量刑,而且有助于實現量刑的個別化,進而確保量刑公正的全面實現;而相反,如果法官整體素質不高,或司法腐敗現象嚴重,則需要以剛性的量刑規則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以避免法官恣意量刑或司法腐敗。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法官素質有待大幅提高的時代。
不獨此也,即使在法官素質很高的國家,重視量刑規范的建構,也是量刑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美國就是較早實行量刑規范化的國家,《美國量刑指南》(以下簡稱《指南》)是當前不少國家與地區學習的榜樣,而這一量刑規則乃是美國決策者矯正量刑亂象的產物。1973年聯邦地方法院法官馬文·福南克(Marvin E.Frankel)發表了一本名為《量刑:沒有規則之法律》(Criminal Sentences:Law Without Order)的書,引起美國司法界及法律學界極大的重視與討論。當時福南克法官在紐約市的聯邦地方法院任職已15年,經驗豐富,見解犀利,被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尊稱為“量刑改革之父”。福南克法官認為:“在量刑之領域,我們給予法官幾乎完全不受約束而全面性之權力,這對宣稱法治社會的我們而言,是令人震驚而且無法忍受的事。”②Marvin E.Frankel,Criminal Sentences:Law Without Order,1972,p5.馬文·福南克的這一觀點引起法律界的巨大關注,1974年耶魯大學法學院專門成立針對量刑差異的實務研討會,也呼吁成立量刑委員會,制定強制性的量刑規則。1984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與民主黨均以打擊犯罪作為重要訴求,于是,綜合犯罪控制法獲得國會通過,其中,包括量刑改革法案及聯邦量刑委員會的設立,被收錄于聯邦法典第18編與第28編,統稱為1984年《量刑改革法》(Sentencing Reform Act)。在《量刑改革法》的授權下,美國設立了量刑改革委員會,由其草擬聯邦量刑指南,并在1987年4月13日向參議院提出第一版的量刑指南,經參議院審議通過,于同年11月1日生效。《指南》長達一千多頁,對各種犯罪如何科處刑罰規定極為詳細,它以量刑表(Sentencing Table)的方式,規定量刑結果之計算法則。根據該指南,每一犯罪均有一個基本的犯罪級數(Base Offense Level),法官依據該基本犯罪級數,依據量刑情節調節犯罪級數(共43級),并依被告之前科記錄計算被告之前科級數(共6級),二者之縱橫連線將對應量刑表之258個格子中的一格。法官原則上只能在該格子之幅度內進行量刑。此外,量刑改革法要求每格中最高法定刑不得高于最低法定刑之25%或6個月有期徒刑,以免同一格內量刑之結果差異較大。①參見吳巡龍:《美國的量刑公式化》,《月旦法學雜志》2002年第85期。此外,英國施行的《量刑準則》②英國的《量刑準則》主要由《總的原則:犯罪嚴重性程度》(主要是確立犯罪的嚴重性程度依賴于行為人的主觀罪責、客觀危害或危險的評價原則)、《2003年刑事審判法新刑罰的適用原則》(即確立新刑罰類型的適用規則)和《認罪的量刑減讓》(對被告認罪的量刑折減定出原則那個規定)三部分組成。、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省施行的《量刑資訊庫系統》③這是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的電腦化量刑資料庫,該資料庫并不用直接對法官提供所擬判決的結果,更不指示法官量刑權的運作,只是提供有關類似案件最高和最低的量刑規定,將量刑的決定權交給法官,讓法官從保障量刑的一致性的角度考慮,盡量選擇該資料庫所提供的平均值。、荷蘭施行的《北極星準則》④北極星準則的目標有六項:統一的標準、無差異的司法、有條理的準則系統、易于理解的司法、成比例的刑罰和將不一致的量刑減至最低程度。等,也都是量刑規范化的制度體現。
盡管美國量刑指南在實施20年的時間內,就由強制性規則變為參照性規則,但我們并不能抹殺其制度績效。《指南》基本上是一種判例法范圍內具有制定法效力的規范性文件,其基本原理是經驗歸納和概率計算,主要作為判決結果的預測,而核心則表現為量刑幅度的數值化,這主要有“徒刑”和“罰金”兩個量表。它是美國量刑委員會在審查《美國法典》中數百個刑事法律并加以整理的基礎上,針對具體罪名搜集約5萬份案例資料(含4萬份有罪判決的簡要報告與1萬份的審前調查報告),經過十幾年的總結、分析與比較,確定每一種犯罪的適當量刑幅度。以徒刑量刑表為例,表的縱軸代表43個“犯罪等級”(offence level),表示犯罪行為嚴重性程度的等級。縱軸代表6個“犯罪歷史標度”(criminal history point),表示被告犯罪歷史的危險性等級。透過縱橫兩軸的交叉結合,得出一個特定的量刑格,作為徒刑幅度范圍的依據。就制度績效而言,在《指南》之下,量刑乃被視為一種客觀活動,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極度萎縮,這就最大限度意義上保障了量刑統一化。自《指南》實施到2004年,以聯邦法院為例,符合量刑幅度內的量刑,大約都維持在65%至80%之間。如果將合理偏離《指南》的案件計入,比例則高達九成以上,足見《指南》對美國量刑實務的積極影響。⑤See Hinojosa,Richardo.Final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United States v.Booker on Federal Sentencing.D.C:U.S Sentencing Commission,2006,p.56.同時,在美國,為何將定罪的權力交由陪審團,而將量刑的權力交由專業法官,也是因為量刑是一種非常專業、復雜的活動,需要立足于刑罰目的,并在綜合評估行為人之責任的基礎上,依據經驗、規范、技術等作出判定。
有種觀點認為,量刑規范化應當緩行,這是因為:其一,“立法合理的前提下,司法裁量權的限制是實現公正的重要途徑;在立法本身存在一定不周延甚至重大問題的前提下,司法裁量權的嚴格限制會使公正的實現更加困難”;其二,“越是細密的立法規定,司法的裁量余地越小,實現司法公正也就越發困難”。①參見李潔:《論量刑規范化應當緩行——以我國現行刑法立法模式為前提的研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第1期。筆者認為,主張量刑規范化應當緩行,其實就是否定量刑規則的價值。一直以來,學界都在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有無、幅度等進行爭論,現在已經沒有學者像概念法學那樣全盤否定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意義,而是和上述否定論者一樣主張法官自由裁量權對實現司法公正的意義。然而,這并不排除的另一種情況是:如果法官整體素質有待提升且自由裁量權過大,而法律又沒有為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提供一定的實體標準與程序保障,則同樣會使法官在自由裁量權的幅度內為自己謀取利益,并作出不公正的判決。這就不僅會導致司法不公,甚至會形成司法腐敗。以此審視中國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我們不難發現,由于刑法典在有期徒刑問題上沒有分等、分級,以致于刑法典中存在著諸多“5年以上有期徒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等巨大的自由裁量幅度,同時,也因為把“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同時規定在一些結果加重犯的法定刑之中,這就使法官在量刑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也帶來了司法實踐中的諸多量刑亂象。為了避免量刑亂象,顯然不能只依賴于法官的公正與良知,更需要以量刑規則確保量刑公正的實現。
就此而言,“兩高”頒布的兩個有關量刑的司法解釋,所要實踐的目的是均衡與公平兩大原則,作為最小公約數,量刑規范化之目的主要體現為不合理差異的縮小或排除。
三、應建構責任主義與量刑規則相結合的量刑原理
量刑必須以公正、均衡和實現社會目標為基本訴求,這就不能采取“幾兩罪,承擔幾兩責,也就判幾兩刑”這種數量對應的量刑模式,而是需要立足于現代責任主義原則,建構相應的量刑規則,以供法官遵守。這才是我國量刑原理的建構方向。
(一)外在體系:重視量刑規范化建構
外在體系乃是立足于責任主義原則,以具體的、可操作的量刑規范使法官能夠規范地、有效地根據案件基本事實從法定刑設定的幅度中得出基準刑,并依據量刑情節和立足于責任刑與預防刑之間的辯證關系,得出公正的宣告刑。
有爭議的問題是:量刑規范化是否等于是量刑精確化或電腦量刑?有學者指出,規范量刑就是采用科學方法精確計算行為人的罪責程度和刑罰程度,揭示兩者相互對應轉換的內在聯系,求解量刑公正的最佳適度,最大限度避免刑罰打擊誤差。①參見趙廷光:《論量刑精確制導》,《現代法學》2008年第4期。筆者認為,這一主張看似合理,也能夠迎合最高司法機關改革的要求,但如果把法官量刑演變成為自動售貨機式的操作,則存在著重大風險。其一,從域外的經驗來看,以精確化作為量刑規范化建構的目標,也不具有恒常制度的意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于2005年1月12日,以U.S.v.Booker and U.S.v.Fanfan一案,②125 S.Ct.738(2005)宣告1984年《量刑改革法》(Sentencing Reform Act of 1984)中,賦予聯邦量刑準則強制性(mandatory)的兩項條款無效,這被視為法官量刑權限受到聯邦量刑準則箝制的反動,也意味著自聯邦量刑準則于1987年11月1日生效施行以來,法院量刑權的桎梏,至此終告解除。其二,從理論上分析,精確量刑意味著把罪—責—刑之間的對應關系數量化,轉化成量刑情節與量刑結果之間的“計算”,會導致“5兩罪=5兩責=5兩刑”的機械數量對應,這就完全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不僅不利于實現量刑公正,而且也無法實現刑罰目的(特殊預防維度)。同時,這一主張還屬于早期概念法學的基本主張,即以概念清晰、邏輯嚴謹的法律文本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因此,不僅飽受法社會學、利益法學的批判,而且明顯落后于時代發展以及民眾對量刑公正的期待。其三,量刑精確化不符合刑罰個別化的需要。一般認為,刑罰目的在立法、司法與執行階段具有不同的詮釋,在立法階段應該以一般預防為主,特殊預防為輔;司法階段應該以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并重,而執行階段應該以特殊預防為主,一般預防為輔。③王世洲:《現代刑罰目的理論與中國的選擇》,《法學研究》2003年03期。盡管,我們可以在理論上將其區分為不同階段,但量刑規范建構則必須首先考慮規范的實施問題,并在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之間達致最佳平衡點,這就需要在確保刑罰統一化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刑罰個別化。很顯然,那種以量刑精確化為制度建構的努力,只能有助于實現刑罰統一化,而抹殺了刑罰個別化的意義。于此還要求解的是,我們又應該如何定位量刑規范化。
其一,量刑規范化必須服務于刑罰目的。哲學上的刑罰目的可以分為兩個類別:一是報應傳統(retribution tradition);一為功利傳統(utilitarian tradition)。前者主張刑罰應該建立在罪有應得的基礎之上,重視罪刑均衡;后者則主張量刑應該達到一些目的,比如威懾、恢復被害人利益或社會復歸等。不同的理論建構,會有不同的量刑政策選擇,但兩者均不排除同等情況下的量刑結果差異不能太大,有區別的是不同情況下量刑差異存在的正當性根據是什么,報應傳統將其解釋為責任程度上的差異,從而使傳統意義上的結果責任論發展到心理責任論,再發展到規范責任論,最終逐步向功能責任論靠攏。而功利傳統主張在責任刑的基礎上重視預防刑,強調量刑不僅具有預防犯罪之目的,而且還有被害人利益恢復、社會復歸等功利目的。現代刑法目的理論往往是在報應傳統與功利傳統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即將報應理論與功能理論合并起來進行理解,而以正義及合目的性作為刑罰根據。④參見甘添貴:《刑法之重要理念》,臺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24頁。
其二,量刑規范化并不能夠成為嚴格規則主義的“復辟”。嚴格規則主義主張,立法者“試圖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辦法,它的最終目的,是想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律據典,同時又禁止法官對法律作任何解釋”。⑤[英]梅里曼:《大陸法系》,顧培東等譯,西南政法學院1983年印行,第42頁。這乃是早期概念法學的基本主張,在當代已經被證明為不可行,也不合理。Michael Tonry就曾指出:“恰當的量刑制度需要有足夠的限制(constraining enough),以確保類似的案件能得到相近的刑期與處置方式(like cases are treated alike);量刑制度亦需要有足夠的彈性(flex able enough),以確保不同情節的案件能得到不一樣的刑期與處置方式(different case are treateddif-ferently)。”①Michael Tonry,Sentencing Matt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54.這也許是一個不能達到的完美狀態。不過,這既是大眾所希望的,也是我們需要努力建構的量刑系統。
其三,量刑規范化的核心在于實體標準的建構。就實體建構而言,量刑規范應該為法官的評價提供明確的范圍與方法。我國刑法第61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不難看出,這只是為量刑規定了評價的依據,并且這種規定與《德國聯邦刑法》第46條、《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條相比,不僅更抽象,而且還構成了重復評價,即犯罪的事實基本上決定了犯罪性質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就此而言,中國量刑規范化的首要任務是實現量刑評價范圍與方法的法定化,即哪些情節或要素可以影響法官量刑以及影響程度如何等,應該由量刑規范做出盡可能完備的規定,即除了刑法已經規定的自首、立功、累犯等之外,立法者應該根據司法實踐的經驗,慎重對待犯罪動機、目的、行為意志、義務違反程度、彌補被害人損失的努力、刑事和解等對量刑的影響。此外,量刑規范還應該為法官量刑提供評價方法。首先,應該禁止重復評價,即一個事實不應該在定罪事實中評價之后,再在量刑中重復評價一次。其次,應該提倡折衷式量刑準據,它是指程序上強制法官去考慮量刑準據,但實體上法官因個案合理之考慮,則得排除適用,而上訴審則可就“量刑裁量有無濫用”加以審查。最后,應該以量刑比例、量刑基準等架設量刑情節對宣告刑影響的比例關系。具體量刑情節對法定刑的影響幅度是多少,則必須以量刑比例方式予以規定,并且以量刑基準明確“罪—責—刑”之間的對應關系,以為法官量刑提供判斷基準。
(二)內在體系:重視現代責任主義原則
作為前提,以何種刑罰種類處罰以及判處多重的刑罰,這是刑法和刑法理論所共同涉及的核心問題。這大約涉及如下基本問題:一是在《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對自首、立功、悔罪表現等影響宣告刑的幅度(量刑比例)做出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如何判斷具體個罪的基準刑(或處斷刑)乃成為量刑的難點,而這種難題的破解又有賴于量刑規則對量刑基準的規定。因為“當前的量刑規范化試點或者改革,大體上是以上述具體個罪的量刑基準論為理論支撐展開的”。②同前注①,張明楷文。因此,下文僅以量刑基準為例,說明責任主義原則對量刑規則的制約意義。
對于量刑基準是什么,國內學界目前主要有三種觀點。(1)量刑根據論。該觀點認為量刑基準主要是解決量刑的考量要素,以及運用什么原則來進行量刑的問題。③參見陳興良:《刑法適用總論》(下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頁。(2)刑罰量論。持此論者把量刑基準視為對已確定適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抽象個罪,在不考慮任何量刑情節的情況下,僅依其犯罪構成事實所應當判處的刑罰量。④參見周光權:《量刑基準研究》,《中國法學》1999年第5期。(3)“平均刑量論”,即“作為法制實踐離散程度的客觀反映,量刑基準是某種犯罪各組權威示范性案例樣本之間相互獨立的平均刑量”。⑤白建軍:《量刑基準實證研究》,《法學研究》2008年第1期。而德日學界主要有點的理論與幅的理論之爭。前者認為,“與責任相適應的刑罰只能是正確確定的某個特定的刑罰(點),而不是幅度”;后者則認為,“與責任相適應的刑罰(或以責任為基礎的刑罰)具有一定的幅度,法官應當在此幅度范圍內考慮預防犯罪的目的,最終決定刑罰”。⑥同前注①,張明楷文。筆者認為,把量刑基準等同于量刑根據,這雖然有助于劃定量刑評價范圍,即哪些事實對量刑具有制約或影響作用,但卻混淆了量刑基準與宣告刑之間的關系,因此并不可取。“平均刑量論”把量刑基準界定為某種犯罪各組權威示范性案例樣本之間相互獨立的平均刑量,這從實證的角度表明了量刑基準乃是以往所判案例之宣告刑的平均數,也指出量刑基準與宣告刑之間的平均數,但卻在可操作性上不僅沒有考慮到中國刑法“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模式,而且如何得出犯罪各組權威示范性案例樣本之間相互獨立的平均刑量乃面臨著技術難題。國內學者所主張的“刑法量論”與德日國家學者堅持的“點的理論”與“幅的理論”之間具有明顯的親緣關系,只是,點的理論把抽象個罪在不考慮任何量刑情節的情況下,犯罪構成事實所對應的刑罰量解釋為一個具體的刑種或某個確定的刑期,以得出責任刑。而幅的理論把其視為一個幅度,強調責任刑與預防刑并重,這是綜合刑論的基本主張。
其實,如何定義量刑基準,與我們建構量刑基準這一概念的功能密切相關,量刑基準與量刑根據不同,它在于為法官確立基準刑提供一個標準與方法,即法官依據法定的量刑基準,可以比較客觀、準確、快速地得出基準刑,并綜合考慮各種對被告人有利與不利的量刑情節(量刑根據所確定),得出一個公正的宣告刑。這在《意見》中得以集中體現,《意見》明確了“根據基本犯罪構成事實在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根據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實,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根據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并綜合考慮全案情況,依法確定宣告刑”的量刑步驟,這就要求法官合理確定具體個罪的基準刑。問題是:如何確定該基準刑呢?因為刑法中存在著大量的結果犯,這些犯罪大都以犯罪數額、犯罪次數或犯罪情節等作為犯罪成立的要件,并且隨著犯罪數額、犯罪次數和犯罪情節的變化,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也隨之變化,所以,我們必須以技術理性建構這種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數量對應關系,以為法官確定基準刑提供標準。這就需要針對抽象個罪建構出量刑基準。就此而言,點的理論把量刑基準視為一個確定的刑期或刑種,這與基準刑存在著混同現象,它表明的其實就是《意見》所指的基準刑。而相反,幅的理論指出了量刑基準的本質,它表明了量刑基準乃是一個刑罰幅度,如德國聯邦法院1954年11月10日的判例指出:“什么樣的刑罰與責任相當,不可能正確地決定。在此存在一個有界限的幅度,即下限的刑罰已經與責任相當,上限的刑罰也與責任相當。事實審的法官(Tatrichter),不得超過上限。因此,就刑罰的程度與種類而言,他不得科處他自己也認為與責任不相當的嚴厲刑罰。但是,在此幅度內應當判處什么樣的刑罰,他是可以自由裁量來決定的。”①同前注①,張明楷文。不難看出,幅的理論立足于責任刑與預防刑之間的平衡,主張量刑必須綜合考慮案件中罪量與刑量之間對應的比例關系,不同具體個罪的罪量不同,因此,其刑量自然也不同。這就需要以一定的刑罰幅度體現責任主義原則。就此而言,幅的理論具有合理性。問題是,幅的理論能否以規范形式加以規定,這在德國判例及刑法理論中都沒有明確。因此,也留下了未完成的遺憾。
筆者曾指出,量刑基準與基準刑不同,前者是一個幅度,為確定基準刑服務,而后者是一個確定的點,為得出宣告刑服務。為發揮量刑基準的這種功能,量刑基準應該是一種確立程式,即首先有一個起點刑,基準刑的確定不得低于這個起點刑。然后,隨著犯罪數額、犯罪次數、被害人的人數或犯罪后果等的加入,基準刑也隨之增加,這就等于向法官提供了一個計算基準刑的確立程式。②參見姜濤:《量刑基準:從點幅之爭到確立程式》,《云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以《意見》有關交通肇事罪之量刑基準的確定為例,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1)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可以在六個月至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2)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3)因逃逸致一人死亡的,可以在七年至八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同時,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責任程度、致人重傷、死亡的人數或者財產損失的數額以及逃逸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①參見2010年10月1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常見犯罪的量刑”部分。在這種規定的背后其實隱含著一個“以起點刑為基礎,隨著責任程度、致人重傷、死亡的人數或者財產損失的數額以及逃逸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的增加,基準刑之刑罰量亦增加”的遞增公式。這種量刑基準雖然不具有普適性,但對于結果犯、結果加重犯等來說具有意義。
然而,這種刑罰量的增加必須建立在責任主義原則之上。在當今刑法理論中,責任主義原則主要在兩個層面存在:一是歸責意義上的責任主義,它以“無罪責則無刑罰”為號召,②[德]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修訂譯本),徐久生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頁。目的在于通過限制國家刑罰權來實現對人權的保障,它意味著無故意或過失,無責任能力、無違法性意識可能性、無期待可能性,都不具有非難可能性,都不得作為犯罪加以處罰;③同前注?,陳子平書,第302頁。二是量刑意義上的責任主義,責任屬于報應論體系中的基本范疇,它不僅為國家對行為人發動刑罰權提供了正當根據,而且要求刑種、刑度與刑種、刑度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以防止刑罰權的濫用或任意擴張。④同前注③,梁根林文。盡管,當代刑罰理論強調責任與預防并重,比如,羅克辛指出:“目的理性體系以這里所代表的形式提出的第二個核心創新,形成了把‘罪責’擴展為‘責任’的范疇。在這里,對于罪責這個各種刑罰必不可少的條件,總還必須補充進刑事懲罰的(特殊或者一般)預防必要性。因此,罪責和預防性需要是相互限制的,然后才能共同產生引起刑罰的行為人個人的‘責任’。”⑤[德]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頁。然而,在基準刑的確立上,這是立法應該規定的內容,這種規定應該以報應論為基礎,強調一般預防,所以,基準刑的確立必須以責任主義原則為基礎,其正如耶賽克教授所指出:“保護社會的目的只有以公正的方式才能實現(聯邦法院刑事判決24,40)。如果刑罰應當作為有責的違法行為的抵償,就必須保持責任內容和刑罰的適當的比例關系,過高或過低地適用刑罰都是應當予以禁止的。”⑥[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頁。就此而言,量刑基準中起點刑的確定,以及基準刑增加的幅度與標準等的確定,則必須立足于責任主義原則予以合理確定。這不僅需要在具體個罪內部評估罪—責—刑之間的對應關系,而且需要評估具體個罪與具體個罪之間罪責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刑罰之間的協調性,不允許在罪刑規范層面上出現重罪輕罰和輕罪重罰現象。
總之,量刑公正在當代已經不再局限在價值的層面上,而是提升到規范層面。為確保法官能夠公正量刑,量刑規范應該立足于責任主義原則建構出合理、正義的量刑基準,然后由法官根據這一量刑基準“計算”出基準刑,并將其作為宣告刑得出的“基準”(基準刑),之后法官在綜合運用各種量刑情節,在責任與預防的雙重考量之下,⑦責任和預防可以被視為犯罪預防的兩個不同側面,都服務于犯罪預防目的。得出最終的宣告刑。這樣,又延展出了量刑原理中的責任主義與量刑規則兩個基本維度,它們分別構成了現代量刑原理的內在體系與外在體系。
(責任編輯:杜小麗)
D F613
A
1005-9512(2014)02-0142-11
,《意見》和《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兩個規范性文件標志著量刑規范化在中國的初步建構,同時也在司法實踐中得以貫徹落實。那么,我國量刑規范化取得了何種效果呢?實踐效果是最好的例證。以大慶市法院系統的實踐為例,自2010年10月1日開始實施量刑規范化以來,不僅服判息訴率明顯上升,而且量刑規范化試行案件無一上訪。②參見《關于量刑規范化改革情況的報告》,《大慶日報》2011年11月14日。廣西壯族自治區15個中級人民法院、111個基層人民法院全部開展了量刑規范化改革試行工作。法院辦案質量、效率明顯提高,取得了“五升三降”的良好效果,即服判息訴率、調解撤訴率、退賠退贓率、當庭宣判率、當庭認罪率上升,上訴率、發改率、上訪率下降。③參見《廣西量刑規范化改革取得“五升三降”效果》,《法制日報》2011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人也指出,通過量刑規范化改革,量刑更加公正和均衡,刑事案件上訴率、抗訴率、上訪率普遍大幅度下降,辦案質量明顯提高;當庭認罪率、調解撤訴率、退贓退賠率、當庭宣判率和服判息訴率明顯上升,有利于促進調解,實現案結事了;量刑過程更加公開和透明,有效預防“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的發生,實現陽光審判、透明司法,促進公正廉潔辦案。④參見李娜:《3000余法院試行量刑規范化上訴抗訴變少服判增多》,《法制日報》2011年2月9日。在完備而合理的量刑規范下,法官量刑的過程不再是一個黑盒子,因為相關量刑因素業已根據責任主義原則具體化為條文,這有助于增加量刑裁判之透明性及合理性,矯正量刑失衡現象。
姜濤,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本文獲得“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PAPD)的資助,同時也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刑事政策制約刑法解釋的理論建構與制度實踐研究”(項目編號:13CFX045)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