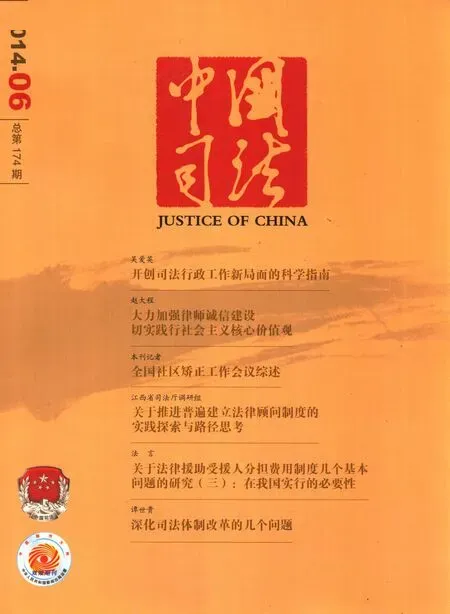論人民陪審員行使職權的獨立性
——以法律解釋主體論的缺失為視角
孔丁英(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論人民陪審員行使職權的獨立性
——以法律解釋主體論的缺失為視角
一、一種缺失:法律解釋主體中為什么沒有人民陪審員
(一)我國的法律解釋主體論及其缺失
傳統的法理學把法律解釋分為立法解釋、行政解釋、司法解釋、學理解釋,相應地,法律解釋主體分別是指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學者。還有一些觀點則認為法律解釋專指法官在裁判案件過程中對法律的理解和判斷。然而,不論如何理解法律解釋的主體,在現有的教科書、專著、論文中,都很少把人民陪審員放在法律解釋主體中進行研究。如果認為法律解釋學的研究宗旨是為司法活動提供適用法律的技術,那么與法官同樣有權決定法律適用的人民陪審員自然也值得研究。但現有的法律解釋學在談及解釋主體時完全忽略了人民陪審員的存在,不能不說是法律解釋主體理論的一大重要缺失。
(二)人民陪審員在法律解釋主體中缺位的原因
社會實踐的需求是推動科學研究進步的原動力。人們在研究法律解釋主體時不關注人民陪審員,正是由于當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效性不如人意,因而司法實踐缺乏將人民陪審員當作法律解釋主體來看待的現實需求。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公眾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認知程度不高,缺乏影響力。筆者所在法院曾在2011年的一次社會活動中隨機對89名普通民眾進行問卷調查,其中僅有17人知道我國有人民陪審員制度,占受訪人數的19.1%;在這17人中,大體了解人民陪審員作用與職責的僅有1人,其余16人聽說過人民陪審員,但不知道其具體的工作性質與內容;接受調查的其他62人表示沒有聽說過人民陪審員制度,占受訪人數的80.9%。這主要是因為人民陪審員制度長期虛置,沒有實際發揮作用。
2、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的獨立性不強,具有與法官趨同的傾向。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把人民陪審員納入法院的管理之下,由法院對人民陪審員進行任免、培訓、考核等管理工作,事實上把人民陪審員視為“編外法官”,并力圖使其與法官同質化。這樣一來,人民陪審員幾乎成了法院的一員,與法官形成了同事乃至上下級關系。“很多陪審員的主觀心態都是盡量聽從法官安排,‘不要給法院找麻煩’”①鐘莉:《價值·規則·實踐:人民陪審員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頁。。在這樣的氛圍下,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工作時缺乏獨立性,難以發表自己的法律見解。人民陪審員被要求與法官保持同質化,其行為方式、思維方式都在模仿法官。從法律解釋學的角度來說,似乎也就沒有必要把人民陪審員作為單獨的一類法律解釋主體來研究了。
3、人民陪審員并未深度參與審判工作,履行適用法律的職權不充分。人民陪審員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審判,取決于制度保障。我國對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的權利規定了一些保障措施,但都比較籠統,也不夠到位。首先,沒有明確人民陪審員庭前閱卷的程序,導致人民陪審員在開庭時因不熟悉案情無法提問,思路跟不上其他法官,進而在評議時也提不出自己的意見;其次,人民陪審員的參與并未影響合議庭的人數規模,所以人民陪審員參與的合議庭一般為2名法官、1名陪審員,或1名法官、2名陪審員,人民陪審員在合議庭中人數偏少、比例偏低,造成了人民陪審員在評議時面對職業法官的心理劣勢,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也難以充分發表出來,或者較容易被法官說服而改弦更張;再次,人民陪審員需要兼顧本職工作,參與審判的積極性和責任意識難以保障,“在實行陪審制度比較成熟的法院,也有10%左右的人民陪審員從未履行甚至拒絕履行自己的陪審職責”②祖鵬、李玉華主編:《人民陪審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為研究對象》,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頁。,深受詬病的“陪而不審”的情況仍然大量存在。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工作的程度不深,難以充分行使解釋和適用法律的職權,不能為法律解釋學提供研究的素材,于是,人民陪審員在法律解釋主體中的缺位也就不足為怪了。
二、一個比較:日本的裁判員怎樣影響法律解釋
(一)日本的裁判員制度與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
2004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了《關于裁判員參與刑事審判的法律》(簡稱《裁判員法》),確立以參審制為基礎、吸收部分陪審制要素的國民直接參與司法的裁判員制度,于2009年5月正式開始施行。至今,日本的裁判員已實施4年有余,受到各方面的積極評價。“裁判員制度實施以來,受到運營審判活動的職業法曹及參與審判的一般市民的肯定評價,可以認為裁判員制度已經穩固地建立并確定下來了”③〔日〕青木孝之:《刑事司法與裁判員制度》,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188頁。。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在較短的時期內就比較良好地運行了起來,可以說是通過外部導入的方式建立國民參審制度的成功范例。
日本文化(包括法律文化)與我國有很多相似之處,日本的裁判員制度與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同為參審制,在參與審判的具體方式上也具有較強的可比性。
(二)裁判員參與審判對刑法解釋和適用的影響
《裁判員法》明確規定了涉及法律解釋的判斷由合議庭中的法官決定。盡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學者和法官已經敏銳地意識到,裁判員作為普通市民參與審判,把市民的法律意識和價值觀念帶入審判過程,還是會悄悄地改變刑法解釋的機制和內容。
1、裁判員的參與可能改變刑法理論的體系和概念。在評議案件時,裁判員和法官一樣具有適用法律的權限,但涉及需要解釋的法律問題時,則由合議庭中的法官來作出判斷。但法官在作出法律解釋的判斷前,要聽取裁判員的意見,并且要對裁判員進行說明。如果裁判員對法官的解釋表示不理解或不接受,事實上評議就無法進行下去。這要求法律用語通俗化、易于裁判員理解和接受,以便法官和裁判員溝通和交換意見。
2、裁判員的參與可能改變刑法具體問題的判斷框架。例如,關于過失犯中的預見可能性,理論上有一般人標準說和行為人標準說的爭議,日本法院判例采用的是一般人標準說,由法官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以設想中的一般人為標準進行判斷。但在裁判員審判的案件中,“判斷這些標準的人本來就是‘一般人’,那就只要以自身為標準來判斷這些標準就可以了,這樣就有可能危及以一般人標準和行為人標準來區分違法性和責任的觀點存在的基礎”④〔日〕松澤伸:《關于機能的刑法解釋論方法的一考察》,《刑法雜志》第43卷第3號(2004年3月)。。本來是客觀性的判斷,有可能變成裁判員以自身為標準的主觀性判斷,這就大為改變了判斷框架的性質。
3、裁判員的參與可能改變刑事裁判文書的說理方式。日本的裁判員在作出裁判時也要像法官一樣闡述理由。但與職業法官在長期的“精密司法”之下訓練出來的細致相比,裁判員的說理多多少少存在邏輯跳躍甚至前后矛盾的情況。為了避免粗線條適用刑法的情況,最高法院頒布了裁判員參與審判案件的刑事判決書范例,要求在判決書中詳細列舉控辯雙方的主張和理由,并逐一作出評價。
4、裁判員的參與可能改變法官的“量刑行情”。經過長期的司法實踐,日本法官對各種類型案件的量刑已經形成了許多根深蒂固的習慣和傳統,這在實務中被稱為“量刑行情”。長年從事刑事審判的職業法官對刑罰的感覺和初次接觸刑事案件的裁判員當然是不一樣,裁判員的參與肯定會改變過去的“量刑行情”。為避免“量刑行情”大幅波動,日本最高法院要求法官在審判開始前向裁判員說明量刑的原理和步驟,提示裁判員注意針對量刑事實開展法庭調查,在評議時由法官逐條列出控辯雙方的量刑主張和應考慮的因素,由法官引導裁判員逐條進行討論和評判,并將結論和理由盡可能詳細地寫入判決書⑤〔日〕青木孝之:《刑事司法改革與裁判員制度》,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188頁。。
(三)對我國的啟示
日本是怎么做到使裁判員制度充分活躍起來的呢?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從立法設計和實務操作上切實地保障裁判員獨立行使職權、獨立發表意見。其中有幾點值得借鑒:
1、在立法及實施法律前進行充分的討論和準備工作。《裁判員法》在通過前已經經過充分的討論,在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上達成高度共識,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裁判員法》還在附則中規定了5年的準備期(即2009年5月正式實施)以及要做的工作,通過廣泛宣傳、深入調研、組織模擬審判等方式,一方面讓國民了解裁判員制度,做好擔任裁判員的心理準備,另一方面也為裁判員制度的正式實施收集意見、積累經驗。在2009年3月,《裁判員法》即將正式實施前,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相當于我國的國務院辦公廳)開展了全國規模的民意調查,在接受調查的3萬多人中,有97.4%表示知道有裁判員制度,僅有2.6%的人不知道裁判員制度的存在;在問到“如果知道自己被選為裁判員會如何對待”時,13.6%的人回答“很樂意去做”,57.9%的人回答“既然是義務,就盡可能去做”,25.9%的人回答“不想做”,2.6%的人回答“不知道”。這說明經過5年的宣傳動員,在還沒有正式實施的情況下,裁判員制度在民間的認知程度就已經非常高,大部分民眾對擔任裁判員有一定心理準備,為制度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在制度設計上建立詳細周密的保障措施。日本《裁判員法》遠比我國的同類規定詳盡,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僅有20條,共1690余字,而日本《裁判員法》則有8章,正文113條,附則28條,共37700余字(日文字數),為了保障裁判員獨立地、實質性地參與審判程序,詳細周到地規定了許多保障措施。例如該法第49條要求裁判員必須參加庭前準備程序,就很受好評。我國《刑事訴訟法》在2012年修改時同時規定了案卷移送和庭前會議制度,但沒有要求人民陪審員在開庭前閱卷,也沒有明確人民陪審員是否參加庭前會議,立法上考慮不夠周到。
3、在司法審判實務中最大限度地尊重裁判員的法律解釋。法院是直接負責實施裁判員制度的機關,如果不能得到法官的理解和支持,裁判員制度就無法真正實施。日本的法官不但普遍支持通過引入裁判員來改善刑事審判,而且對裁判員制度的宗旨和理念表示出了極大的尊重。“法官在決定法律解釋時必須聽取裁判員的意見,并且要向裁判員詳細說明解釋結論,如果裁判員不理解或不接受法官的解釋,評議事實上就無法進行下去”⑥〔日〕平良木登規男:《裁判員審判中的評決》,《法學研究》第84卷第9號(2011年9月)。。法官以簡明易懂的方式解釋法律,致力于使法律解釋能夠被多數裁判員所理解和接受。這樣一來,不但裁判員獨立發表法律意見的權利得到了保障,而且法官對法律的解釋也在潛移默化之中被改變了。
三、一條路徑:人民陪審員怎樣獲得法律解釋主體地位
相對而言,我國對人民陪審員在參與審判過程中的獨立地位保障不夠充分,因而人民陪審員的參與對司法實踐解釋和適用法律的影響不大,我國的法律解釋學也不關注人民陪審員對法律解釋的影響。人民陪審員制度已存在多年,但在社會上缺乏影響力,不為群眾所知曉,原因也正在于此。
毋庸諱言,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需要繼續進行改革。但是,在短期內對人民陪審員實行根本性的變革也不現實。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先在現有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圍繞強化人民陪審員的獨立地位,使人民陪審員的意見能對法官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進行一些帶有改革性質的探索:
(一)保障人民陪審員開庭前熟悉案情,盡早進入工作狀態
改變當前人民陪審員在庭審時才接觸案件的做法,建立人民陪審員庭前閱卷制度,開庭前召集庭前會議或證據交換的,應通知人民陪審員參加,以便人民陪審員盡快了解案情,進入工作狀態,避免因不熟悉案情而無法有效參與庭審和評議。為了保證人民陪審員有充分的庭前準備時間,需要修改在開庭七日前確定人民陪審員的規定,應規定在確定合議庭組成人員的時候一并確定人民陪審員。
(二)增加人民陪審員在合議庭中的人數,強化人民陪審員的評議優勢
改變當前人民陪審員在合議庭中人數偏少的格局,應保證人民陪審員對職業法官的絕對人數優勢,使法官不能輕易影響人民陪審員發表意見的獨立性。具體人數可參照日本《裁判員法》的規定,原則上由3名法官、6名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對于事實清楚、控辯雙方無爭議的案件,可以由1名法官、4名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同時,為保證有足夠的人民陪審員可以供選擇,不至于給人民陪審員造成過大負擔,應適當增加人民陪審員的員額。
(三)加強人民陪審員在審判決策機制中的地位,尊重其獨立發表的意見
我國法院內部的審判決策機制比較復雜,在合議庭之上還有審判委員會,有些法院還有庭務會和審判長聯席會可能介入審判決策過程。按照《關于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若干問題的規定》,人民陪審員和法官意見不一致的,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這基本維持了以審判委員會為法院內部最高審判決策機構的體制。但是,如果認為人民陪審員是人民代表,那么審判委員會何以能夠否定人民代表的意見,其依據有待商榷。當然,如果規定審判委員會不能否定人民陪審員的意見,也不盡合理。可以考慮折衷的做法,讓人民陪審員列席審判委員會,發表意見并參與討論,這不僅是對人民陪審員獨立地位的尊重,而且也讓審判委員會委員有機會與人民陪審員直接對話,這種當面接觸或許會影響一些委員的意見選擇。
(四)端正對人民陪審員制度宗旨的認識,改變不利于人民陪審員獨立履行職責的做法
不可否認,當前一些法院和法官對人民陪審員制度宗旨的認識并不到位,由此在實踐中滋生出許多不利于人民陪審員獨立履行職責的做法。例如有些法院選任的是專職在法院上班、由法院發放工資的全日制陪審員,有些法院給人民陪審配備統一的徽章、制服等等,這些做法客觀上加強了人民陪審員對法院的歸屬感,相應地削弱了人民陪審員作為“國民規范意識”代表的地位和履行職責的獨立性,扭曲了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理念,這些做法都應該予以擯棄。
在現行制度下,人民陪審員由法院政工部門管理,這在事實上使人民陪審員成為法官的同事、法院領導的下屬,不利于人民陪審員獨立履行職責。既然人民陪審員是由人大常委會任命,就應該由人大常委會設立管理人民陪審員的專門機構,負責對人民陪審員的資格審查、職務任免、日常管理、培訓、考核、監督等工作,對人民陪審員工作中發現的重大問題采取跟蹤機制和督辦措施,從外部監督保障人民陪審員在法院獨立履行職責。
獨立履行職責的地位得到保障,人民陪審員才能真正參與到法律解釋和適用過程中,實現通過吸收群眾法律意識改善司法審判的目的。人民陪審員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解釋和適用法律,是檢驗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否具有實效性的一桿標尺。
(見習編輯 朱騰飛)
數據庫
2013年全國法律援助工作統計分析(一)
截至2013年底,全國法律援助管理機構數為431個,法律援助機構數為3249個,其中行政性質機構和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分別為1544個和633個,這兩類機構占機構總數的67%;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不含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1010個,占機構總數的31.1%。全國業務經費納入財政預算機構數為2922個,占機構總數的89.9%,有專門接待場所機構數為3041個,其中臨街一層機構數為2196個,占機構總數的67.6%,增長了15.9%,東,中、西部法律援助機構建設情況存在一定差異。
全國共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65069個,比2012年增長2.1%,其中依托司法所設立工作站38901個,在工、青、婦、老、殘,信訪、高校、監獄等設立工作站25485個,在看守所設立工作站833個。
全國法律援助管理機構和法律援助機構工作人員共有14548人,編制數為12991人,同比均略有增長。其中女性工作人員為6483人,占44.6%。法律專業工作人員共有11343人,占總人數的78%;具有本科和研究生以上學歷工作人員分別為10681人和834人,分別占總人數的73.4%和5.7%,法律援助機構中具有法律職業資格或律師資格的工作人員數為6414人,法律援助注冊律師數為4813人,與2012年相比均有所上升。各地電臺,電視臺播出法律援助節目共計77362次,同比增長138.2%;互聯網刊登涉及法律援助的信息16490篇;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法律援助機構共舉辦法律援助培訓班9259個,培訓人數301116人次,培訓總學時5629933小時;受到省部級以上表彰的機構和個人分別為959個和1093個,宣傳、培訓和表彰力度進一步加大。
(來源: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