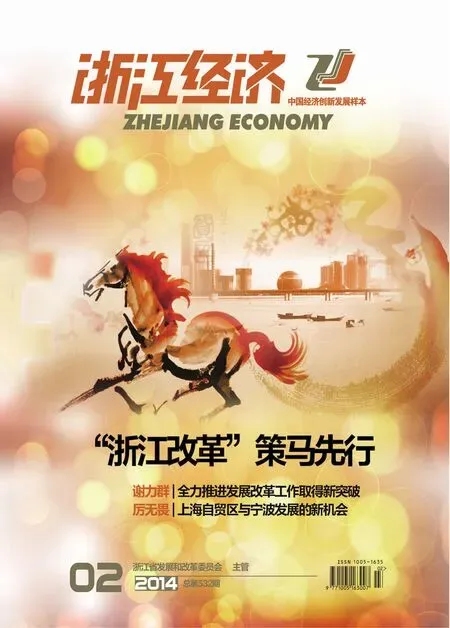加快推進進城農民市民化
王祖強
作者為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軟科學研究所所長,浙江省“科學發展觀與浙江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這一重要論述,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流轉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當前,農民進城的意愿下降是制約浙江新型城市化發展的新矛盾、新問題,目前尚缺乏簡單明了的一攬子解決方案。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傳統農村集體產權局限于農村內部(村域或鄉域)的狹窄范圍,及其封閉、分割、固化、散亂和低效的狀態,市場機制在促進農村資產交易、變現和保值增值上運行不暢,發揮的作用不大。交易權是一種十分重要的財產權益,農村農民依然十分缺乏,對進城農民尤其珍貴和迫切。因此,亟需用新的改革思維聯動推進戶籍制度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宅基地使用權制度改革,滿足進城農民在戶籍關系脫離后對集體資產的利益訴求,為農民進城注入新的動力。
農村各種集體資產權益因其與農民戶籍身份結合固化在一起,成為進城農民的主要牽掛和“農轉非”積極性明顯下降的經濟誘因
當前,浙江推進新型城市化遇到一大矛盾與困難,就是進城農民“農轉非”的積極性明顯下降,大量轉居、轉業到城鎮的農戶、大中專在讀學生等拒絕將戶口遷移到工作或學習所在地。2012年,浙江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達到63.2%,已經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城鎮戶籍人口比重僅為32.0%,相差近31.2個百分點,相當于1900萬進城農民沒有真正成為市民。新世紀初期,浙江每年農轉非人口還能保持在35萬人左右,但到2012年浙江農轉非人口下降到不足16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調查顯示,74%的農村戶籍流動人口愿意在城市長期居住,但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即使是較富有的以從事非農產業為主、有較穩定收入來源的農民,通常也不愿意放棄農村土地,即使長期定居城鎮,也沒有將戶口遷入城鎮,成為了典型的“兩棲人口”,形成了對城市和農村土地的雙重占用。
這就造成了嚴重的經濟社會悖論:一方面,農村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大量閑置,而城市化和工業化用地供應嚴重短缺;另一方面,農村集體資產大量固化閑置、不能變現增值,而農村發展資金與農民進城的能力嚴重不足。究其原因是農民擁有的集體資產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的權益十分巨大,例如義烏市、瑞安市、蕭山區和鄞州區等近郊農民的人均集體資產(土地)權益在100萬元-300萬元之間,各種集體資產權益又與農民的戶籍身份結合固化在一起,成為進城農民的主要牽掛和非轉農“逆城市化”的經濟誘因。
雖然現在農村的建制變了,農民的身份變了,居住的方式變了,但農村集體資產的產權制度與管理模式依然如故,成為制約進城農民市民化的一大遺留問題。進城農民對村級集體資產管理、權益維護不放心,怕集體資產流失、被平調、被侵占,影響到農村社會發展和穩定,也阻礙了行政村向城市社區的轉型,阻礙了現代城市的發展。農村集體資產(經營性資產和公益性資產)所有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等是農民的基本權益,無論他們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鎮,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們的合法財產權。但戶籍與村集體資產所有權相互聯結,使社會資源固化在農村,容易出現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板結現象。
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是進城農民重要的改革訴求,是一項富裕農民、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惠民工程
在推進農村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聯動改革方面,無論是浙江嘉興“兩分兩換”和溫州“三分三改”,還是江蘇“三集中、三置換”和廣東“雙轉移戰略”,本質上都是以“分”促“換”的破解思路,借助于制度創新實現農民身份與各種集體權益的分離,打破農民戶籍、身份與各種集體資產權益緊密結合固化的狀態,在此基礎上,通過擴大市場交易和流轉范圍,逐步逐項打破傳統固化了的個體社會身份界限,為發揮市場在農民市民化中的基礎性作用創造制度環境。
當前浙江各地正在進行的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初步打破了農村集體產權模糊、封閉、散亂和低效的狀態,但因商品化、市場化程度不夠,依然缺乏交易、流轉和變現增值的能力。因此,要允許股權繼承、轉讓,疏通股權流轉和交易渠道。農村股權交易流轉的范圍越大,越有利于農村經營性資產保值增值,對于有可能導致的股權集中,不要有太多顧慮,自愿、自主的交易,在更廣闊的社會平臺上的交易,具有更好的價值發現功能,更有利于農村資產交易變現、保值增值和實現共同富裕。目的是要在等價交換基礎上實現農村生產關系的革新,實現農村土地與勞動力、資產權益與戶籍身份的分離,創造出新型生產關系。
新型城市化不僅包括農民就業和居住的城市化,還包括農民宅基地使用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集體資產所有權和農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商品化、市場化。進城農民的核心利益訴求是,將全部經營性資產、土地等資源性資產和公益性資產折股量化到人,在此基礎上,推動農村資源資產化、商品化和證券化,擴大交易流轉范圍,通過市場交易實現資產變現和保值增值。
建立進城農民宅基地退出機制,擴大宅基地使用權交易轉讓的范圍,幫助進城農民實現宅基地使用權交易變現增值
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民的一項重要的財產所有權。建立進城農民宅基地退出機制,這是新型城市化最為艱巨的制度創新重任之一。對農民而言,住房是其最大的資產,如果農村宅基地和住房可以交易變現增值,舉家外出的農民可能通過轉讓變現而籌集一部分進城長期居住的資金,從而增強農民市民化的能力。對城市發展而言,宅基地的流轉可以提供城市發展最緊缺的土地資源。
把農村宅基地使用權交易流轉局限于農村內部(村或鄉鎮)的狹窄范圍,十分不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需要從理論準備到制度設計兩方面入手,幫助進城農民實現宅基地使用權交易變現增值。當前浙江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最大的亮點在于允許農村房屋所有權的交易,邁出了把農房的抵押和置換范圍擴大到縣域的重要一步。盡管政策并未突破紅線,農房交易范圍仍限于本村,但在縣域范圍的抵押貸款和置換交易功能依然實現了農房價值的重估,為農房擴大交易范圍打開了突破口。從禁止宅基地租賃、買賣,到允許其在本鄉鎮出讓、買賣,再到允許其在縣域范圍抵押和置換,這無疑是農村土地市場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進步。政策藩籬正在一步步被突破,交易范圍正在不斷擴大。
農村宅基地交易流轉宜疏不宜堵。應制定宅基地流轉制度,依法準許宅基地入市,建立合理規范的農村宅基地流轉平臺和渠道,打破城鄉二元分割的土地利用機制。宅基地與戶籍農民所享有的各項福利掛鉤的,這是宅基地難以順利流轉的核心。要逐步實現宅基地與農民的身份福利的分離,非集體內成員、非農人員不能因為購買宅地基就享有集體經濟組織的福利待遇。要通過交易流轉讓農村宅基地隨著農民進城而減少。
率先在浙江農村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和新型財產權利關系,使農村的集體資產、集體土地和成員向社會資產、社會土地和社會人轉變
農村集體股權交易流轉有望成為新一輪改革的重點。結合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以及李克強總理在常熟市家庭農場調研講話的內容看,種種跡象表明中央對此持開放態度。農村股權流轉問題不僅涉及到產權能否交易、轉讓和繼承,而且涉及到進城農民戶籍關系脫離所在集體時能否帶走自己的合法財產。集體資產股權的流轉性關系到集體成員投資入股的積極性和農村經濟的長遠發展。因此,應積極搭建縣級乃至省級集體股權交易平臺,培育集體經濟股權交易市場,逐步突破農村集體股權的地緣性、封閉性和福利性限制,通過市場交易在農村建立新的財產權利關系。
農村集體產權很有可能一躍變身為活躍的資產,給城市化注入新能量。只有使集體屬性人轉變成社會自然人,進城農民市民化問題才能得以解決。具體來說,農村集體經濟要從根本上實現“五個轉變”:(1)從傳統集體產權制度向現代產權制度轉變;(2)從封閉、固化的產權形式向開放型、可交易的產權形式轉變;(3)從單一的土地和物業租賃經濟業態向綜合型經濟業態轉變;(4)從股份經濟合作社向公司制、集團型股份企業轉變;(5)從依賴集體分紅的農民向享受城市社會保障并承擔資產經營風險的股民和社會人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