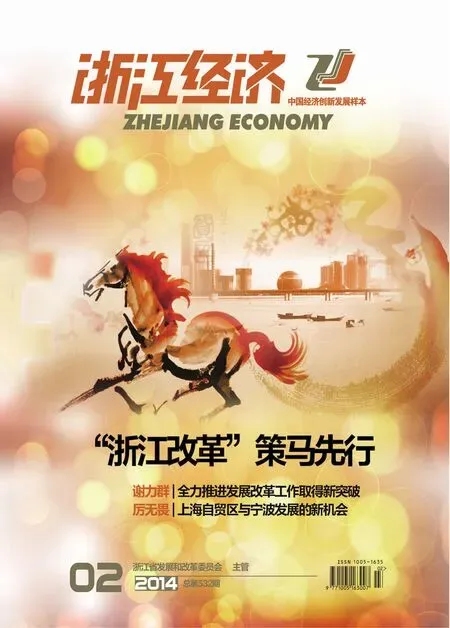稅源之爭:誰動了誰的奶酪?
王義偉
在分稅制的激勵下,區域與區域競爭,招商引資在很多區、縣(市)都是“一把手”工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與企業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兩股力量交互作用,有些企業去了勞動力更相宜的中西部,有些企業去了空間資源相對豐富的近郊,更多的企業扎根本地發展壯大。近年來,有些企業不是遷往城外卻在城區間遷移,原因是什么,如何解決?
分稅制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激勵各地優化投資環境,筑巢引鳳,另一方面各城區競相出臺各類優惠政策招商引資,互挖墻角,導致稅源在主城區之間無序轉移,并引發一系列矛盾。遷出區通常設置重重障礙或對企業注銷登記等事項拖著不辦,不予放行。遷入區通常已經兌現部分優惠政策,希望企業盡快在所在地開票納稅。企業通常已經投入巨資建成新廠區,希望轉出區政府和轉入區政府盡快解決矛盾,以免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基層對此抱怨頗多,希望市級層面出臺政策予以協調。
眾所周知,蕭山區、余杭區撤市設區以來財政仍由省直管,而主城區有市、區兩級財政。蕭山、余杭擁有相對豐富的空間資源,同時背靠主城區,可以借助主城區的科技、教育、醫療、交通等功能,從而成為投資洼地,部分稅源趨之若鶩,淘寶就是其中一例。這種稅源轉移肥了蕭山、余杭,瘦了主城區市、區兩級的稅基。
基于此,有以下集中解決方案:一是聽之任之。現在好多企業是“電腦+人腦”的輕資產公司,企業搬遷費用很低,如果聽任“挖墻角”行為發生,各城區為了爭奪稅源,對于“產蛋多”的好公司,將拼命使用稅收優惠、稅式支出、財政獎勵等手段,最終結果是稅收流失,“產蛋多”的好公司與“產蛋少”的普通公司對當地的稅收貢獻趨同。稅收在競爭中流失,稀缺的空間資源浪費。二是一律禁止。有些城區在培育企業上有優勢,但空間資源匱乏,當企業發展壯大到一定階段,需要通過擴大規模來做強做大,當地政府滿足不了企業的用地需求,又禁止企業異地擴張,企業發展怎么辦?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企業可能“離家出走”。所以,一律禁止這個方案不符合企業成長規律。三是稅收分成。這個方案的要點是在一定期限內(比方說5年)遷入區與遷出區進行稅收分成,通過分成降低遷入區預期收益,補償遷出區前期投入與付出。這對遷出區和遷入區都比較公平,轉出區把企業培育壯大,到了產蛋的時候分一些雞蛋,合情合理。而且,稅收分成比例和分成期限均可以調校,遷入區和遷出區容易找到利益平衡點。稅收分成比例和期限設計,應以最有利于企業成長壯大為依歸,如此市本級稅收所得才能最大化。
在同樣的招商政策下,由于本地企業在城區之間遷移費用相較于外埠企業為低,從而本地企業在城區內部意愿遷移較高,遷往其它地區的意愿較低。在同樣質地的企業中,遷入區能以較低的優惠政策覆蓋本地企業的遷移費用,凈收益較高,從而更青睞本地企業。但從全市角度來看,外埠企業能帶來更高的稅收,但并不是遷入區的最優選擇,寶貴的空間資源用在了相對低效的本地企業上,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除空間要素外,科技要素重要性與日俱增,為了保護各地科技創新投入的積極性,需要把外遷企業的一部分稅收貢獻界定給遷出區。兩種財政體制困擾,需要從市區一體化戰略高度來統籌解決。據此,筆者提出三條建議:
一是制定出臺協調政策。在遵守統一的稅收政策的前提下,針對遷徙企業制定區與區之間稅收分成指導政策。即遷徙企業盡管在遷入區開票納稅,但區級財政所得部分由遷出區和遷入區分享,稅收分成比例和分成年限應有一定彈性。協調政策要堅持“抓大放小”原則,對納稅額超過某一標準的企業遷移才適用該政策,對于納稅額比較小的企業應采取放水養魚策略,任其自由移動。
二是進一步明確主要區塊功能定位。加強規劃引導,增強三大規劃之間相互協調與配合,進一步明確主要區塊功能定位,形成定位清晰、分工明確、相互協同、創新驅動的空間發展格局。堅持市級主導、區級主體,進一步優化專屬基礎設施配置,加強軟、硬環境建設,打造主導產業特定集聚平臺,培育、吸引稅源,擴大稅基,最大限度避免內耗。
三是統籌推進市區一體化。堅持經濟社會一體化方針,向省里爭取兩區財政下劃至市里,統一市區社會保障標準,統籌推進蕭山、余杭全面融入市區,實現一體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