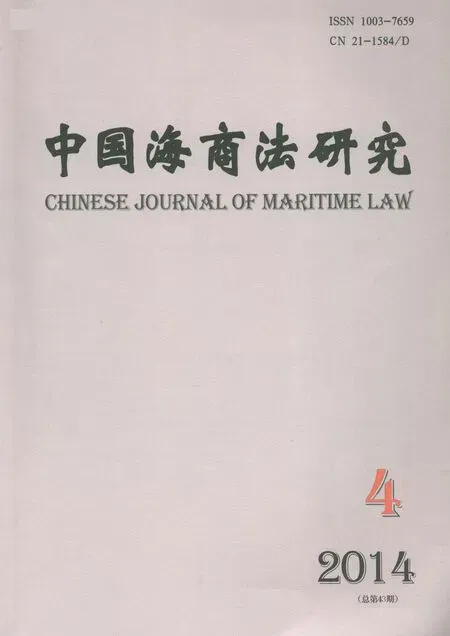船員勞務豈是“個人勞務”?
——兼論《侵權責任法》第35條在海事審判中的適用限制①
吳勝順
(寧波海事法院 溫州法庭,浙江 溫州 325088)
船員是高風險職業。船舶在海上從事運輸、捕撈等生產作業,難免發生船員傷亡事故。船員在船工作因執行職務遭受人身損害(簡稱船員勞務人身損害),用人單位或者說雇主應承擔賠償責任,在這一點上,無論從工傷保險角度,還是從民事侵權責任角度,已經成為一種基本概念或共識。即便在侵權責任立法缺位時期,船東對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承擔無過錯責任,在審判實踐中就無太多分歧,唯在法律援引上略顯欠缺而已。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解釋》)頒布實施后,上述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然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簡稱《侵權責任法》)的施行,不是問題的問題卻又成了問題——該法第35條規定:“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而且,在解釋和適用上,認為該條規定已經取代了《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即:雇員因執行職務行為自身遭受損害的,雇主承擔過錯責任而非無過錯責任。[1]259海上人身損害責任糾紛是傳統的海事糾紛,而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更是占據其中的大部分。審理此類案件,是適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第1款規定按無過錯責任處理,還是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按過錯責任分擔,或者另找出路,在實踐和認識方面又陷入了混亂。歸責原則是侵權責任的核心問題,決定著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當事人舉證責任負擔、免責條件,以及案件事實查明、法律適用和實體處理結果,必須在認識上加以澄清,在實踐中予以統一。筆者擬從海事審判實務出發,對此作些探討。
一、海事審判實踐中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歸責原則及其法律適用
(一)《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實施之前
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普遍被定性為工傷事故致害,船東承擔工傷事故賠償責任。救濟方式主要有兩種,分別適用于不同情形:一是工傷保險賠償途徑,以工傷認定和勞動仲裁為前置程序,應當參加而未參加工傷保險的,由用人單位按工傷保險待遇支付費用;二是徑行訴訟途徑,即不經工傷認定,直接向海事法院提起訴訟以解決糾紛。船東賠償責任風險,則可通過工傷保險或商業責任保險分攤。但是工傷保險對象有所限制,覆蓋面仍顯不足,不符合條件的,受害人還是要通過訴訟途徑尋求救濟,而商業責任保險不過是將船東賠償責任轉嫁給了保險人而已。
工傷保險賠償采用無過錯責任,是中國勞動、社會保障立法一貫采取的原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稱《民法通則》)實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復的方式明確雇主對雇工應承擔工傷事故賠償責任*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雇工合同“工傷概不負責”是否有效的批復》(1988年10月14日[88]民他字第1號)。。《人身損害賠償解釋》施行前,海事法院審理船員勞務人身損害侵權糾紛,一般也都解釋為工傷事故致害,認為相關法律法規規定雇主應對雇員承擔賠償責任,進而適用《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無過錯責任的規定;船員存在明顯、重大過錯的,同時適用過失相抵原則,按《民法通則》第131條減輕船東責任。下面這個案例就是如此:黃賢民受雇于某對拖漁輪所有人范忠水等八人,自2002年4月份起在漁輪上任廚工。至禁漁期,漁輪停泊在船廠修理,由黃賢民留船看管。同年9月1日清早,黃賢民被發現已死亡在該對漁輪與里舷的船舶之間,具體死亡原因和時間不明。黃賢民遺屬訴請范忠水等人賠償損失近14萬元。范忠水等人辯稱其無過錯,不承擔責任。海事法院經審理認為,黃賢民與各被告之間構成雇傭關系。黃賢民在受雇期間,被發現因不明原因死亡在所看管的漁輪周圍灘涂上,各被告作為雇主應根據《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規定承擔賠償責任。但黃賢民在事故當晚,擅離工作崗位,外出喝酒至深夜,對自身生命安全疏于注意義務,有明顯過錯,根據《民法通則》第131條的規定,可相應減輕雇主的民事責任*參見寧波海事法院(2002)甬海溫初字第147號、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3)浙民三終字第10號。。
(二)《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實施之后至《侵權責任法》實施之前
就雇傭關系下雇員因職務行為遭受人身損害,《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和第2條明確了兩個問題:一是雇主承擔無過錯責任;二是無過錯責任可并用過失相抵原則,但僅限于受害人故意或重大過失。《人身損害賠償解釋》是對審判中如何適用法律作出的司法解釋,并未創設當事人新的權利義務。換言之,司法解釋中上述兩個條款既是對審判實踐的提煉,也是對實務爭議的回應,與中國勞動、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一脈相承,可謂殊途同歸。該司法解釋施行后,海事法院審理船員勞務人身損害侵權糾紛,無不依《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第1款和《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的規定,由船東承擔無過錯責任;船員存在重大過失的,并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2條,減輕船東責任。舉個該時期的案例:陳華富受雇在林存造等四人實際所有的漁輪上工作。2006年11月13日,在捕撈作業中,陳華富雙腿被網繩絞傷,經鑒定,分別構成9級和10級傷殘。陳華富訴請林存造等四人賠償損失近20萬元。林存造等人辯稱陳華富故意違反勞動紀律釀成事故,不承擔賠償責任。海事法院經審理認為,依《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第1款,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賠償,根據《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由林存造等人承擔責任。陳華富雖在事故發生前里朝外穿著雨衣以及未將雨衣打結,致網繩纏住雨衣繼而絞傷雙腿,但林存造等人未舉證證明其在雇傭前,已經核實雇員是否具備海上捕撈技能,或者進行必要的技能和安全培訓,也未舉證在事故發生前,已提醒或者制止陳華富反穿雨衣。陳華富自我保護意識不強,尚不足以達到《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2條第2款“重大過失”的程度,不減輕雇主賠償責任*參見寧波海事法院(2007)甬海法溫事初字第5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8)浙民三終字第27號民事判決書。。
(三)《侵權責任法》實施之后
至《侵權責任法》施行時為止,船東對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承擔無過借責任,在理論、認識上漸趨一致,審判實踐中不再分歧,且已經司法解釋統一了法律適用。然而,這種統一卻因為《侵權責任法》第35條的規定而不復存在。以下案例就是一個明證:陸海波受廣西某船務公司雇傭在“昌華油1”輪任二管輪。2011年1月4日陸海波在檢修機艙鍋爐時,左手被排風機吸進擠壓受傷,經鑒定構成八級傷殘。陸海波訴請船務公司賠償損失40多萬元。船務公司辯稱,陸海波違反維修規程,造成安全生產事故,屬于提供勞務一方致本人損害,應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規定,按過錯程度由陸海波承擔相應責任。海事法院一審認為,陸海波與船務公司之間構成勞務關系,依《侵權責任法》第35條規定,應在分清過錯的前提下確定雙方責任。船務公司有關陸海波違規操作存在重大過錯的抗辯,證據和理由不足;船務公司事先未制定詳細的船舶設備維修程序,在排風機打開并運行的情況下僅留一人進行觀察,明顯存在過錯。陸海波系在從事勞務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船務公司作為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宣判后,船務公司上訴稱,一審未依照《侵權責任法》第35條規定由雙方依過錯分擔責任不當。二審認為,陸海波在輪機長指示下檢修鍋爐,操作方式雖無明顯不當,但其在操作中未盡必要安全注意義務,對造成自身損傷有一定過錯。根據雙方過錯程度,改判由陸海波自負20%責任*參見寧波海事法院(2011)甬海法事初字第35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浙海終字第123號民事判決書。。
上述三個案例有若干共同點:一是作為被告一方的船東和雇主,均在訴訟中抗辯受害人自身存在過錯,并要求免除或者減輕賠償責任;二是船員對自身損害或多或少存在過失,至少事故發生與其疏忽大意、防護意識不強相關;三是受害人均系在執行職務行為中遭受人身損害。同時,也有不同之處:一是在前兩個案例中,雇主一方系個人合伙,而第三個案例所涉單位為法人企業;二是從受害人一方的過錯程度看,第一個案例最重,第二個案例次之,而第三個案例除類型糾紛中普遍存在的受害人自身未盡必要安全注意義務外,并無具體過錯行為。三個案例,分別發生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實施之前、《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實施之后至《侵權責任法》實施之前、《侵權責任法》實施之后,各代表了不同時期審判實踐對同一類型糾紛的歸責原則態度和法律適用取向。
比較題引三個案例,第三個案例在歸責原則和法律適用上是顛覆性的:船東要求根據《侵權責任法》第35條由雙方分擔責任;一審適用該條后段規定,但又判決船東承擔全部責任,有“引而不用”的意味,審判理念上似仍堅持無過錯責任;二審不僅肯定了《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的適用,還對受害人科以非常苛刻的過錯責任。更為嚴重的是,《侵權責任法》實施后,船東對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按何種歸責原則以及如何適用法律,并非如立法者所愿從一種統一走向另一種統一,更非從無法可依回歸有法可依,而是各行其道。大致有以下幾種作法:仍依《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第1款規定按無過錯責任處理*參見北海海事法院(2011)北海事初字第18號民事判決書。;[2]依《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按過錯責任處理;區分主體,船舶為個人所有或共有的,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否則適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其中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的,舉證負擔上也存在兩種不同作法:嚴格按過錯責任,由雙方各自舉證并分清過失程度;適用過錯推定,由船東對船員過錯承擔舉證責任*查閱寧波海事法院2011年之后的生效判決書,上述幾種作法均存在。。
二、《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及其法律適用爭議
如前所述,導致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歸責原則和法律適用重陷混亂的根源,在于《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但是,問題在于,此種混亂到底是立法本身反復所致,還是法律適用解釋不恰當所致,或者兼而有之?
(一)從《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到《侵權責任法》第35條
雇員因職務行為遭受人身損害,通過工傷保險賠償或徑行訴訟解決,屬于不同的救濟途徑,且分別適用于不同情形。進而言之,二者不僅賠償途徑、方式、程序不同,而且在實體法上,前者適用勞動、社會保障法律,后者適用民事法律,分屬不同的部門法。雇員徑行對雇主提起民事賠償訴訟,混合適用工傷保險法律和《民法通則》,略顯牽強。這也是海事審判一般不直接引用工傷保險法律的原因之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實施前,海上人身損害糾紛均參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與工傷保險賠償,在定殘標準和賠償待遇上,均存差異。。《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較好地彌合了該類糾紛在《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適用上的缺失,并以第2條第2款明確可并用過失相抵,矯正無過失責任絕對化。從《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的無過錯責任到《侵權責任法》的過錯責任,這期間,中國社會保障機制越來越健全,對勞動者人身權益保護也越來越強,立法自無反其道而行的道理,也沒有理由制定與勞動、社會保障法律基本原則相沖突的侵權責任法。
從《侵權責任法》第35條的立法背景中,也許更能夠窺出些許端倪。《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實施后,對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家政服務領域的侵權糾紛,比如保姆、家庭裝修工人遭受人身損害等,在司法實踐中被解釋為雇傭關系,按無過錯責任處理,由此引起了熱議。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雇主與雇員之間并無支配與被支配的隸屬關系,一概按雇傭關系適用無過錯責任,對雇主不公平。[1]257,[3]此為其一。其二,《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過程中,至第二次審議稿,尚無第35條內容。第35條是第三次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時才加上去的,原因也正是為了回應上述社會熱議*參見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柏林2009年12月22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所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由此不難看出,第一,《侵權責任法》第35條之所以如此規定,主要是針對諸如保姆、家庭裝修之類的家政服務領域,初衷是矯正而非全盤否定《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第二,該條在最后一次審議稿中才加上,并未如其他大部分條文那樣經過詳細論證和討論,與其他部門法(如勞動、社會保障法律)以及現行司法解釋、審判實踐存在脫節現象,或者出現法律漏洞,雖非立法者所愿,但僅就立法技術和過程而言,并不意外*《侵權責任法(草案)》第三稿于2009年11月6日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該稿第35條與后來生效的《侵權責任法》一致。同年12月22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時,也僅提到第34條和第35條的追償問題,而未涉及第35條后段有無不同意見。。
(二)對《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的各種解讀
《侵權責任法》施行過程中,理論和實務對第35條的解釋和適用,給出了各種不同意見。
1.學者意見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梁慧星教授和楊立新教授的看法。《侵權責任法》通過后,梁慧星教授在多個場合演講時都指出,第35條最后一句是該法兩處主要不足之一。梁慧星教授認為:“第35條規定個人之間的使用關系,被使用人在執行職務當中自身受到損害的按照自身的過錯來承擔,此規定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勞動者執行公務的過程中受工傷受殘疾有勞動保險,絕對不能按照侵權責任法當中的過失相抵來進行過失分擔。……此項規定不公正,也違反勞動法的規定,違背社會保險法的規定。……對于勞動者受傷的情形,我們就要把勞動法的規定、社會保險法的規定解釋為本法第5條所說的‘其它法律另有規定’,直接適用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的規定而不適用第35條最后一句的規定來回避并補救此錯誤。”[4]而楊立新教授則認為,該條不應該規定在《侵權責任法》中。[5]
2.實務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侵權責任法研究小組在《侵權責任法》通過后第一時間編寫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一書,明確指出:“本條(第35條)還規定,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致使自己受到傷害的,適用過錯責任,即根據提供勞務一方和接受勞務一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并認為,“本法實質上是以‘提供勞務一方’、‘接受勞務一方’、‘勞務’、‘勞務關系’等術語分別取代了‘雇員’、‘雇主’、‘雇傭’、‘雇傭關系’等術語,在中國立法及司法實踐中,二者的含義其實是相通的。”該書還進一步提出:“實際上,本條(第35條)已經取代了《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十一條規定的內容,在今后的審判實踐中如遇到此類問題,應依據本條規定處理*另參見法民四(2012)第43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關于印發劉貴祥庭長在全國海事審判工作會上的總結講話的通知》。。”[1]257-259上述條文理解與適用意見對審判實務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審判人員此后審理該類糾紛,在不斷疑惑和相互詢問中,逐漸改變了歸責原則和法律適用。但轉變過程,接受程度,對法條的理解和解釋,以及法律的具體適用,卻在相當程度上存在著分歧和爭議。
(三)《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解釋和適用的困境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侵權責任法》實施后第35條后段規定在解釋和適用上存在困境。
1.立法預設、理論認識與司法實踐相脫節
從第35條后段規定的立法背景中可以看出,《侵權責任法》在雇員因職務行為遭受人身損害責任承擔上,采用的是二元作法:個人勞務,按民事侵權關系,由《侵權責任法》規范;其他情形,按勞動關系,由勞動、社會保障法律規范。學者的意見,按一元作法:均依勞動、社會保障法律按無過錯原則處理,無論梁慧星教授的“不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最后一句”還是楊立新教授的“第35條不應該在《侵權責任法》中規定”,無不如此。而在《侵權責任法》生效后近4年的審判實踐中,實行的卻是三元作法:按勞動、社會保障法律作為工傷保險賠償處理;按《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作為雇傭關系處理;按《侵權責任法》作為個人勞務關系處理。立法、理論和實踐相脫節,又如何保證統一認識和裁判?從立法角度看,《侵權責任法》作為中國基礎性民事侵權法律,在其生效以后,此前與之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相關規定,被《侵權責任法》所取代,《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第1款已無繼續適用的余地。但現實生活中,除了工傷保險關系和個人勞務關系外,還大量存在既不能按工傷保險處理又難以納入《侵權責任法》第35條所指“個人勞務關系”的雇員因職務行為遭受人身損害侵權糾紛,顯然已經超出了立法預設。從法律規范效力的角度看,學者意見有其嚴格的道理,但一方面排斥《侵權責任法》的適用,架空《侵權責任法》,另一方面又使此類糾紛重陷“無法可依”的尷尬境地,這也是幾年來審判實務不斷在《侵權責任法》第35條和《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之間徘徊、搖擺的最大原因。
2.法律概念和法律規范解釋上的困難
《侵權責任法》第35條所指的“勞務”及與之相關聯的幾個概念,“個人勞務關系”、“提供勞務一方”、“接受勞務一方”,此前很少見諸立法,而《侵權責任法》本身又未作界定。如果從立法背景出發,理解為僅指家政服務領域個人之間的“勞務”,將帶來兩個問題:一是現實生活中,單位或組織同樣需要家政服務,顯然難以列入工傷保險社會統籌,也無法納入“個人勞務關系”;二是個人雇傭并非只在家政服務領域,更多的是在生產經營領域,如漁業捕撈、個體交通運輸,等等。如果將“勞務”及其相關概念與《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中的“雇傭”及其相關概念作相同解釋,則又會帶來以下問題:一是超出了立法預設的規范事項,將“勞務”從單純的生活領域擴大到了生產、經營領域;二是因同一性質“勞務”遭受同樣損害,受雇于單位和受雇于個人,在法律上不同等對待;三是雇員在生產、經營中,因執行職務行為遭受人身損害,具有工傷事故致害性質,卻因為索賠途徑或者賠償程序不同,無法得到應有的權利救濟。
綜上,對于《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無論作哪種適用解釋,在外延和適用對象上均難周全。《侵權責任法》實施后,《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不少條款(主要是第1條至第16條)已失去了繼續適用的正當性。而一概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又存在上述諸多問題。針對現實生活的復雜性和雇員因職務行為遭受人身損害糾紛的多樣性,[6-10]在立法或司法機關未進一步對法律適用作出有效解釋前,作為一種權宜之計,筆者認為:第一,基于對《侵權責任法》第35條立法背景的考量,一方面對《侵權責任法》第35條所指的“勞務”,作限縮性解釋,僅適用于不具有隸屬支配關系的生活領域“勞務”,如家政服務,其他領域不適用該條后段規定;另一方面對于家政服務等領域以單位作為“接受勞務一方”情形,類推解釋、適用第35條后段規定。第二,對于生產、經營等領域具有隸屬支配關系致雇員人身損害的,不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也不適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第1款規定。對此,梁慧星教授的意見至為中肯。
三、船員勞務人身損害不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
《侵權責任法》實施后,船員勞務人身損害,在歸責原則和法律適用上已經出現了相當混亂的局面,有必要加以澄清和統一。
(一)船員勞務關系不是“個人勞務關系”
對于船員與船東之間以給付勞務為標的的這種合同或合同關系,立法、司法解釋以及審判實務各賦予其不同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船員條例》(簡稱《船員條例》)稱之為“勞動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稱之為“勞務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將履行該合同所產生的糾紛案由確定為“船員勞務合同糾紛”,而依《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則認為是“雇傭關系”。可見,僅從概念上區分雙方之間形成“勞動關系”、“勞務關系”,或者“雇傭關系”,既無確定的立法依據支撐,也無法為糾紛法律適用指明任何捷徑。但通過以下幾方面的分析,還是能夠劃清船員勞務關系與《侵權責任法》第35條所規范的“個人勞務關系”之間的界限,為審理船員勞務人身損害糾紛提供法律適用和解釋上的根據。
1.從船員勞務關系本身分析
從主體上看,船東可能是法人、合伙組織,甚至個人,其與船員之間,既難嚴格以“勞動關系”涵蓋,更不能概括為“個人勞務關系”。對于船員勞務人身損害賠償,不能因主體不同而區別對待。從勞務標的看,無論船舶從事運輸、捕撈或其他海上作業,都是一種生產、經營行為,與《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立法背景下的家政服務風馬牛不相及。從雙方關系上看,船東與船員之間具有指示與被指示、支配與被支配的隸屬關系,船員為船東利益,并按船東指示和要求履行技術性、專業性的職務行為,與日常生活中諸如保姆、裝修等工作有很大的差別,不屬于《侵權責任法》立法預設的“勞務關系”。工傷事故致害承擔無過錯責任,是工業化時代發展的產物,理論上有意義的區分在于,雙方之間是否具有隸屬支配關系,是否因執行職務行為遭受人身損害,既不以主體是單位或個人劃界,也不以是否符合工傷保險條件或是否按工傷保險賠償定性。因此,無論將船東與船員之間的這種關系定義為“勞動關系”、“勞務關系”或者“雇傭關系”,也無論船員有無參加工傷保險,以及是否按工傷保險賠償,都不改變船員勞務人身損害具有工傷事故致害的本質屬性。
2.從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分析
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本質上屬于工傷事故致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簡稱《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簡稱《社會保險法》)以及《工傷保險條例》對工傷事故致害有強制性的規定,并自始至終貫徹無過錯責任原則;2007年9月1日起實施的《船員條例》第四章更是專章對船員職業保障作出規定,要求簽訂勞動合同、參加包括工傷保險在內的各類社會保險。可見,對于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沒有理由因《侵權責任法》的實施,尤其是該法第35條后段的規定,而降低或減弱法律、法規對船員權益的保護。
3.從審判實務分析
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是工傷事故致害,但由于船員工作的流動性以及船東主體的多樣性,除一些國有運輸船舶外,船員大多未辦理社會保險,更由于海事審判不以工傷認定和勞動仲裁為前置程序,大量的船員勞務人身損害糾紛并非通過工傷保險賠償而是通過海事訴訟解決。二者救濟途徑不同,賠償程序不同,但實體上的公平與正義,尤其是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傾向性保護,理應得到統一體現,至少在《侵權責任法》實施之前,海事審判實踐就已經如此。改變船東與船員之間關系的性質,或者以船舶為個人所有或合伙共有為由,將其納入“個人勞務關系”,進而適用過錯責任,暫且不論法律適用,至少對案件事實查明、當事人的舉證負擔都是嚴重的沖擊。海事事故具有復雜性和技術性,證據難以固定,船舶發生沉沒、船員全體遇難時,更是如此。讓船員或其遺屬承擔船東過錯舉證責任,許多時候,不僅不現實,甚至荒唐。
綜上,不論船東是單位或者個人,其與船員之間構成的“船員勞務關系”,不是《侵權責任法》第35條規定的“個人勞務關系”。
(二)船員勞務人身損害的歸責原則及其法律適用
歸納前文論述,筆者認為:首先,船員勞務人身損害仍當適用無過錯責任,而不適用過錯責任;其次,船員勞務不是《侵權責任法》第35條所規范的“個人勞務”,不適用該條后段規定;再次,《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第1款盡管有其合理性,但在《侵權責任法》實施后,繼續適用司法解釋的正當性已不復存在,也不宜在裁判中再直接引用。至于審判實踐中一方面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另一方面又在舉證責任上采用過錯推定,以減輕或免除船員或其遺屬舉證負擔的作法,至多反映了審判人員法律適用上搖擺不定的心態和權利保護傾向,不是法律的正當適用和解釋,法理上行不通。
《侵權責任法》在人身損害責任領域取代《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后,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歸責原則,既不能適用《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又不能適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11條第1款,終究是實體法的尷尬。至于解決之道,筆者認為:首先,對于歸責原則,應將船員勞務人身損害定性為工傷事故致害,通過法律適用解釋,以《勞動法》和《社會保險法》為歸責依據,適用《侵權責任法》第7條規定,按無過錯責任原則處理。其次,對于過失相抵,船員自身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的,適用《侵權責任法》第26條和第27條,以平衡船東賠償責任。
四、結語
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本質上具有工傷事故致害性質,不屬于《侵權責任法》第35條所規范的“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情形,不能按該條后段規定適用過錯原則。《侵權責任法》實施后,對于船員勞務人身損害的歸責原則和法律適用,認識和實務已經重新陷入混亂,有必要加以澄清和統一。同時,建議針對《侵權責任法》法律適用作司法解釋,或者海事審判中審理船員勞務人身損害案件如何適用法律作司法解釋時,對《侵權責任法》第35條后段規定進行限縮性解釋,適當限制其在海事審判中的適用。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奚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XI Xiao-ming.The comprehe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ofTortLiabilit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M].Beijing:The People’s Court Press,2010.(in Chinese)
[2]楊釘:船東對受雇船員人身損害的責任承擔[J].中國海商法研究,2013(1):29.
YANG Ding.The liability of the ship owner for the personal injury of the crew member during employment[J].Chinese Journal of Maritime Law,2013(1):29.(in Chinese)
[3]保姆在雇主家意外死亡 東家沒錯仍需賠償近7萬元[EB/OL].(2004-09-28)[2014-05-26].http://news.sina.com.cn/o/2004-09-28/14493791304s.shtml.
Housemaid died by accident,employer compensate nearly 70 000 yuan though no fault at all[EB/OL].(2004-09-28)[2014-05-26].http://news.sina.com.cn/o/2004-09-28/14493791304s.shtml.(in Chinese)
[4]李少平:疑難侵權案件理論與實務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0.
LI Shao-ping.Stud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ort cases in question[M].Beijing:Law Press,2012:20.(in Chinese)
[5]楊立新:《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解釋與司法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196-215.
YANG Li-xin.The interpretation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ofTortLiabilit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M].Beijing: The People’s Court Press,2010:196-215.(in Chinese)
[6]奚曉明.民事法官必備法律司法解釋解讀(上)[M].修訂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121.
XI Xiao-ming.Reading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for civil judges(Vol. I)[M].rev. ed.Beijing:The People’s Court Press,2011:121.(in Chinese)
[7]黃福寧.人身損害索賠[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35.
HUANG Fu-ning.Personal injury claim[M].Beijing:China Procuratorate Press,2011:35.(in Chinese)
[8]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選(2011年第1輯)[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80.
Institute of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aw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Cases of the people’s court(2011·Vol. I)[M].Beijing:The People’s Court Press,2011:80.(in Chinese)
[9]楊春梅,鄂文東.消防民事爭議案例研究[M].北京:群眾出版社,2011:31-42.
YANG Chun-mei,E Wen-dong.Research on civil cases related to fire protection[M].Beijing:Mass Press,2011:31-42.(in Chinese)
[10]李華楠.民事審判法官的邏輯與經驗——深圳法院民事疑難案例解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166-173.
LI Huang-nan.Logic and experience of civil judges—analysis of civil cases judged by Shenzhen Court[M].Beijing:The People’s Court Press,2011: 166-173.(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