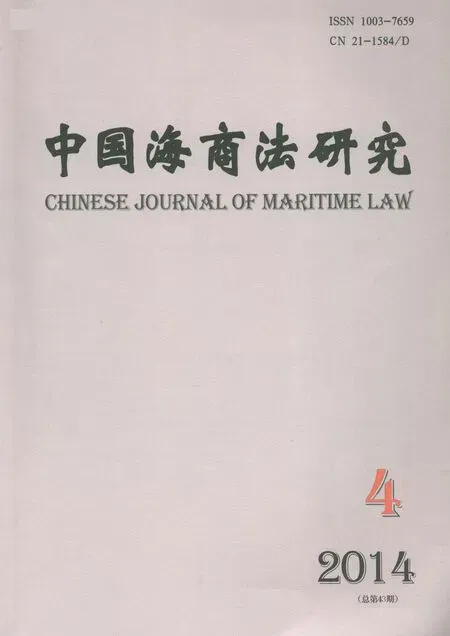論國際航運壟斷協議之競爭規制
王秋雯
(華東政法大學 科學研究院,上海 201620)
一、問題的提出:海洋權益維護與航運反壟斷規制制度之微觀研究
中國航運市場正常良好的競爭秩序目前正遭受嚴重的破壞,例如,外國大型航運公司、國際航運組織聯合在中國沿海對貨主在同一時間、以同一價格征收附加費,近海航線一些航運經營者以掠奪性低價策略采用“零運價”、“負運價”排擠競爭者,外資航運公司占據了中國國際航運業務的大部分市場份額而凸顯了外資壟斷,世界海運三巨頭組成運營聯盟壓縮中國航運企業運營空間。這些問題使中國航運反壟斷規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有必要探索如何完善中國海運競爭法律制度來遏制航運壟斷,規制海運市場,切實維護中國海洋權益。
航運經營者之間的合作協議是海上貨物運輸市場中較為常見的實踐做法。由于此類協議加強了航運經營者之間的聯合,為它們從事協同性行為,例如聯合提價、聯合收取附加費、統一運輸條件等提供了平臺與空間,可能具有嚴重的限制競爭效果,造成航運市場消費者福利乃至社會總福利的減損。如果航運經營者之間的協議符合壟斷協議之構成要件——即它以兩個或兩個以上在經濟和法律上具有獨立性的競爭者為主體要件,以競爭者之間明示或者默示的聯合行為作為行為要件,以妨礙、限制或者扭曲競爭為目的要件或者后果要件——則應被納入壟斷協議制度的規制范疇。然而在中國現有法律框架下,作為海運競爭特別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中航運壟斷協議規制之規定過于零散且并不全面,而作為一般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簡稱《反壟斷法》)又缺乏可以應用到航運市場的具體操作標準,從而導致何種航運協議可獲得反壟斷豁免,不能獲得豁免的協議應當如何適用壟斷協議制度進行壟斷判定等一系列問題不甚明確。國際主要海運監管法域立法的模式各異與內容差異則更增添了航運壟斷協議競爭監管的混亂,也為中國航運立法的學習借鑒帶來了選擇障礙。雖然航運法學界已有一些關于國際航運壟斷協議的研究,但研究的著眼點往往較為宏觀,如何界定航運業壟斷組織、有哪些航運壟斷協議、哪些事項享有反壟斷豁免、如何進行豁免、反壟斷豁免是否要附條件等具體微觀問題亟待深入研究*例如朱新艷、陳剛在研究中特別強調在立法層面明確航運反壟斷協議規制的實體規則,但對于如何明確此類問題卻未進一步論述,參見朱新艷,陳剛.航運壟斷協議規制探討[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11.。基于此,筆者擬在對國際航運壟斷協議范疇界定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類型化研究,具體分析其反競爭的效果程度,并對歐盟與美國相關法律制度進行比較考察,以此為基礎探索以反競爭效果為界分的航運壟斷協議規制體系之建構。
二、國際航運壟斷協議內容及其反競爭效果:從組織到內容的研究范式轉變
現今學理上對于國際航運壟斷協議的研究往往專注于組織形態的研究,例如將其界分為班輪公會、協商協議組織、聯營體、戰略聯盟等具體形式,然而考慮到航運競爭者壟斷合作形式的形態邊界不清,以壟斷協議之內容為基礎的研究亦或更益于理解與討論航運壟斷協議的競爭抑制效應與反壟斷豁免的產業經濟邏輯。按協議內容可將國際航運壟斷協議歸納為:固定價格協議、統一運輸條件與聯合服務協議、限制運力的合理化協議、信息交換協議、技術性合作協議、具有排他性的使用戰斗船協議以及托運人服務協議(俗稱“忠誠契約”)。
(一)固定價格協議及其反競爭效果
(二)統一運輸條件協議及其反競爭效果
運輸服務水平與質量也是國際航運市場中的重要競爭要素,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可以通過制定統一的運輸條件或統一采用某種市場策略來反競爭。例如,在承運人運輸責任上適用統一的責任相對輕微的國際公約,采用統一的滯期費與滯期損失賠償標準,采用相同的服務條款,對托運人提供統一運載量與裝置的相似船舶運載貨物,提供一致或者相似的港口裝卸操作服務等*參見Trans-Atlantic Conference Agreement,FMC No. 11375-059,Article 5(1)(c)。。從反壟斷法上看,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統一運輸條件的協議使承運人失去了獲取競爭優勢的激勵機制,也剝奪了托運人的自由選擇權,無論從船方利益還是貨方利益考量都不會增加福利也不會提升效率,相反卻是迫使消費者向低標準運輸服務妥協。而且不同于以改進技術或優化航運資源配置為首要目的的技術性合作協議,此種統一運輸條件的協議其實質是承運人就統一適用低標準的服務條件達成一致,只會使航運經營者沉溺于壟斷溫室拒絕改善服務質量,而不是致力于提升效率或者增進社會福利。
(三)合理化協議及其反競爭效果
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的協議除涉及價格與運輸條件外,還可能涉及海運服務商業營運事項,諸如限制運力、協定班輪運輸時刻表、劃定營運區域、貨載分配、分攤運營收入與損失,以確保利潤均沾。此類內容與海運服務商業營運相關的協議往往被業內統稱為“合理化協議”。歐盟在泛大西洋公會協議壟斷案中的公會協議就針對前述內容對成員經營者的商業營運進行約束*參見Trans-Atlantic Conference Agreement,FMC No. 11375-059,Article 5.3。。合理化協議往往附屬于航運組織的固定價格協議,通過運力供給限制、地理市場劃分與利潤分配層面的商業整合可以弱化航運組織成員背離組織定價實施更低價格擴充市場份額的動機,因此,強化航運組織的價格固定機制,在此意義上具有固定價格協議之效力增補的反競爭效應。
通過協議設定卡特爾成員的停靠港口并減少班輪航線與班期,將部分船舶撤出營運以“凍結運力”,以及在成員間進行市場切割——這是以“運力管理計劃”之名限制運力的常見實踐做法。[4]運力限制以“饑餓療法”人為凍結運力造成市場供給不足的假象,以此推高價格,且由于遏制了成員的背離動機使運力限制可能產生比協同價格更有效的固定價格作用。然而另外一方面必須考慮的是,運力限制的確可以在季節性或周期性航運市場蕭條時抑制惡性競爭、穩定航運市場、節約航行成本、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從而提升航運者福利與社會總福利,也可能通過協議諸方之間的合作實現技術與信息傳遞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故運力限制協議之反競爭效果不宜一概而論,有必要結合協議參與者的數量及其市場份額、市場供求、市場結構與集中度、進入壁壘、對固定價格之增補效應等諸多因素進行較為全面的分析判定。
合理化協議還涉及地理市場與產品市場劃分之內容,例如班輪公會協議就通過劃分市場防止成員在同一區域彼此競爭。地理市場劃分卡特爾除通過限制競爭得以有效維持價格外,由于運營市場已明確割裂,因此還具有比價格卡特爾更易于監管成員、防止背離的特性,其競爭抑制效果嚴重:一方面,效益差的航運企業因市場得到保護而不會被淘汰,效益好的企業則因市場受限而不能擴大生產和經營規模;另一方面,這些人為割裂開的市場將成為壟斷市場從而減少消費者在市場上的選擇權,損害其權益與福利。[1]132-133對于劃分產品市場的貨載保留與貨載分配協議,存在著競爭違法認定與國家海運扶持政策與制度之間的沖突:在反壟斷法原理上劃分產品市場與劃分地理市場一樣,既限制價格競爭、縮減運力供給,又限制消費者自由選擇之權益;但是主權國家往往強調一定比例的“國貨國運”政策,因而在國內立法、雙邊條約、多邊公約中認可此類貨載分配制度。在意大利全國報關委員會案中,歐洲初審法院原則上認可國家限制競爭行為不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1款(現《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第1款),但主張國家強制的競爭法例外必須狹窄解釋,例外的適用僅限于國家強制義務是經營者限制競爭的唯一因素而不夾雜任何個人私慮*參見Judgment of CFI in Case No.T-513/93 Consiglio Nazionale degli Spedizionieri Doganali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NSD) [2000] ECR II-1807,Para.58。。
合理化協議中的運營收入與損失分攤內容亦具有反競爭效果。倘若卡特爾內部只進行銷售數量配額分配而不均攤收入,則銷售者往往尚有動力尋求技術改進以獲得配額內利潤最優,然而收入與損失分攤機制將銷售者的收入與其經營質量脫鉤使航運經營者喪失技術改進動力。[5]因此運價卡特爾、運力限制卡特爾如果同時輔以運營收入與損失分攤的協議內容則會產生嚴重的反競爭效果,但其本身的反競爭效果卻也往往僅局限于固定價格協議、限制運力協議與市場劃分協議之反競爭效力增補。
(四)技術性合作協議及其反競爭效果
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的技術性合作協議之表述源于歐盟航運競爭法的規定,2008年歐盟《有關海上運輸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條的指南》中指出:“特定類型的技術協議因未對競爭構成限制可能不屬于條約第81條的禁止性規定。例如,以改進技術或實現技術合作為唯一目的和效果的橫向協議就屬于豁免范疇。有關執行環境標準的航運協議也可能被認為屬于豁免范疇。競爭者之間有關價格、運力或者其他競爭要素的協議則原則上不予豁免*參見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OJ C 245,26.9.2008,Para. 35。。”雖未清晰界定技術性合作協議的內涵與外延,但可以明確的是技術性合作協議往往不具有明顯的反競爭效果,此種技術性聯合不但有助于推動技術或經濟進步,能夠使消費者從技術進步中獲益,且往往以限制競爭為絕對必要條件,并不會在市場產生排除競爭的效果。
(五)信息交換協議及其反競爭效果
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交換既可通過協議進行,亦可以國際航運協議組織為平臺進行,還可能是在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不存在協議或者平臺條件下所為之共同行為,因此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交換協議有時被視為是企業間的協議,有時被視為是航運組織的決議,還有時被視為是企業間的協同行為。歐盟委員會指出:“信息交換系統需要達成一項協議,經營者以此協議為基礎進行信息交換,或者將信息提供給一共同機構,而該機構以商定的形式和頻率負責集中、編輯和處理信息,然后再反饋給參與者*參見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OJ C 245,26.9.2008,Para 38。。”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交換協議對于市場競爭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尚不可一概而論,為國際航運反壟斷法律制度是否規制以及如何規制此類行為提出了新問題。原則上看,國際航運經營者可以通過相互交換信息在更加透明化的市場上減低運力過剩時面臨的風險,有助于穩定市場;然而如果信息交換成為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協調與控制市場的工具,這種信息交換就構成違反反壟斷法的壟斷協議。[6]例如,信息交換可能是為某一反競爭行為提供便利的機制,比如監控或執行某一價格卡特爾,在此情況下的信息交換就具有反競爭效果*參見Judgment of ECJ in Case No.C-49/92 P Commission v. Anic Partecipazioni SpA,[1999] ECR I-4125,Para. 121-126。。因此,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交換協議的反競爭效果、減損航運市場消費者福利之程度,有賴于具體個案分析。
通過對個稅改革內容的分析,可以發現此次改革的力度非常大。下面通過實例進一步分析此次個稅改革對我國人民稅負的影響。
(六)排他性協議及其反競爭效果:使用戰斗船協議與忠誠契約
國際航運經營者的排他性協議既包括縱向反競爭協議,也包括橫向反競爭協議,前者表現在承運人與托運人訂立包含運費延期折扣或者雙重運費以捆綁托運人為主要內容的忠誠契約,后者表現在承運人之間以聯合抵制其他經營者為唯一目的的使用戰斗船協議。有學者認為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的排他性協議是嚴重限制航運競爭的壟斷協議,指出:“遠洋航運市場中排他性協議的首要目的是擴大航運卡特爾的市場操縱力,而不是提高效率與增進托運人福利。”[7]194然而在筆者看來,排他性協議的反競爭效果必須區分橫向壟斷協議與縱向壟斷協議而不宜一概而論。
1.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的橫向排他性協議:使用戰斗船協議
戰斗船是早期班輪公會與非公會船公司在航線上進行公開對抗式競爭的一種原始策略。“當公會控制的航線上出現非成員公司的營運船舶時,公會就派遣專門的公會船只緊隨會外船,與之同時開航和靠港,并不計其營運成本和利潤以相同于或低于會外船的運價爭取其貨物,經過反復削價的價格競爭直到將非公會船排擠出該航線為止。使用戰斗船所造成的損失由公會全體成員共同承擔。”[8]美國1984年航運法更直接以反競爭性界定戰斗船協議,指出其是將其他經營者排擠出市場的排除、限制、減少競爭的協議*參見U.S.,Shipping Act of 1984,Article 3(10)。。使用戰斗船協議是以排擠競爭對手為唯一目的的聯合抵制,由于該協議的締約者聯合降價之目的在于排擠競爭對手而不惜犧牲利潤,其結果損害小企業權益,亦不會為消費者帶來長期好處,會產生消費者福利與社會整體福利的嚴重減損。[9]
2.國際航運經營者之間的縱向排他性協議:忠誠契約
忠誠契約是一種承運人用來限制托運人締約自由的協議,承運人通過采用運費回扣或者雙重運費機制捆綁托運人,防止其與其他承運人締約,從而與托運人之間成立排他性契約關系。對于如何看待忠誠契約以及與其相關的運費延期折扣與雙重運費制度的反競爭作用,學理上存在較大爭議。有學者認為此類契約將惠及消費者,因為承運人實際上通過返還折扣的方式變相壓低了運費,消費者會因此增加福利而不是利益受損,故不宜直接禁止此類協議。[10]但也有相反觀點認為忠誠契約構筑了隱形的市場進入壁壘,阻礙新經營者進入市場,侵害了航運市場之競爭秩序。[11]筆者認為,雖然忠誠契約的確構成捆綁消費者的排他性協議,其反競爭作用卻并不像使用戰斗船協議同等嚴重,因為消費者始終掌握是否與托運人締約之自由。當然,消費者的締約自由能否真正付諸實施取決于具體的市場情況,假若市場為某個大型航運組織主導使消費者喪失議價的話語權,則此時忠誠契約就具有嚴重的反競爭效果。占有較大市場份額的承運人往往比那些市場份額小的承運人更容易濫用強大談判實力脅迫托運人與其訂立忠誠契約對托運人進行交易綁定從而反競爭。因此,忠誠契約之反競爭效果取決于市場集中度、承運人市場操縱力的大小,對其反競爭效果進行個案判定是較為妥適的方法。
三、以反競爭效果為界分的國際航運協議類型化
競爭可以為市場注入活力、降低價格、惠及消費者,但考慮到浪費性競爭、外部性、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偏離、市場不確定性等諸多問題,競爭卻未必總是有效率的。國際航運壟斷協議的法律規制架構需要在協議限制競爭效果、效率改進效果、航運企業利益與消費者福利、法律執行成本之間進行權衡,筆者以為,以反競爭效果為界分并綜合考慮前述要素將國際航運壟斷協議類型化,或許可以為航運協議規制、航運產業規制、航運業競爭規制的制度建構、行政執法實踐乃至司法審判實踐提供新的視角。
(一)航運經營者協議限制競爭效果與效率改進效果權衡基礎上的類型化
壟斷廠商可以人為地制造其產品的稀缺性從而將價格提高到競爭水平之上產生壟斷定價,這種壟斷型產出的推定無效率為反壟斷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效率也暗含了反壟斷政策的局限,因為在某些特定領域,從成本收益角度分析生產集中化帶來的節約會超出壟斷定價的成本,因而壟斷比競爭更有效率。反壟斷法律制度深受產業組織理論影響,將效率視為重要的社會價值。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納更試圖證明反壟斷法唯一的目標即是提升經濟效率。[2]preface依前述關于國際航運壟斷協議反競爭效果之討論并兼顧協議的效率改進效應,可以將航運協議大體劃歸為三類:限制競爭效果嚴重但效率改進效果近乎為零、限制競爭效果待定但具有一定效率改進效果、限制競爭效果不嚴重且效率改進效果顯著。
首先,固定價格、統一運輸條件、市場劃分、使用戰斗船協議具有嚴重的限制競爭效果,且除聯合的航運經營者獨享壟斷利潤外并不產生其他社會收益,基本可以被直接推定為壟斷導致的產出無效率,理應劃歸為第一類。然而雖然反壟斷法一般將價格卡特爾視為嚴重限制競爭的“核心卡特爾”(hardcore cartel),但國際航運競爭者間的固定價格協議卻以“空核理論”(empty core)為理論根基得以排除競爭規制。根據該理論,在一個可以進行討價還價博弈的市場中競爭者有不同的選擇,既可以選擇聯合,也可以選擇背離聯合而單獨獲利,而博弈的核心就在于一組穩定的均衡分配從而構建出競爭者之間的有效聯合。[12]但是在一個不存在“核心”的市場中則不存在這種穩定的價格產出組合,總會有經營者通過打破市場均衡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就形成了所謂的“空核”。[3]61班輪運輸市場多被認為存在這樣的空核特征,經營者的固定價格因而有利于效率提升。[13]然而筆者認為以“空核理論”否定航運固定價格協議的競爭規制恐怕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在于:第一,“空核理論”認為班輪市場的不穩定狀態在于受到市場進入退出自由的影響,卻忽視了班輪運輸市場由于開辟航線的高沉沒成本帶來的隱性進入壁壘,無疑會對“空核理論”帶來某種弱化;第二,“空核理論”之最大問題在于航運經營者的價格結盟未必必然會穩定市場競爭秩序,市場秩序的穩定也并非僅能靠價格固定實現。[14]航運業的價格產出與其他運輸行業不能說有根本差異,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于與航運公司具有類似行業特點的鐵路公司的固定價格協議就持禁止態度,早在1897年著名的泛密蘇里案中就以反托拉斯法否定鐵路公司的固定價格協議*參見United States v. 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ociation,166 U.S. 290(1897)。。歐盟海運競爭立法中也將固定價格、劃分市場協議一并認定為“核心卡特爾”,不允許豁免競爭法之適用*參見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906/2006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Agreements,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between Liner Shipping Companies (Consortia),OJ L 256/31,29.9.2009,Article 4。。雖然美國仍堅持航運協議的產業規制監管,協議只需向聯邦海事委員會報備即可豁免適用反托拉斯法,但其本質卻與歐盟規制模式殊途同歸——美國豁免航運協議反托拉斯規制的前提在于協議必須賦予成員可以隨時背離協議之獨立行動權,這種制度設計實際上極大程度地強化了航運卡特爾成員的欺騙與背離,弱化了卡特爾同盟;而一旦協議試圖防止成員背離則不得享有豁免,直接適用本身違法原則。即使在歐盟尚未取消班輪公會集體豁免時,歐洲初審法院就在中西非航運公會案中判決,分屬三家航運公會的成員約定不在各自公會的運營范圍外與其他公會覆蓋的運輸區域從事競爭,這樣的協議違反《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1款(現《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第1款)之規定,也不符合第81條第3款(現《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第3款)規定的豁免條件*參見Judgment of CFI in Joined Case No. T-24/93,T-25/93,T-26/93,and T-28/93 Compagnie maritime belge transports,Compagnie maritime belge SA,Dafra-Lines A/S,Deutsche Afrika-Linien GmbH & Co. and Nedlloyd Lijnen BV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EWAL I) [1996] ECR II-1201,Para.33-52。。這一結論在上訴中獲得歐洲法院的維持*參見Judgment of ECJ in Joined Case No. C-395/96 and C-396/96 Compagnie maritime belge transports, Compagnie maritime belge SA,and Dafra-Lines A/S v. Commission(CEWAL II) [2000] ECR II-1365。。
其次,合理化協議、忠誠契約、信息交換協議則屬于限制競爭效果不定但具有一定效率改進效果之協議,因此類協議的限制競爭效果無法一概而論,乃需結合市場集中度、承運人市場操縱力的大小、市場供求狀況、卡特爾形態松散或緊密、對其他卡特爾協議的壟斷增補效應等諸多因素全面衡量,但卻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效率,例如合理化運營后產生的成本節約、運費折扣為消費者帶來的運費減低、信息交換使市場透明化從而減低運力過剩的市場風險。在更嚴格意義上,除航運市場供求失衡以外的運力限制往往亦屬于第一類嚴重限制競爭且無效率的協議類型,歐盟海運競爭立法中就將其與固定價格、劃分市場協議一并認定為“核心卡特爾”,不允許豁免競爭法之適用。
需要著重解釋的是,緣何將同屬于排他協議的使用戰斗船協議與忠誠契約區別以待?實際上競爭規制制度的差別設計恰好回應了橫向壟斷協議與縱向壟斷協議在反競爭效果上的差異化。使用戰斗船協議作為發生在同一相關市場之內的橫向壟斷協議,其對競爭限制效果是直接且深遠的;而忠誠契約則往往締結于承運人與托運人、無船承運人、船舶代理人或多式聯運其他區段經營者之間,對競爭之限制往往無法直接判定并可能具有一定的效率提升效應,因此需要結合市場結構等要素特別考察壟斷勢力能否在不同市場之間進行傳遞從而損害競爭。當然,認為忠誠契約之反競爭效果遜于核心卡特爾協議不等于忽視其反競爭效果。有實證量化研究表明忠誠契約可以強化航運經營者的市場勢力。[7]193-213美國航運法就拒絕給予忠誠契約反托拉斯法豁免*參見U.S.,The 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1998,Section 7(b)(4)。。但博克將市場進入壁壘引入排他性契約的論述或許更有助我們把握忠誠契約規制制度的設計。博克拒絕對排他性契約(exclusionary contracts)的反競爭效果一概而論,甚至質疑經營者可以通過與消費者之間的排他性契約維持或增強壟斷地位的觀點。其研究表明,如果市場進入壁壘較高則航運卡特爾組織可以通過降低價格防止新的經營者進入市場,而無需通過與消費者締結排他契約;如果市場進入壁壘較低則消費者會選擇與新進入者締約而不是接受壟斷者的排他契約。在這個意義上,忠誠契約是否能夠獲得應用并實際提升壟斷者的市場勢力是存在疑問的。[15]
其三,技術性合作協議本身即以效率改進為唯一目標,在壟斷不損及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具有完全的社會效率提升效應。歐盟海運競爭法認為此類技術性合作協議當然地符合一般競爭法下的豁免要件——有助技術或經濟進步,能夠使消費者從中獲益,以限制競爭為絕對必要條件,且不會排除競爭——因而直接豁免此類協議適用競爭法。
(二)航運經營者協議限制競爭效果與消費者福利衡平基礎上的類型化
20世紀60年代以后,肯尼迪政府和尼克松政府提出的“消費者主權”使經濟法完成了作為經濟弱勢群體進行實體性價值救濟和社會校正的工具的構建,塔夫脫大法官在AddystonPipe&Steel案中的判決使“消費者利益至上”作為執行反壟斷政策的司法標準也得到明確,產生了從效率到消費者福利之轉變。歐盟法院一貫強調效率與消費者福利是兩個分離的標準,必須給予獨立關注,競爭的必要維持并不足以實現效率利益自動轉移給消費者。因此歐盟委員會逐步采用嚴格的消費者福利標準,只要消費者沒能公平分享限制協議的效率利益,歐盟委員會就拒絕同意豁免該協議。[16]現代反壟斷法從保護效率到保護消費者而不是保護小企業的發展,使航運業的競爭規制必須首先考察航運服務消費者(包括托運人、發貨人、收貨人、運輸單據持有人)因壟斷協議導致的福利減損。而消費者福利的分析不限于消費者收益之增減,亦需要考量托運人的締約選擇權是否被剝奪、或在多大程度上受限。航運經營者之協議豁免反壟斷規制的首要前提即是無損消費者福利,次之的考量因素才是壟斷帶來的效率提升與社會總福利增加。依前述關于國際航運壟斷協議反競爭效果之討論并兼顧航運市場消費者福利增減,實際上可以得出與上文效率標準下相似的三種分類:首先,固定價格、統一運輸條件、市場劃分、使用戰斗船屬于限制競爭效果嚴重且嚴重減損消費者福利的壟斷協議;其次,從影響締約托運人自由選擇權的視角來看,限制競爭效果不定但對消費者福利有減損的協議則基本可以攝涵忠誠契約、合理化協議以及信息交換協議;其三,如果航運經營者之間不存在價格上的聯合,且仍然獨立于消費者締約,則其技術性合作屬于限制競爭效果不嚴重且未減損消費者福利之協議。
四、類型化基礎上的航運協議競爭規制制度建構
(一)以反競爭效果為界分的航運壟斷協議類型化規制體系建構
以海事商人習慣為淵源的海事海商法律制度歷來尊重航運經營者之契約自由,然而一旦航運經營者濫用契約自由就會啟動海事海商法律制度中強行法的介入來矯正市場、實現正義,而航運產業規制制度與反壟斷規制制度無疑均屬強行法之范疇。以規制為內容的強行法介入的法理根基在于對船方濫用契約自由有準確的定位。前述關于國際航運壟斷協議反競爭效果并兼顧航運協議之效率改進效應、航運市場消費者福利增減進行的協議類型劃分無疑有助于我們建構作為強行法的規制制度之主要架構。
固定價格、統一運輸條件、市場劃分、使用戰斗船協議因其嚴重的競爭抑制效果、壟斷導致的無效率、減損消費者福利效果,即構成契約自由之濫用,不但需要強行法規制,且從執法效率而言規制制度介入的門檻應當較低。根據美國反托拉斯判例法的發展,此類主觀意在危害競爭并且實質上往往能夠嚴重危害市場競爭的壟斷協議適用本身違法原則,無論協議是否付諸實施,無論實施效果如何,法院根據既往的反托拉斯法實踐認為此類協議的反競爭效果十分明顯且無助于公共利益與經濟效率,直接判定其違法。雖然《反壟斷法》采歐盟模式使用禁止與豁免相結合的制度設計并主要適用合理原則,然而明確某類航運協議的嚴重反競爭效果并施以較高標準之效率提升或福利增進的證明義務于航運經營者,有助于節約原本就有限的執法成本。波斯納從執法成本的法律經濟分析入手對此進行了說明:法律規制僅考察固定價格的行為本身而不附加行為意圖等其他判斷因素,乃是因為銷售者不太可能在明知固定價格不太可能成功的情況下進行此類圖謀,即便有時候懲罰了無法得逞的圖謀也不會造成損害,并且基于公共執法預算約束力假定,執法效率是必須被納入考量范圍的制度建構要素,對于不會得逞的固定價格圖謀進行追究會導致消耗在邊緣案件中的執法資源不能用在更重要的案件中。[2]54-55但是,對于不嚴重限制競爭的其他壟斷協議,執法者則必須綜合分析其福利影響才能判斷是否要做出違法認定。此外,考慮到技術性合作協議可能帶來更優的市場資源配置與效率提升效果,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聯合實現的合理化似乎比自由競爭更可取,在航運競爭法制的架構中宜做反壟斷豁免處理。上述以協議反競爭效果為基礎架構的競爭規制體系實際上回應了中國反壟斷法合理原則下的執法分析模式與思路,將本身違法與反壟斷豁免視為競爭規制的兩極,在這兩極中進行取舍權衡,有益于解決證明標準的問題,也有利于將反壟斷執法資源集中在復雜案件上。
(二)航運壟斷協議的公法規制模式選擇:產業規制還是競爭規制?
盡管我們已經從協議反競爭效果程度、效率標準、消費者福利標準層面初步討論了強行法介入航運經營者契約防止其濫用合同自由的干預邊界,但尚存的問題在于航運壟斷協議強行法規制的模式選擇。在這一問題上,世界海運競爭兩大監管法域美國和歐盟的規制制度呈不同模式:前者倚重產業監管機構——聯邦海事委員會來規制航運經營者的協議壟斷,采用以協議報備制度為基礎的事前協議監管模式,并在航運法中設定一部分空缺不予豁免,交由反托拉斯執法機構負責;后者則沒有獨立的航運競爭執法機構,而將航運壟斷協議交付競爭監管,采事后規制模式,雖在法律制度中豁免某些航運協議的競爭法適用,但近年來的法律變革卻越來越收緊航運協議的競爭規制豁免范疇。不存在單獨的航運產業競爭監管機構或許與歐盟作為國家間共同體的性質和職能有關,但中國航運壟斷協議的公法規制卻無法繞開產業規制與競爭規制的模式問題,特別是在航運業逐漸放松管制的情況下是否應將競爭監管權交由統一的反壟斷執法機構負責?霍溫坎普認為實施規制將導致反壟斷法地位降低,反之如果政府限制產品的價格和產出水平則反壟斷法就被拋在一邊,因此當一個產業面臨“放松規制”的境況時反壟斷才代替殘余的規制政策發揮作用。[17]按照霍溫坎普對產業規制與競爭監管關系的解讀,放松規制的結果往往是通過限制反壟斷豁免的方式擴大反壟斷的實施范圍,作為放松規制之典型的中國海運業無疑會更加依賴競爭規制,與其他非網絡型產業一樣通過競爭規制促進競爭、提升效率,而不是倚重產業壟斷。筆者認為,航運壟斷協議的競爭監管并不排斥產業規制,航運產業政策可以貫穿于反壟斷法的實施過程中,以經濟效果理論為核心的“合理原則”就注重在反壟斷與經濟效益方面進行合理權衡;另外一方面,扶持航運業發展完全可以通過適度政府補貼、優惠稅率、低息貸款、貨載優先等一系列“非壟斷”鼓勵的方式進行。[18]綜上,從偏重產業監管的事前控制模式向競爭規制事后調控模式的過渡的漸進性轉變無疑是航運壟斷協議的公法規制模式的未來走向。
(三)以競爭規制、事后調控為主導的航運壟斷協議規制思路與框架
中國目前的航運壟斷協議監管體系呈現產業監管與競爭監管之間的競合:一方面,交通運輸部負責航運協議的報備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反壟斷執法機構也承擔起一部分航運協議的競爭監管工作。航運協議產業監管與競爭監管之間的競合現象或許可以從中國法律制度建構時對于域外法不同領域的學習、借鑒與本土化來解釋。中國反壟斷法律制度的構建主要從歐盟競爭法中汲取經驗,然而航運協議備案監管的做法卻主要借鑒自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的運價協議與航運協議備案制度。但無論是學習歐盟競爭法還是借鑒美國航運協議監管,對中國的航運壟斷協議競爭監管制度而言似乎都存在一定的“片面化”問題——或在學習歐盟法時忽視了其海運業競爭監管制度,或在借鑒美國法時無視了其備案制度與反托拉斯法的銜接,從而使在歐盟和美國都不存在的產業監管與競爭監管的脫鉤乃至沖突問題在中國規制航運壟斷協議時凸顯出來。美國將航運協議在聯邦海事委員會的預先備案作為豁免適用反托拉斯法的依據,但美國航運法中明確規定了禁止在航運協議中使用某些反競爭性條款,例如不得針對運費、附加費、貨物分類、裝卸費采用歧視性定價,不得采用延期折扣,不得不合理地拒絕交易,航運協議組織或班輪公會不得從事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的掠奪性定價,不得劃分市場等*參見U.S.,The 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1998,Section 10。。美國做法看似豁免航運協議的反托拉斯法規制,但航運法嚴格的限制性條件已經弱化了航運協議的壟斷效果。歐盟海運競爭法變革后航運業開始適用歐盟一般性競爭法,但是有條例明確豁免航運聯營的競爭法適用,前提是:航運聯營應符合歐盟競爭法壟斷協議的豁免要件,不得從事“核心限制競爭行為”,不得在相關市場上超過30%的市場份額,不得限制成員的協議退出自由*參見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906/2006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Agreements, 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between Liner Shipping Companies (Consortia), OJ L 256/31, 29.9.2009。。這實際上意味著通過該條例取得豁免甚至比獲得一般競爭法下的豁免更加嚴格。
比諸歐美而反觀中國航運競爭法律制度,航運協議雖適用《反壟斷法》,但是對于航運協議向交通運輸部預先備案后是否豁免其適用《反壟斷法》之規定,航運壟斷協議在何種程度上構成經營者集中協議而應當適用事前規制制度的問題尚不明確,因此明確以競爭規制、事后調控為主導的航運壟斷協議規制制度具體應如何架構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此筆者認為,考慮到中國反壟斷法律制度主要借鑒歐盟立法模式,適度參考歐盟海運競爭法的有關內容,并結合前述有關以反競爭效果為界分的航運壟斷協議類型化討論,賦予產業監管機構技術性協議豁免監管權,不失為可行的制度建構進路。首先,以競爭規制、事后調控模式作為主導性立法思路。雖然歐盟和美國對于航運協議在多大程度上排除一般反壟斷法適用的范疇問題規定不一,但無疑歐美做法均認可一般性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規制航運壟斷協議上的功能和作用。因此,確立以競爭規制、事后調控模式作為主導性立法思路實際上也與國際主要海運法域的做法相一致。其次,在《航運法》中以反競爭效果為界分,兼顧效率標準與消費者福利標準建構類型化航運壟斷協議規制體系:對于固定價格、統一運輸條件、市場劃分、使用戰斗船協議,考慮到其嚴重的競爭抑制效果、壟斷導致的無效率、減損消費者福利效果,可以參照歐盟做法,視為“核心卡特爾”直接予以禁止;對于技術性合作協議,則可以賦予其反壟斷豁免;對于其他類型的航運協議則適用合理原則,由反壟斷執法機構適用個案考量、事后規制。再次,技術性合作協議的豁免可以由產業監管部門按照美國協議報備制度來進行管理,將豁免制度作為融合航運產業政策與競爭規制的合力點,并在《航運法》中明確授權反壟斷豁免的實體法要件與程序法要件。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王曉曄.王曉曄論反壟斷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WANG Xiao-ye.Antitrust law[M].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10.(in Chinese)
[2]POSNER R.Antitrust law[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3]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Fin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in liner shipping,DSTI/DOT(directorate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division of transport)[R].Paris:OECD,2002.
[4]POZDNAKOVA A.Liner shipping and EU competition law[M].The Netherland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8:59-60.
[5]HERMAN A.Shipping conferences[M].Deventer: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1983:25.
[6]MARLOW P,NAIR R.Liner shipping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a European perspective[J].Marine Policy,2006(6):684.
[7]RICHARD P.Exclusive contracts and market power:evidence from ocean shipping[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03(2).
[8]王杰,王琦. 國際航運組織的壟斷與競爭[M].大連: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2000:19.
WANG Jie,WANG Qi.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of international shipping organizations[M].Dalian: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Press,2000:19.(in Chinese)
[9]SJOSTR?M W.Ocean shipping cartels:a survey[J].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2004(2):120.
[10]LEWIS W A.Overhead costs:some essays in economic analysis[M].New York:Rinehart,1949:72-83.
[11]SJOSTR?M W.Monopoly exclusion of lower cost entry:loyalty contracts in ocean shipping conferences[J].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1988(3):339-344.
[12]HYLTON K N.Antitrust law:economic theory and common law evolu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15.
[13]PIRRONG S C.An application of core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ocean shipping market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92(1):89-131.
[14]DINGER F.The future of liner conferences in Europe:a critical analysis of agreements in liner shipping under current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M].Frankfurt:Peter Lang,2004:88.
[15]BORK R.The antitrust paradox: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M].New York:Free Press,1993:303-309.
[16]張永忠.反壟斷法中的消費者福利標準:理論確證與法律適用[J].政法論壇,2013(3):107.
ZHANG Yong-zhong.Consumer welfare standard in antitrust law:theory and legal practice[J].Tribun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13(3):107.(in Chinese)
[17]HOVENKAMP H.The antitrust enterprise:principle and execution[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230.
[18]王秋雯.產業政策與競爭規制協調視野下的國際航運反壟斷豁免理論反思[J].河北法學,2014(11):110-111.
WANG Qiu-wen.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timonopoly exemption:a perspective from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J].Hebei Law Science,2014(11):110-111.(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