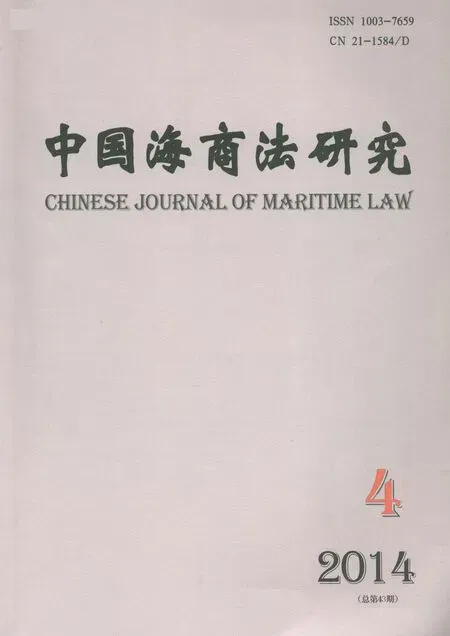我國船舶司法拍賣規(guī)范的沖突與調適
李曉楓,高俊濤
(1.大連海事大學 法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2.華東政法大學 科學研究院,上海 200042)
船舶司法拍賣是我國特有的訴訟程序,海事法院對此有著豐富的司法實踐。2000年7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簡稱《海訴法》)總結多年來海事法院船舶拍賣的經驗教訓,對船舶司法拍賣作出一系列專門規(guī)定,進一步規(guī)范了相關制度。不過,就實務操作效果而言,《海訴法》的規(guī)定仍過于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海訴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zhí)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guī)定》(簡稱《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等規(guī)范的出臺,極大地豐富了船舶拍賣規(guī)范依據,成為船舶拍賣實務中的操作細則。但是,源于海事糾紛之特殊性,《海訴法》與一般民事執(zhí)行程序中的規(guī)范存在很多沖突,同時《海訴法》本身也凸顯一些不周延之處,這給船舶司法拍賣實務操作帶來諸多困惑與不便。
一、船舶拍賣與流拍財產再次拍賣規(guī)定之間的沖突
(一)船舶拍賣公告期限不兼容
根據《海訴法》第32條的規(guī)定,拍賣船舶的公告期間不少于30日。與之相比,根據《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的第11條第2款之規(guī)定,拍賣動產應當在拍賣7日前公告,拍賣不動產或者其他財產權的應當在拍賣15日前公告。同時,該規(guī)定的第26條、第28條規(guī)定,如果發(fā)生流拍,而且到場的申請執(zhí)行人或者其他執(zhí)行債權人不申請以該次拍賣所定的保留價抵債的,應當在60日內再行拍賣。
對比《海訴法》與《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的規(guī)定,前者規(guī)定拍賣公告期不應當少于30日,而后者僅規(guī)定為7日或15日。但是,《海訴法》沒有規(guī)定流拍之后的法律程序,而《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沒有規(guī)定再次拍賣的公告期限、通知期限等,僅規(guī)定兩次拍賣的時間間隔不應當超過60日。
據此,若同時適用《海訴法》和《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的規(guī)定,會帶來不便。根據《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如果第一次拍賣的競價未達到保留價,導致流拍,法院應當組織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拍賣。而在實務中,無論是第一次拍賣還是流拍之后的再次拍賣,海事法院都應當根據《海訴法》的規(guī)定發(fā)布拍賣公告。如果結合《海訴法》和《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的規(guī)定,第二次拍賣、第三次拍賣的公告期限也不應當少于30日,依此組織船舶拍賣將導致拍賣周期過長。
由于《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的公告期限較短,分別為7日、15日,因此即使發(fā)生再次拍賣,拍賣的總體期限也不會很長。但是,《海訴法》在規(guī)定之時沒有考慮到流拍及再次拍賣的后續(xù)程序,因此導致了上述問題。實務中,海事法院往往通過各自的內部規(guī)定進行變通,例如對第二次、第三次拍賣的公告期控制在一周左右,但是上述變通做法的法律依據有所不足。筆者認為,出于船舶拍賣效率性的需要,有必要在未來的立法中明確船舶多輪拍賣之間的時間間隔,以一周為宜。
(二)船舶拍賣次數限定脫離現實
根據《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法院應當首先采取拍賣的方式處置被執(zhí)行人的財產,如果拍賣時無人競買或者競買人的最高應價低于保留價,且到場的申請執(zhí)行人或者其他執(zhí)行債權人不申請以物抵債,法院應當組織再次拍賣。其中,動產拍賣以兩次為限,不動產及其他財產權拍賣以三次為限。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盡管船舶的性質是特殊的動產,但是通常海事法院對船舶拍賣準用了不動產的拍賣規(guī)定,即先經過三次拍賣,如果無法成交再依法組織變賣。
但是,船舶扣押及拍賣有其特殊之處:一方面,船舶在扣押期間需要看管,直至船舶成交之后移交完畢為止,此間的看管成本較高。如果所有的船舶都必須經過三次拍賣以及變賣,會導致船舶處置成本過高,影響各方當事人的權利。另一方面,船舶在扣押期間面臨的風險較大。其中既有自然風險,例如我國東南沿海臺風等惡劣天氣會致使船舶毀損。另外,亦有法律責任風險,例如實務中多有被執(zhí)行人逃逸,法院被迫需要聯系船員或第三方看管船舶,如在此期間發(fā)生船舶事故,會導致看管責任難以厘清。因此,船舶不宜扣押時間過長,以避免遲延權利人實現債權,亦使法院免于船舶看管事務工作,集中司法資源。
對此問題,有的觀點認為應當根據不同的船型調整船舶公告的期限,例如對于商船拍賣應當規(guī)定不得少于30日的公告,對拍賣漁船或其他小型船舶應當規(guī)定不少于7日的公告期。[1]此外,有的海事法院在操作時進行變通,對于評估價值比較低的船舶、無證套牌船舶以及因氣象、船舶狀態(tài)、市場行情等因素不宜長期扣押的船舶,不限定拍賣次數,根據實際需要決定拍賣次數或者是否進行拍賣。例如,對于評估價在50萬元以下的船舶,僅拍賣一次,如果發(fā)生流拍法院將依職權直接組織變賣;又如,對于評估價在10萬元以下的無證套牌船舶以及評估價在5萬元以下的小型船舶,考慮到看管成本等因素,法院有時決定不經拍賣,直接組織變賣。
筆者支持上述做法,無論是根據船舶類型調整公告期限,還是根據船舶價值賦予法院一定的裁量權,都能夠減少船舶拍賣成本,從而有利于維護當事人利益。《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作為《海訴法》船舶拍賣工作的操作細則,沒有注意到船舶拍賣的此類特殊性,導致適用上的不便。而《海訴法解釋》僅在第39條規(guī)定,20總噸以下小型船艇的扣押和拍賣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進行,該規(guī)定僅考慮噸位因素,而且同樣須受制于《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的限制。此外,雖然海事法院的內部做法反映了實務上的現實需要,但是在現有法律法規(guī)等規(guī)范中找不到適用依據,尚需日后出臺法律或者司法解釋作出調整。
二、船舶拍賣款分配程序與破產程序的沖突
以往,由于我國司法實務中缺乏船舶企業(yè)破產實例,《海訴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yè)破產法》(簡稱《企業(yè)破產法》)之間的法律程序沖突被長期忽視。近年,隨著金融危機對船企影響不斷加深,我國在2013年底連續(xù)出現了數起大型船企的破產清算、重整案例,典型的有舟山永鴻海運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件、海南泛洋航運有限公司破產清算案件、長航鳳凰股份有限公司的破產重整案件。在上述案例中,《海訴法》和《企業(yè)破產法》兩法之間的法律沖突顯現。
(一)船舶拍賣后續(xù)規(guī)定不同
《企業(yè)破產法》第19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有關債務人財產的保全措施應當解除,執(zhí)行程序應當中止。”
但是,《海訴法》與《企業(yè)破產法》的規(guī)定截然相反。根據《海訴法》的規(guī)定,在船舶拍賣程序啟動之后,海事法院應當發(fā)布船舶拍賣公告,海事債權人應當在公告指定的期限內申請債權登記,在獲準登記之后應當提起確權訴訟,否則視為債權人放棄了在本次船舶拍賣價款中受償的權利。
而且,在船舶拍賣公告發(fā)布之后,海事法院在公告期間會裁定是否準許債權人的登記申請、審查是否受理確權訴訟案件。“海事法院接受委托、作出強制拍賣船舶的裁定后,在船舶拍賣程序中,根據《海訴法》第10章‘債權登記與受償程序’第111條的規(guī)定,必須啟動債權登記程序。”[2]如果依照《企業(yè)破產法》第19條的規(guī)定,已經進行的船舶拍賣、債權登記、確權訴訟程序將中止,造成當事人的不便及訴訟資源的浪費。
筆者認為,由于船舶拍賣的技術性很強,《海訴法》已對船舶拍賣委員會、船舶所有權轉讓等問題作出了更加細致的專門規(guī)定,因此普通法院在受理船企破產案件之后,所涉船舶拍賣也更宜委托海事法院進行。筆者建議在未來的立法或司法解釋中明確,針對在破產案件受理之前已經啟動的船舶拍賣,海事法院沒有必要中止拍賣。
(二)債權確認和船舶拍賣款分配程序有沖突
1.債權登記、確權訴訟的問題
對于涉船海事債權的登記與確認,無論是根據《海訴法》的規(guī)定,還是根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圍的若干規(guī)定》,海事糾紛應由海事法院專屬管轄。而且,《海訴法》明確規(guī)定,法院發(fā)布船舶拍賣公告之后債權人應當在公告期間申請債權登記,否則視為放棄在本次拍賣船舶價款中受償的權利。據此,海事債權人必須經過向海事法院申請債權登記及提起確權訴訟才可以參與船舶拍賣款的分配。
但是,與船舶拍賣由海事法院管轄不同,船企的破產案件應當由普通法院管轄。《企業(yè)破產法》旨在將與破產有關的財產、案件盡量整合到受理破產案件的普通法院受理。《企業(yè)破產法》第21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有關債務人的民事訴訟,只能向受理破產申請的人民法院提起。”
兩法之間的沖突給當事人帶來了困惑,對于破產船企的船舶拍賣,海事債權人究竟應當向海事法院申請債權登記、參與船款分配,還是應當向破產管理人申請債權登記、向破產法院提起訴訟,抑或應當同時參加兩個法院的債權確認程序。以上問題在法律規(guī)定及司法實務中均無明確的結論。
2.船款分配程序的問題
在正常的船舶拍賣過程中,海事債權人根據《海訴法》的規(guī)定向海事法院申請債權登記、提起確權訴訟,從而在海事法院獲取執(zhí)行依據。根據《海訴法》第117條之規(guī)定,海事法院審理并確認債權后,應當向債權人發(fā)出債權人會議通知書,組織召開債權人會議。
但是,根據《企業(yè)破產法》,普通法院在受理破產程序時,也應當組織召開債權人會議,討論分配企業(yè)的剩余資產。該法第44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時對債務人享有債權的債權人,依照本法規(guī)定的程序行使權利”,第59條規(guī)定:“依法申報債權的債權人為債權人會議的成員,有權參加債權人會議,享有表決權。”根據對《企業(yè)破產法》規(guī)定的文義解釋,自破產申請受理之后,所有債權人必須向普通法院申請參加債權人會議,適用該法規(guī)定的程序進行表決。
兩部法律規(guī)定了相互獨立的債權人會議,都可以審查并確認債權的分配,并且都為債權人參與拍賣價款分配的必經程序。由此帶來以下兩個困惑。
第一,非海事債權人是否有權利參加海事法院組織的債權人會議。對于該問題,目前司法實務中海事法院不同意非海事債權人參加船舶拍賣款分配的債權人會議。但是僅從《海訴法》條文分析,上述做法存在模糊之處。《海訴法》第十章“債權登記與受償程序”共9條規(guī)定,均采用“債權人”的稱謂,而《海訴法解釋》第87條僅規(guī)定,《海訴法》的第111條之中“與被拍賣船舶有關的債權”特指“與被拍賣船舶有關的海事債權”。《海訴法解釋》沒有明確規(guī)定《海訴法》其他條款之中的債權人是否同樣特指海事債權人。
筆者認為,《海訴法》的本意應該是只有海事債權人才能夠參加船舶拍賣款分配的債權人會議。《海訴法》第117條規(guī)定,海事法院審理并確認債權后,應當向債權人發(fā)出債權人會議通知書,組織召開債權人會議。據此,債權人參加會議的方式是由海事法院通知。對于非海事債權人,不需向海事法院申請登記,海事法院亦無法獲知其信息,如何通知其參加會議?因此,非海事債權人參加該債權人會議應當不符合《海訴法》制定時的本意。
第二,海事債權人與非海事債權人的受償位次是否相同。對于該問題,有觀點認為,債權具有平等性,所有債權均應按照順序和比例接受分配,無擔保的海事債權應與其他船舶企業(yè)的普通債權處于相同的受償位次。[3]也有觀點認為,在船舶價款分配時,如果既有與船舶有關的海事請求登記債權,又有與船舶所有人有關但與被拍賣船舶無關的其他債權(包括海事債權與非海事債權)時,應當優(yōu)先分配登記債權,尚有余款的再清償其他債權。后一種觀點的理論依據是,船舶拍賣受償相當于船舶的破產程序,只是大陸法系國家不承認船舶的責任主體地位。[4]
筆者認為,從法理分析,債權具有平等性,海事債權人的受償位次不應高于破產企業(yè)的其他債權人。但是,根據現有法律規(guī)定,只要海事法院的船舶拍賣受償程序與普通法院的破產清算程序相互獨立,兩套債權登記、確權訴訟、債權人會議及價款分配程序就會各自進行。非海事債權人依照《海訴法》難以參加海事法院組織的債權人會議,難以參與船舶價款的分配。
3.解決上述問題的思路
對于上述兩種債權登記及確權訴訟、價款分配程序之間的沖突,筆者建議的解決思路如下。
首先,債權登記應當由破產管理人統(tǒng)一處理。根據《企業(yè)破產法》中破產債權集中申報的規(guī)定,無論海事債權人還是非海事債權人都應該在破產法院指定的期限內向破產管理人申報債權,從而便于破產管理人集中匯總、編制債權登記表。
其次,確認債權的訴訟應當根據案件的不同性質,由普通法院、海事法院分別審理。盡管《企業(yè)破產法》第58條規(guī)定,債權人或者債務人對破產管理人編制的債權登記表有異議的,可以向受理破產申請的人民法院起訴。但是,由于海事訴訟具有特殊性,諸如船舶碰撞、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等案件不宜由普通法院進行實體審理。因此,如有海事債權人、債務人不服破產債權登記表的內容而提起訴訟,筆者建議由海事法院受理相關海事糾紛,發(fā)揮海事法院在專屬管轄案件方面的優(yōu)勢。普通法院、海事法院各自審理非海事糾紛及海事糾紛。
最后,價款分配應當由受理破產案件的法院統(tǒng)一處理。無論是普通法院審理的普通民事案件,還是海事法院審理的海事案件,一切與破產船企有關的債權都應由破產法院進行統(tǒng)一分配。否則,不但會導致兩種債權分配程序的沖突,也容易造成法院之間工作協(xié)調的麻煩。
綜上,由于《海訴法》與《企業(yè)破產法》之間的沖突難以通過法律解釋予以協(xié)調,因此筆者建議未來以立法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債權登記及確權訴訟、價款分配程序采取不同的辦法,區(qū)分處理。不但有利于解決兩種法律之間的沖突,而且可以發(fā)揮法院的各自優(yōu)勢,提高程序效率與可操作性。
三、船舶拍賣先行撥付費用與確權訴訟程序的沖突
根據《海訴法》第119條之規(guī)定,分配船舶價款時有三種先行撥付的費用:應當由責任人承擔的訴訟費用,為保存、拍賣船舶和分配船舶價款產生的費用,以及為債權人的共同利益支付的其他費用。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簡稱《海商法》)第24條也有相同的規(guī)定。上述三類先行撥付費用應當優(yōu)于船舶優(yōu)先權、船舶抵押權等海事債權受償。先行支付費用的種類具體包括船舶看管費用、外輪的邊防監(jiān)管費用、拍賣公告及評估費用、臺風期間的船舶保險費用等。
但是,《海訴法》第十章規(guī)定,海事債權人應當在債權登記公告期內登記債權,并且應當提供債權證據。對于沒有執(zhí)行依據的海事債權人,應當提起確權訴訟。未經債權登記及確權訴訟的債權人,視為放棄在本次拍賣船舶價款中受償的權利。
問題是,實務中大量的先行撥付費用沒有進行債權登記和確權訴訟,但是法院仍然會決定先作支付。事實上,根據先行撥付費用的性質與特點,部分先行撥付費用可以通過債權登記及確權訴訟程序得以認定,亦有部分先行撥付費用難以通過債權登記、確權訴訟程序受償。兩類費用皆有豐富的實例。
例如,對于船舶看管費用,如果扣押船舶上的船員接受法院的委托繼續(xù)看管船舶,則應適用確權訴訟程序。上海海事法院2009年受理的Nordstar輪案,原告系該輪船長,2009年12月29日,法院扣押船舶,此后船長繼續(xù)留船看管。2010年3月1日,船長與案外人簽訂協(xié)議,約定原告繼續(xù)留船看管,直至2011年1月26日法院與買受人辦妥船舶交接手續(xù)。該案法官認為,無論原告的船員雇傭合同是否終止,其自2009年12月30日起的留船看護行為應當視為保存、拍賣船舶而繼續(xù)提供的勞務,該費用應當先行撥付。[5]但是,如果法院未委托船員看護船舶,而是委托與法院有長期船舶看護協(xié)議的船舶看管公司,則通常船舶看管公司會根據長期看護協(xié)議的計費標準、看護期限,與法院結算看護費用,不需另行提起債權登記、確權訴訟。
又如,船舶評估費用、聘請拍賣師的費用、公告費用等,均屬于先行撥付的費用,但是難以通過確權訴訟處理。上述三類費用的數額相對較少,且委托方均是法院,債權人無法通過確權訴訟程序向被執(zhí)行人追索。
再如,部分費用是否屬于先行撥付費用存在模糊之處。有些案件中,在船舶扣押期間出現惡劣天氣,有其他船舶對被扣船實施救助,此后又以“為債權人的共同利益”為由請求對其救助報酬先行撥付。
筆者認為,盡管根據《海訴法》之規(guī)定,債權人未及時登記債權視為放棄在本次拍賣中受償的權利,但是應當兼顧船舶拍賣實務的需要,賦予部分費用免予經過確權訴訟的法律地位。此種先行撥付的費用宜由法律進一步界定,而且原則上應由法院作為委托人負責聯系。同時,法律宜明確規(guī)定,即使是未經確權訴訟的先行撥付費用,也應在債權人會議上進行說明,如有其他債權人提出異議,應當由海事法院或者其上級法院最終認定。
四、船舶拍賣與司法變賣程序的沖突
根據《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經三次拍賣無法成交的不動產或其他財產權且當事人雙方及有關權利人同意變賣的、金銀及其制品、當地市場有公開交易價格的動產、易腐爛變質的物品、季節(jié)性商品、保管困難或者保管費用過高的物品,人民法院可以決定變賣。
但是,《海訴法》在制定之時沒有考慮到司法變賣的問題,未明確司法變賣的程序規(guī)則,導致司法變賣的法律地位不明,致使買受人和法院存在以下法律風險。
(一)司法變賣的適用條件不明
《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規(guī)定的司法變賣的適用條件較為寬泛,既可以因為多次流拍而適用,也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約定而適用,還可以因保管費用過高等原因由法院依職權采用。但是,《海訴法》僅規(guī)定了船舶拍賣,根據該法第29條之規(guī)定:“船舶扣押期間屆滿,被請求人不提供擔保,而且船舶不宜繼續(xù)扣押的,海事請求人可以在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后,向扣押船舶的海事法院申請拍賣船舶。”該規(guī)定對船舶司法拍賣的實施條件規(guī)定得相對嚴苛。
盡管《海訴法》之中沒有船舶變賣的規(guī)定,但由于實務需要,海事法院在實際操作中大量采用了船舶變賣方式,其援引的法律依據就是《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船舶售價大幅下降,船舶司法變賣有著更突出的程序價值。
針對《海訴法》嚴格的船舶拍賣條件,對比《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之中相對寬泛的變賣條件,筆者建議:第一,應當限制船舶司法變賣的適用條件。《海訴法》對船舶拍賣的條件限制較嚴,體現了立法態(tài)度,即只有在請求人或被請求人申請拍賣船舶的前提下,法院才能采用司法拍賣程序。同理,船舶司法變賣也應當由請求人或被請求人申請啟動,不能按照《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由海事法院依職權采用。第二,司法變賣是在船舶拍賣出現流拍,為減少看管成本及風險而采用的變通做法。船舶司法拍賣是司法變賣的必經程序,不能按照《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由債權人或債務人經協(xié)商直接適用。第三,至于司法變賣之前應經過的流拍次數,筆者認為可以允許法院視船價高低予以變通。對于評估價格較高的船舶,應當沿用目前海事法院的做法,經過三次拍賣的流拍之后,再啟動司法變賣程序。而對于評估價較低,例如50萬元以下的船舶,以及因氣象、船況、市場行情等因素不宜長期扣押的船舶,可以規(guī)定適當放寬至一次流拍即可轉入變賣程序。
(二)司法變賣的法律后果不清
根據《海商法》的規(guī)定,船舶優(yōu)先權應當通過法院扣押船舶行使,并可通過法院強制出售船舶而消滅。同理,船舶抵押權、船舶留置權等其他擔保物權也可以通過法院拍賣船舶而消滅。《海訴法》規(guī)定與《海商法》相一致,僅規(guī)定了船舶拍賣程序。2005年生效的《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順應了司法實踐需要,對多次流拍的財產允許采用法院組織變賣的方式變現。而且,在操作流程上,法院需要發(fā)布變賣公告,限制變賣成交價格等。
但是,《海商法》和《海訴法》均未考慮司法變賣的問題,而如果法院采用司法變賣的方式,是否可以消除船舶所附的優(yōu)先權等擔保物權?
在實務中,由于司法變賣對法院處理財產有積極作用,有些海事法院在變賣船舶的《所有權轉移證明書》中會載明:“買方對船舶移交以前所負的債務不承擔任何責任。原船舶登記所有人的相關證書予以注銷。”買受人憑該證明向海事局辦理船舶過戶登記手續(xù)。假如法院簽發(fā)的《所有權轉移證明書》未載明買受人不承擔移交前債務,買受人在海事局辦理過戶手續(xù)之時會面臨極大的障礙,且買受人日后還有需面對船舶優(yōu)先權人索賠的隱形風險。《海商法》《海訴法》都沒有授予司法變賣相應的法律地位,現有法律依據不足以認定買受人購得的船舶是清除了船舶優(yōu)先權等負擔的“干凈船”。在筆者參與的船舶變賣案件中,已經出現過當事人就此產生爭議的案例。
筆者認為,司法變賣是在多次流拍之后,通過法院參照拍賣程序,通過公告、以最后一次拍賣的保留價成交。司法變賣制度是司法拍賣制度的必要補充,可豐富法院的執(zhí)行措施,利于緩解多輪流拍給當事人和法院帶來的經濟負擔和工作負擔。如果法律不能賦予船舶司法變賣與船舶拍賣相同的法律地位,將嚴重影響司法變賣的程序價值。但是,現有的法律規(guī)定不能賦予船舶司法變賣買受人相應權利,給買受人乃至法院都帶來了風險,只能有待法律修改或制定司法解釋時再予調整。
五、結語
由于《海訴法》及其司法解釋中船舶拍賣的規(guī)定過于原則,導致在實務中需要同時適用《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等法律規(guī)范作為補充。但是,由于船舶司法拍賣程序的特殊性,其它民事規(guī)范中的程序性規(guī)定難以與其兼容,在并用多種法律規(guī)范時會出現諸多的法律沖突。很多沖突無法通過對現有法律規(guī)范進行解釋而予以解決,而海事法院在操作中采用的變通做法又往往欠缺法律依據。綜上,筆者建議未來由法律或司法解釋作出針對性的規(guī)定解決相關問題,并且對解決問題的方案提出參考性的意見。對此總結如下。
第一,船舶拍賣與流拍財產再次拍賣規(guī)定之間的沖突。一是船舶拍賣公告期限不兼容。《海訴法》沒有考慮到流拍及再次拍賣的后續(xù)程序,而《最高院拍賣變賣規(guī)定》沒有規(guī)定再次拍賣的公告期限、通知期限等。出于船舶拍賣效率性的需要,有必要在未來的立法中明確船舶多輪拍賣之間的時間間隔,以一周為宜。二是船舶拍賣次數限定脫離現實經濟效率需求。建議日后出臺法律或者司法解釋作出調整,賦予法院一定的裁量權,授權法院考量船舶價值、船舶類型、船舶看管成本、船舶狀態(tài)、市場行情等因素,根據實際需要決定拍賣次數或者是否進行拍賣,實現減少船舶拍賣成本、提高經濟效率、維護當事人利益的立法意圖。
第二,船舶拍賣款分配程序與破產程序的沖突。一是船舶拍賣后續(xù)規(guī)定不同。《企業(yè)破產法》規(guī)定,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有關債務人財產的保全措施應當解除,執(zhí)行程序應當中止,這與《海訴法》規(guī)定截然相反。鑒于船舶拍賣強烈的技術性特征以及現行海事法院專屬管轄的專業(yè)性,建議在未來的立法或司法解釋中明確,針對在破產案件受理之前已經啟動的船舶拍賣,海事法院沒有必要中止拍賣。二是債權確認和船舶拍賣船款分配程序存在沖突。《海訴法》和《企業(yè)破產法》都規(guī)定了相互獨立的債權人會議,都可以審查并確認債權的分配,并且都為債權人參與拍賣價款分配的必經程序。非海事債權人是否有權利參加海事法院組織的債權人會議,海事債權人與非海事債權人的受償位次是否相同,成為該沖突下的法律問題。為發(fā)揮法院的各自優(yōu)勢,提高程序效率與可操作性,建議未來以立法或司法解釋的形式,確認債權登記應當由破產管理人統(tǒng)一處理,確認普通法院、海事法院各自審理非海事糾紛及海事糾紛,發(fā)揮專業(yè)優(yōu)勢。債權的訴訟應當根據案件的不同性質,由普通法院、海事法院分別審理,明確船舶拍賣價款分配應當由受理破產案件的法院統(tǒng)一處理。
第三,船舶拍賣先行撥付費用與確權訴訟程序的沖突。《海訴法》規(guī)定債權人未及時登記債權視為放棄在本次拍賣中受償的權利,但有部分先行撥付費用難以通過債權登記、確權訴訟程序受償。為兼顧船舶拍賣實務的需要,應賦予部分先行費用免予經過確權訴訟的法律地位,此種先行撥付的費用宜由法律進一步界定,而且原則上應由法院作為委托人負責聯系。同時,為維護其他債權人權益,法律宜明確規(guī)定,即使是未經確權訴訟的先行撥付費用,也應在債權人會議上進行說明,如有其他債權人提出異議,應當由海事法院或者其上級法院最終認定。
第四,船舶拍賣與司法變賣程序的沖突。《海訴法》在制定之時沒有考慮到司法變賣的問題,未明確司法變賣的程序規(guī)則,導致船舶司法變賣的法律地位不明。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船舶司法變賣的適用條件不明,二是船舶司法變賣的法律后果不清。司法變賣制度是司法拍賣制度的必要補充,應通過立法程序賦予船舶司法變賣與船舶拍賣相同的法律地位,確認船舶司法變賣的程序價值。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伍載陽,劉喬發(fā).船舶拍賣實務問題研究[J].法律適用,2002(5):49-52.
WU Zai-yang,LIU Qiao-fa.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ship’s auction[J].Journal of Law Application,2002(5):49-52.(in Chinese)
[2]陳斌,黃青男.試析地方人民法院委托海事法院拍賣船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法律適用,2005(1):80.
CHEN Bin,HUANG Qing-nan.Probe into problems and measures when local court entrusted maritime court to auction the ship[J].Journal of Law Application,2005(1):80.(in Chinese)
[3]孟強.單船公司破產債權受償順序問題研究[J].中國商法年刊,2008:66-73.
MENG Qiang.Research on the compensation sequence in the procedure of single ship company’s bankruptcy[J].Chinese Yearbook of Commercial Law,2008:66-73. (in Chinese)
[4]鄭秉物.執(zhí)行程序中船舶價款的分配[J].中國海商法年刊,2009(4):89-94.
ZHENG Bing-wu.The distribution of ship’s auction proceeds in court’s execution procedure[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09 (4):89-94.(in Chinese)
[5]陶冶.船員追討船舶看護費用贏官司[N].中國水運報,2011-12-19(3).
TAO Ye.Seafarers won the litigation for claiming reward on watching over the ship[N].China Water Transport,2011-12-19(3).(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