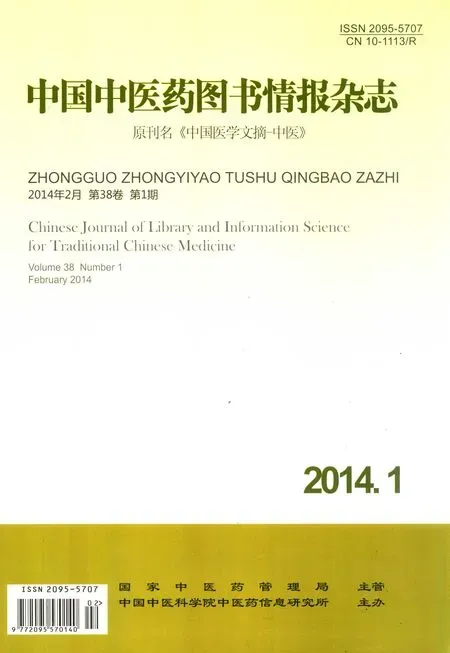對中醫發展的哲學思辨
王松俊
軍事醫學科學院衛生勤務與醫學情報研究所,北京 100850
對中醫發展的哲學思辨
王松俊
軍事醫學科學院衛生勤務與醫學情報研究所,北京 100850
文章就中醫發展中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哲學層面的探討,包括中醫的“觀念”能夠被現代“轉譯”嗎,“關系實在論”能夠替代“實體本體論”嗎,真能以系統科學重構中醫理論嗎,真能用復雜系統科學解釋中醫理論嗎,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是中醫藥的救命稻草嗎,“分子中醫藥學”能救中醫嗎,到底什么才是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中醫科學研究何去何從。文章認為,中醫發展的道路仍不清晰,還需繼續求索。
中醫;哲學
中醫科學性爭鳴的目的是為了尋找中醫的科學規律,更是為了遵循科學規律發展中醫。
1 中醫的“觀念”是否能夠被現代“轉譯”
其一是中醫的“整體觀念”能被現代“轉譯”嗎?整體地考察人的生命與疾病,無疑也是一種可取的認識方法。就像以信息論的方法來認識某個事物一樣,同樣可以忽略事物的結構性質,而僅以信息的產生、傳播、存儲、加工、分發、接收、應用、反饋等等環節為主要認識指針,來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但是,無論以何種方式去認識事物,都必須以他人能夠理解和接收的方式來加以闡釋,并得到認同,才能成為共識。也就是說,科學的知識特征,可能具有獨特性;但是,科學的認識特征,不應具有孤立和排他性。無論對于現代科學,還是對待中醫而言,現代科學知識的豐富程度都毫無疑問地遠遠超過古代,以現代通用的科學語言將中醫闡釋為可為科學共同體理和接受的概念、原理,為什么如此困難。到底是中醫自身的問題,還是這個“轉譯”過程的問題,還是根本就不能實現“轉譯”?
其二是中醫的“自然觀念”能被現代“轉譯”嗎?中醫強調宇宙萬物的共性及其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強調認識人的生命與疾病時需要聯系天文和地文,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盡管相互聯系的哲學思想是正確的,但是,其比附方式和語言,是非常牽強附會的。而現代有些“中醫”,還在為證明這種比附的“正確性”而辯護,則是極為荒唐的。如果我們對經典甚至已經失去考究的態度、懷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氣,而將經典教條化,成為本本主義者、唯古唯經者,那么中醫也就真的沒有希望了。
其三是中醫的“實用觀念”能被現代“轉譯”嗎?中醫的豐富臨證經驗和大量醫藥實踐,之所以沒有成為集理論、方法、技術于一身,融基礎、應用、標準于一體的學問,與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有關,也與近代中國的科學落后有關,更與中醫接受近代和現代科學的程度有關。中醫確懷“究天人之際”的思想,但“通今之變”嚴重不足。
其四是中醫的“直覺觀念”是中醫學這座“大廈”在地基上的嚴重缺陷。只有當中醫的“陰陽”、“氣血”、“臟腑”、“經絡”、“五行”、“八綱”、“三焦”、“四診”能夠被現代科學所闡明并被證明科學理性,中醫才能真正地科學化,也才能現代化和國際化[1]。
2 “關系實在論”是否能夠替代“實體本體論”
有中醫學者從哲學基礎和物質科學的層次,深入探討了物質的“第一性的質”與“第二性的質”之間的關系,強調了以“關系實在論”代替“實體本體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暗示了“關系實在論”是對中醫“關系”理論的哲學理論支持。這個問題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復雜,值得認真研究。
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響我們認識中醫的中心或“焦點”是應該放在“實體”還是“關系”,甚至決定中醫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研究的“重心”。其復雜性在于上述論述中有不少問題還沒有理清。一是,“以現代科學、數學和邏輯學的發展為基礎的關系實在論”與中國古代形成的中醫的所謂“關系”理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既不同質,也不同類,也就是說,從邏輯學上講,既不可比較,也不可類比。現代的所謂“關系實在論”是能夠通過科學哲學的語言使人明白的“關系論”。而中醫理論的“關系論”則是不能夠通過現代科學哲學的語言使人明白的“關系論”。二是,“關系實在論”強調“第一性的質”和“第二性的質”之間的相互關系會發生變化,肯定“關系實在”的同時并不否認所有“關系”都是物質的屬性,也就是說,并非因為重視“關系”而忽視“實體”,相反,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能夠認識實體的應該、也必然是首先認識實體,而只有當不能認識實體或者實體模糊時,才通過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去“認識”這種存在的“關系”,從而推論可能潛在存在的物質。三是,作者將“系統中心論是系統論的一個重要觀點”作為“科學研究的重心從實體轉向關系”的一條重要論據,值得商榷。因為科學系統論在強調“系統”的關系觀念的同時,并沒有忽視系統的結構,即所謂“部分”。科學系統論強調,必須至少從系統特征、系統結構、系統功能(以及結構與功能的關系)、系統環境、系統演化等方面去認識系統,才能算是“系統”地認識。因此,第四,“以關系為立足點,破實體本體論,貫徹非實體主義,的確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到了東方”的立論不能成立。“關系實在論”并非出于東方,其“以現代科學、數學和邏輯學的發展為基礎”也完全不同于東方思想,也就根本談不上什么“回歸”。
現代所謂的“關系實在論”對于我們認識中醫,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可借鑒的思想方法;“關系實在論”可以作為“實體本體論”的認識論層面上的重要補充,但絕不是取代。就像認識西瓜可以直接認識和解剖認識,而沒有必要從種子、土壤、氣候、水分等去推想、猜測,但是目前認識宇宙爆炸卻只能根據有限的科學觀察和“關系”去推測一樣。不可能離開“實體”去表述“關系”。“實體本體論”與“關系實在論”并不矛盾,而且必須共存、互為補充。
那種所謂的“西醫就是將人看成機器”的認識,與將江湖騙子看成中醫代表的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是同樣可怕的偏見。現代醫學從來也沒有將不同的系統、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組織、不同的細胞、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功能大分子、不同的電解質和元素等,看成是毫不相干的孤立存在,即使在其發展過程中,現代醫學也一直坦然承認認識的局限性,并不否認相互聯系以及潛在聯系的可能,從不認為探索已經到頭,而是一直在進行不懈的探索。
3 能否以系統科學重構中醫理論
不少知名學者提出用系統科學思想重構中醫理論體系的設想。未來構建的所謂中醫系統論體系很可能是,中醫概念意義上的心、肝、脾、肺、腎等“藏象”似乎是系統的模糊結構,相生相克似乎是系統的結構功能關系,風、寒、暑、濕、燥、火等似乎是系統的環境影響因素,衛、氣、營、血等似乎是系統的層次,天時明晦、七情六欲等似乎是系統的狀態,如此等等。
但是,在哲學層次的問題仍然存在,即系統科學所謂的“系統結構”是否也還包括所謂還原論的認識論意義上的“結構”概念呢?如果是,那么“系統結構”仍然難以描述清晰,系統結構與系統功能的關系也就描述不清楚,所謂系統論也仍然無法系統地論,也就不是系統論。看來,要真正從理論上構建起完善的、經得起推敲的中醫學系統論體系,可能還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研究探索,包括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結構與功能關系、系統特征、系統環境、系統演化等。
4 能否用復雜系統科學解釋中醫理論
朱清時院士于2006年11月提出“復雜系統科學與中醫學可以交匯”,“可以運用復雜系統科學和耗散結構理論證明中醫不僅是科學,而且其治病的有效性也是必然的”。朱先生對“五行”的比附和解釋都是極為牽強的猜測。
朱先生點準了中醫存廢之爭的穴位,即中醫以其固有的中醫理論體系去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其前提就是已經默認了五行學說的正確性。而中醫存廢之爭的關鍵恰恰是作為中醫理論基礎的五行學說自身是否有科學依據的問題。先生提出的耗散結構理論的四個條件或五個要素可以理解,但中醫的五行說為什么是五行,不是六行?有形部分為什么就單是金、木、水、土,沒有石?無形部分為什么偏是火,不是氣?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出現頻度和地位恐怕都遠超過火,難道氣不重要?朱先生的這種論證,與他上面所批評的“從中醫的角度來說明其科學性”所犯錯誤相同,即以承認五行學說為前提,而不是論證為什么有五行學說。因此,朱先生所論證的命題仍然是一個假命題。至于稱“五個要素”與“五行說”和“五個器官”(應是“五臟”)的對應“這是科學的必然”,更是值得慎重考慮,似乎太過輕率。人體符合耗散結構的系統特征和復雜性的系統特征,并不等于“五臟”、“五行”和耗散系統“五要素”的類比正確,更不能說明“這是科學的必然”。將或然說成必然,不是科學精神所提倡的。
雖然用耗散結構理論和復雜系統科學來論證中醫理論的思想方法可能可行,也可能有效,既有助于我們用現代科學的思維方式去認識中醫,并有可能因此而清晰并鞏固中醫理論基礎,為中醫的現代化指出了一條值得認真探索的途徑,但是,定論還為時過早。
5 中醫藥的救命稻草是否是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
自1999年3月在北京召開中醫藥與基因組學研討會以來,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確實對生命科學領域的科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改變了基因-表達產物-疾病之間的線性相關研究,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生命科學領域的復雜相關性研究的方法論的進步。中醫藥研究與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基因芯片技術等之間的結合也已成為中醫藥現代化研究的重要熱點領域。
值得深入探討的是,這樣的相結合研究所獲得的結果,以及這些結果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否還符合我們對中醫藥科學研究發展方向的初衷,是否有助于中醫藥理論或其科學性的證實,是否有助于中醫藥科學理論的豐富,是否有助于中醫所謂的“以中醫理論為基礎的真正的中藥組方”的確證?還是在此結合中,中醫藥只是配角,僅僅起到提供一個最初的線索、一個初步的可能、一個大致范圍,而后來的研究指針、觀察指標、研究結果、結果闡釋、研究結論、結論應用、應用成果、產品方式、理論豐富等等,均與中醫藥無關,充其量是“受中國傳統中醫藥的某經典驗方的啟示,通過基因組學和蛋白質學等研究,精取其中若干種有效成分,研制成功治療何病的新藥,取得如何的經濟效益,甚至打入國際主流市場等等”。實際上,這樣的新藥已經不是中醫意義的中藥,也不能說明相關中醫臨證理論。至于相關的中醫理論是否正確,相關的辨證施治是否合理,相關的處方組合是否科學等等事關中醫的理論是否科學的若干重要問題,均無人關心,也無人回答,充其量“對中藥復方的作用機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也還只是“驗藥”。如果如此,這還叫不叫中醫藥現代化?還能不能稱之為中醫藥研究的方向?
當然,對于從事新藥研發的藥學家和找藥人而言,從中醫藥傳統醫學寶庫中尋求靈感以發現新藥,這種藥學科學研究的思路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應該積極鼓勵的。但是對于以發展中醫藥為歷史使命的中醫藥仁人而言,則思考問題的角度并不能如此。既然我們已經找到了“中醫學與基因組學相結合”這樣一個結合點和出發點,我們也還需要以中醫藥自身發展為使命來定好期望目標,以期結果與初衷的一致。
中醫與中藥的確可以分而研之。事實上,中藥學應該也可以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不必遙遙無期地等待中醫得到科學化的實證后再開展中藥現代化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認為,這樣的中藥學研究就代表了中醫藥現代化,更不能說這就代表了中醫的現代化。
當然我們采取“首先實證中醫藥的實踐效果,然后再逐步闡明中醫藥理論的科學性”這樣的策略也是完全可以的。中醫藥的實踐效果對于實證中醫藥理論的科學性而言確是必要條件,問題是中醫藥的實踐效果能否成為反推中醫藥理論科學性的充分的邏輯需求?顯然是不能的,因為效果良好并不是證明方法正確、理論科學的充分邏輯。那么,如何才能“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呢?到底什么才是“中醫藥現代化”呢?是我們闡明了中醫藥治療某些重大疾病的機制,即為中醫藥現代化,還是證明中醫藥理論的科學性才算是中醫藥現代化呢?也就是說,我們中醫藥所面臨的重大基礎科學問題到底是,在中醫藥的支流上去尋找其與現代生命科學的共同交匯點,以“證明”中醫藥某些實踐效果的科學性;還是要從中醫藥的根本、起源、主流上去證明其科學性呢?
6 “分子中醫藥學”能否救中醫
仔細推敲“中藥作用的分子網絡調節理論”,存在太多疑問。根據已有中藥藥理和現代分子生物學知識,“中藥的藥效物質是有效分子組合”,“疾病和證候是分子網絡紊亂的結果和表現”,“中藥治療疾病和病證的作用機制是分子網絡調節”,即該研究的所謂三大支柱性的理論基礎并不玄乎。問題不在于這三點能否成立,而在于按照此技術路線和方法設想,能否真正揭示出哪些是有效分子組合?哪些則是無效分子?分子網絡到底是如何紊亂?紊亂成什么樣了?應該如何調節?而中藥的所謂有效分子組合又是如何調節的?這樣的調節是不是就是最佳調節?如何證明它就是最佳調節?……這樣一項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存在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即使我們能夠弄清并證明某復方的有效分子組合,也能夠證明其所謂有效分子組合確實能夠起到所謂的網絡調節作用,我們又如何能夠說明這些有效分子所發揮的調節作用就是并且都是治療所需要和期望的?有什么樣的調節是根本沒有必要的?還有什么樣的調節是必須的而又是有效組合所不具備的?如果我們不能證明這些,那么研究結果除了能夠證明某中藥復方確實存在一組分子,它們有些在體內發揮了作用,其中有一些是有治療作用的有效分子,它們在調節機體紊亂狀態中發揮了作用之外,對于此方是否科學,是否合理,不合理的原因是否是臨證辨證的醫理問題?即研究者所期望的所謂“以藥帶醫”,似乎并無太大幫助。
現代分子生物學已經闡明了多個分子針對一個靶點,以及一個分子針對多個靶點的現象存在,因此,“分子網絡調節的理論體系”其實并沒有什么太多的新內涵。分子網絡調節水平的藥物,主要依賴于分子生物學闡明分子水平的生命科學機制。中醫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存在和發展,取決于其思想和理論的科學性得以證明,而非“分子中醫學”的建立和發展。中醫理論的科學性是中醫學一切分支、演化和派生學科存在的前提,離開中醫理論科學性的所有分支學科都是無本之末和空中樓閣。
7 到底什么才是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
中醫藥的“國際化”與中醫藥“現代化”,在時間軸上是同步的,只是在空間軸上有不同。中醫藥的現代化更加強調首先解決科學性問題,而中醫藥的國際化則更加看重經濟性問題。當然,中醫藥的國際化必須以科學性為前提。因此,在中醫藥現代化的辯證中,更多的是定性的問題,而在中醫藥國際化的辯證中,更多地需要定量的說明。中醫藥的現代化是基礎、是前提,必須首先解決現代化問題,然后才能真正地走向國際化,否則仍然不是真正的國際化,而是被國際邊緣化、另類化。
中醫藥國際化涉及的問題不僅是產業規模和鄰國挑戰。何謂“國際化”,是國際市場貨架上擁有中藥即視為國際化,還是中藥出口比例達到多少才為國際化?是僅僅中藥能夠國際化,還是中醫科學必須國際化?還是不管你屬于中醫藥的哪個行當,誰能“國際”誰就“國際”?到底是中醫藥文化國際化,中醫藥消費者國際化,還是中藥標準國際化,中藥產品國際市場化?還是不管是啥,走出國門就都是國際化?
對于日本等國的研究而言,“中藥”產品是大事,它關系到市場和經濟效益;但是,對于中國而言,“中藥”產品是大事,“中醫”是更大的事,它關系到傳統、文化、情感,并影響科學、社會、政治。
中藥毒性是中藥現代化和國際化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的重大問題。對于中藥毒性,既不應該是因噎廢食的全否定,也不應該是我行我素的無所謂。從普遍意義上講,需要加強中藥的毒理研究,闡明有毒中藥的毒性成分及其應用控制;需要將有關毒性中藥的知識充實到中醫院校教育和中醫師繼續教育中去,以提高中醫臨證處方的安全性;需要將中藥毒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實到中國藥典中去,使其成為一種對中醫臨證處方的法律約束;需要加強中成藥的毒副作用的毒理學研究和質量穩定性控制和標準化控制,以提高市場中成藥商品的安全性;需要加強中藥和中成藥的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及時發現問題以中止更大范圍的傷害事件發生;需要提高公眾對中醫藥的認識和相關知識素養,正確規范用藥。
“中藥基因組計劃”是新藥研發的一條現代化的可行途徑。但是,它是不是“中藥”現代化的“轉折點”、“里程碑”、“革命”和“重大戰略措施”,都還很值得商榷。“中藥現代化”的定義還很值得商榷,就連這一提法目前也仍然還存在許多爭議。首先,必須明確,雖然中藥也有單味藥治病,但它有別于植化單體藥。其次,中藥是指基于中醫理論臨證基礎上的方藥,而不是指中國的藥。再次,中藥的現代化,也不僅是幾個經典驗方的現代化。因此,中藥現代化必須建立在中醫理論現代化的基礎之上,如果中醫的臨證理論都不能成立,中藥的現代化也就不是中醫的中藥現代化。也就是說,真正的中藥現代化,必須首先是作為其基礎的中醫理論的現代化。當然,中醫理論的現代化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和問題,在此之前,中藥也并非只能坐等,可以、也完全應該、甚至必須嘗試開辟新的道路,但是,那只可以稱之為基于中藥材的新藥研發,而不是中藥現代化。
“本草物質組計劃”可以從現代生物學的組學角度去研究中藥、尤其是中藥復方的有效成分與治病的物質基礎,無疑是以現代方法證明中藥方劑科學性的有效途徑。對此,我是完全贊成的,但也許正是傳統中醫藥者所反對的。如果這一重大科學計劃的研究結果能夠證明某些方劑是符合現代科學的也還罷了,傳統中醫藥堅持者肯定會歡迎并以此證明自己的一套中醫科學如何有理有據。但是,如果證明某些方劑含有大量相反作用的成分,甚至毒性藥物成分,我們又當如何?你可以將其中的有效物質成分做成符合現代科學技術規范的藥物,叫一個新的名字,成為一個新藥,甚至打入國際市場,為國家的所謂新藥研發的原始科技創新和自主知識產權做出貢獻,難道你還能否定中醫藥方劑不成?你是能改造中醫藥經典的“六味地黃”,還是能改造“附桂八味”?那是經典,那是不容染指改造、甚至口頭批評的。“我中醫藥是按中醫的一套科學理論辨證施治的,你憑什么用你那所謂的科學來驗證或者改造我?”既然如此,那“本草物質組計劃”龐大的工程對于中醫理論的作用就需要認真思考了。雖然“本草物質組計劃”高舉中醫藥理論大旗,但其中并沒有一句真正涉及中醫理論。
從中醫藥傳統經典方劑中去尋找“新藥”的思路,是找藥人的一條可選的正確道路,但并不是中醫藥科學的出路。雖然中藥可以離開中醫而獨立存在,那樣的中藥也仍然是“中藥”,但已不再是“中醫的藥”,而是“中國的藥”。
中藥現代化研究,“本草物質組計劃”是一種選擇。中醫藥現代化何往?“本草物質組計劃”并非答案。中醫藥同仁仍然需要繼續探索。
2008年1月頒布實施的《中藥注冊管理補充規定》,出臺的目的是從政策層面給民族醫藥的藥品研制在現行藥品嚴格監管的法制體系上打開了一扇方便之門,使民族醫藥的藥品研制在國家監管體系內合法化,從而保護和鼓勵民族醫藥發展。該補充規定特別強調了“古代經典名方”、“中藥復方”、“主治為癥候”、“疑難病癥”等,坦然承認了民族醫藥區別于現代科學技術范疇下醫藥研發的自身特殊性,重點鼓勵民族醫藥在疑難雜癥和尚無有效現代醫藥治療手段的疾病防治方面進行探索,提示了所給出的政策“方便”缺口的有限性。該補充規定并沒有、也不能就其政策的科學性做出說明,也無法得到國際醫藥界的認同,也就是說,無助于其科學性和國際化進程。
8 中醫科學研究何去何從
既然中醫不能孤立于現代科學的“道”之外孤芳自賞,那么,中醫和現代醫學如何才能溝通并走向融合?必須尋找到能夠考量其理論、方法、技術、實踐、效果等的共同準則,而這個共同準則的基礎恰恰只能是科學觀。
中醫存廢之爭,實為中醫是不是科學之爭。要回答中醫是不是科學,必須首先回答科學是什么?什么才是科學?要回答清楚這兩個問題,必須重新檢視科學觀。
基于社會建構主義的科學觀,對于中醫而言,還很難以說清是福是禍。中醫是醫藥衛生資源獲取的自由競爭中的弱者,但同時也是行政保護轉化資源的享有者。
中醫藥體系是含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思維科學的混和體,其中有科學成分,有文化成分,也不必諱言有迷信成分。中醫藥體系的這種多元性,也必然地決定了其走向多向化,即一支走向科學,一支走向文化,而迷信則自生自滅。
與其將中醫藥作為一個大包裹,說文化不全文化,說科學不全科學,說迷信不全迷信,說不清、道不明,倒不如將這個巨大的“混和體”進行分離、萃取,將科學的成分劃歸科學,按照科學發展的規律,將其科學化、現代化,甚至于國際化,不斷發展、發揚、光大;將文化的成分劃歸文化,并且系統化,加以繼承;將迷信的成分,作為一種曾經的對人類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影響巨大的歷史存在,以文化遺產的形式加以保護,成為記憶。這也許才是中醫藥的最后歸宿,也是我們對于中醫藥的帶有強烈民族感情和現代科學精神的理性選擇。但是,更多的擔心是,這種看似理性的想法會不會因此而解構了中醫特有的所謂整體性和文化特性。
中醫藥現代化應該是讓現代人能夠理解中醫藥,讓現代人能夠認同中醫藥,讓現代人能夠接受中醫藥。那么,如何才能讓現代人能夠理解、認同、接受中醫藥呢?首先,要面向現代人,用現代人能夠聽懂、看懂、理解的語匯來詮釋中醫的思想、理論、方法和技術;其次,要面向而不是回避現代科學技術,證明中醫藥的科學性特征。現代醫學模式已經證明,任何醫藥都不僅具有科學特征,還同時具有文化特征。但是,任何醫學形式,僅有文化特征是不夠的,也是不可能被認同和接受的,必須同時具有科學特征。
目前的中醫藥現代化口號很響,決心很大,熱情很高,行動很亂。中醫藥科學研究的目的、使命、任務、方向、目標、重點、課題、途徑、手段、技術、工具、成果、應用、效益、科學價值、人文精神、哲學貢獻到底應該是什么?什么樣的成果才算得上是對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發揮重要作用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國家應該鼓勵、支持、獎勵、導向什么樣的科學研究和成果?如此等等,有太多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刻思考。
9 中醫發展的道路仍需繼續求索
中醫的發展面臨著兩難。一方面是堅持以中醫理論為本體,才不致在發展中迷失自己,才能保證中醫體系不被解構。另一方面是在中醫理論本體的科學性未能達成共識之前,中醫的臨床實踐與臨床研究還得繼續,中藥的發展也不能停步。而這些不同方向的突破,事實上已經證明,它們并沒有、也不可能將中醫現代研究的方向,導向中醫理論體系本體的科學性研究。而中醫學發展最艱巨的任務恰恰就是中醫理論本體的科學性問題。以振興中醫、弘揚中醫為己任的廣大中醫藥仁人志士,是絕對不會僅僅因為從中醫藥“寶庫”中拿來一件寶貝而沾沾自喜的。也就是說,盡管受中醫經典驗方的啟示可以從組方的若干種成分中提取出有限的幾種有效成分研制成治療藥物,甚至“走向世界”,但是,像這樣的“中藥”并非中醫理論意義上的中藥,這樣的研究也無助于中醫理論本體科學性的證明,這樣的發展還不是中醫的發展。
中醫的發展必須開放。中醫的整體性不應該拒絕現代醫學的還原性,中醫的模糊性不應該拒絕現代醫學的清晰性,中醫的主觀經驗不應該拒絕現代醫學的客觀理據。開放就是從不拒絕到接納、吸收,再到融合。中醫的病機、病理、病因、藥理等現代研究,都還有相當艱巨的任務。無論是現代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免疫學、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還是現代藥理學、藥物化學、藥物基因組學,都可以為中醫、中藥的研究和發展所用。問題在于如何才能處理好“堅持中醫理論的本體性”與“以現代科學和技術為工具”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既要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手段,又要不背棄中醫理論的思想方法。這也恰恰是發展過程中的難題所在。
現代醫學應該、也需要給包括中醫在內的所有傳統醫學以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使其本著科學的精神,向著為人民健康服務這一共同目標,循著科學的道路,繼續在探索中發展。
中醫的科學發展,還需要繼續求索。
[1]王松俊.辨證中醫:對生命的哲學思考[M].北京: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2008.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Wang Songjun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CM can be Translated in modern manner, whether Physical Ontology can be replaced by Relation Realism, whether the TCM theory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systemic science or interpreted by complicated systemic science, whethe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can serve as straws for TCM, whether Molecular TCM and Pharmacology can save it, what is the re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f TCM and Pharmacology and which is the way for TCM study. It i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s still unclear and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TCM; philosophy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1
王松俊,研究員,研究方向:醫藥科技發展戰略,科研管理,醫學科技情報。E-mail: wangsjamms@sohu.com
2013-04-08,編輯: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