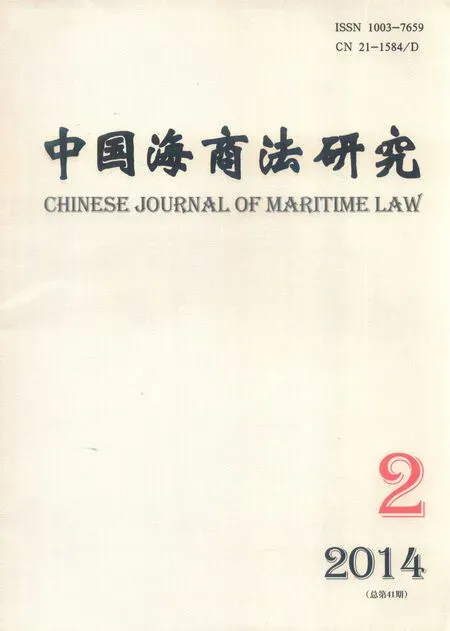船舶融資租賃糾紛法律適用問題研究①
蔡志萍,張 昕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天津 300100)
融資租賃(financial leasing)的雛形于19世紀末產生于美國的費城與紐約的鐵路機車融資實踐中。[1]以1952年美國租賃公司組建為標志,融資租賃成型并迅速推廣。[2]融資租賃微觀上兼具融資、融物功能,可促進生產、銷售及資金合理使用,實現供貨人、出租人、承租人三方共贏;宏觀上則可刺激市場內需、擴大出口、增加投資、擴展就業,[3]故獲得世界各國的普遍歡迎。在中國,1980年中國東方租賃公司與中國租賃公司先后成立,三十余年來,融資租賃業已成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近年來受完善稅收抵免、加速折舊、出口退稅等政策刺激,中國融資租賃行業迅速復興。據統計顯示,截至2012年底,全國在冊運營的各類融資租賃公司(不含單一項目融資租賃公司)共560家,相較2012年初增加264家,尤以外商租賃增長為多,達到約460家,比上年增加250家。在業務總量上,全國融資租賃合同余額約為15 500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度9 300億元增加約6 200億元。[3]隨著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和金融創新的推進,天津融資租賃業近年來發展迅速,已逐漸成為全國融資租賃行業領先地區,2012年底中國融資租賃十強共13家企業中,注冊地在天津的企業即有5家,占38.46%。預計在天津市綜合改革創新區的建設過程中,融資租賃行業將繼續發揮強大的推動作用。
由于船舶建造成本大、耗時長,需要大量資本支持,而近年來航運市場極不景氣,傳統信貸渠道輸血不暢,航運企業迫切需要其他融資途徑支持。在融資租賃業復興的背景下,船舶融資租賃(簡稱船舶融租)具有不可限量的前景。但行業發展有機遇也有挑戰。尤其應清醒地看到,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備,是船舶融租業進一步發展面臨的規則性風險。相關部門多年來一直推動《融資租賃法》進入立法項目。而最高人民法院也試圖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規范裁判尺度,2012年3月正式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簡稱《融租解釋草案》)。近年來,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簡稱天津高院)為配合中央工作,一方面大力進行相關制度的探索性建設,出臺《關于審理融資租賃物權屬爭議案件的指導意見》(簡稱《天津指導意見》),試圖推動天津地區船舶融租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對受理的船舶融租案件高度重視,嚴把審判關,試圖為今后的相似案件樹立標桿效應。在天津既有經驗之上,筆者對現有案例予以梳理與分析,歸納出船舶融租案件存在的典型特點與重要問題,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簡稱《合同法》)等法律及相關理論,對這些問題給予解答,同時對《融租解釋草案》相關條文予以評析,以期實現理論研究來源于實踐、服務于實踐的目標。
一、對現有案件的梳理
在全國范圍內,已經公布的船舶融租案件較少①根據筆者在“中國審判法律應用支持系統”中“中國法院裁判文書庫”與“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庫”搜索全文“融資租賃+船舶”得出的案例不過24篇,除去13件其他案例及1件生產設備融資租賃合同案件后,船舶融租合同案件僅有10件,雖然該數據庫顯然不能囊括中國法院的全部案例,但現階段中國法院受理的船舶融租案件數量較少,也可見一斑。,天津方面也不例外。2010年以來天津海事法院受理的船舶融租案件不過4件。天津高院2010年以來受理的船舶融租案件只有2件②此外,2004年尚有1件為解決與其他法院生效文書沖突問題而對天津海事法院一起調解書提審的案件。但該案案由雖名為船舶融租實為借貸。。不過,現有案件仍然可反映迄今為止中國船舶融租案件存在的特點。
(一)標的價值較高,履約期一般不長
船舶融租案件的標的物為船舶,價值往往高達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在履約期方面,雖然船舶壽命一般超過10年,最長甚至能達30年以上③參見《關于老齡船舶檢驗的暫行規定》。,但考察范圍案件顯示,船舶融租合同的履約期一般均在5年以內,大大低于船舶預期壽命④考察范圍案件中僅有一起案件租期8年,超過5年,即(2000)廣海法事字第28號案件。。
(二)融資租賃模式與期滿后船舶歸屬約定多樣化
傳統上將融資租賃合同劃分為四大模式:直接租賃、轉租賃、回租和杠桿租賃。[4]考察范圍案件包括直接租賃與回租,此外,還包括以下兩種模式:一是承租人先行向造船廠訂購船舶并支付首期款項,之后出租人通過向造船廠支付剩余款項取得涉案船舶所有權的方式加入,與承租人簽訂融資租賃合同,承租人已支付的購船款項視為首期租金;二是出租人在與承租人履行融資租賃合同期間,將合同權益全部轉讓給第二出租人,再由第二出租人與原承租人訂立新的船舶融租合同。以上兩類模式,均可視為直接租賃的變種。就期滿后船舶所有權的歸屬而言,考察范圍案件主要包括船舶自動歸屬承租人型、承租人以象征性價格(如1元)取得船舶型、承租人以實質性價格(如船舶預期殘值)取得船舶型、續租等四類情形。
(三)涉及多方主體
雖然理論上船舶融租主體僅有出租人、承租人、供貨人(包括出賣人或船舶建造人)三方,但考察范圍中有的案件還涉及租金義務擔保人(保證人或抵押人)、受讓承租人擅自處分船舶的人及承租人無權處分船舶后就船舶獲得抵押權的人等主體。
(四)訴訟主體與訴訟事由的固定化
考察范圍案件中,原告均為出租人,被告為承租人(及其擔保人)⑤在出租人因承租人無權處分船舶而提起的權屬確認訴訟中,被告還可能包括船舶受讓人,設定抵押的人則一般作為第三人參加權屬確認訴訟。,訴訟一般因拖欠租金引起,因供貨人、出租人原因產生糾紛的案件無一起⑥早年王巖坡先生與吳德橋法官的研究均發現了這一點,證明長年以來訴至法院的融資租賃案件在此方面并無太大改變。。[5-6]此外,考察發現,出租人一般不會解除合同行使取回權⑦例外案件:如(2011)津海法商初字第523號案件、(2012)滬海法商初字第163號案件。。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筆者認為是融資租賃合同性質決定的⑧出租人一般只關心投入的資金是否能如期還本付息,對船舶既無興趣,也無運營能力,更無專業水平,且船舶通常由承租人指定購買/建造,特征化明顯,即使出租人收回船舶,也很難轉賣或找到其他經營人續租。譬如,根據起草《合同法》時多數融資租賃公司的反映,取回設備對租賃公司壓力很大,設備管理費無力支付,而船舶的管理成本、規費等相較一般機器設備而言更是巨大,租賃公司無力承擔。。[7]隨著目前船價低位運行,這一趨勢顯然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五)存在以融資租賃為名的借款案件
在有的案件中,當事人簽訂形式上的融資租賃合同,但在其后因不具備資質等多種原因未履行該合同,而由“出租人”直接向“承租人”發放款項,再由承租人自行購買船舶,所有權亦登記在承租人名下。這類案件被法院認定為借款。
(六)涉案合同條款存在特殊約定
考察發現,涉案船舶融租合同存在與《合同法》不太一致的約定,這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根本違約認定上,某些案件中合同設定了“陳述與保證”條款,出租人就采取一切必要的內部措施簽署、履行合同等事項予以陳述、保證,承租人就進行投資、籌資和資產處置應當提前通知出租人等事項進行陳述、保證。但出租人不因違反陳述與保證承擔責任,而一旦承租人做出的任何陳述、保證不真實、不全面,即構成根本違約,承擔嚴重法律后果;有的案件中合同約定,如承租人未支付任何一期應付租金,且承租人收到出租人就未付租金發出書面通知5日內仍未支付,則視為根本違約。
第二,在違約責任設計上,某些案件中合同約定,如果承租人違約,出租人有權解除合同并收回船舶,同時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遲延違約金以及其他款項和費用。與《合同法》第248條相比,這一約定明確了兩種救濟渠道可一并行使,無疑帶有懲罰性質。
(七)與船舶登記制度存在銜接問題
一方面,融租船舶多以光船租賃登記形式取得一定的“公示”效力,這與目前開始興起的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融資租賃登記功能上發生重合;另一方面,就船舶所有權登記,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登記條例》(簡稱《船舶登記條例》)第2條有關中方投資人出資額不得低于50%的規定①《船舶登記條例》第2條規定:“下列船舶應當依照本條例規定進行登記:……(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設立的主要營業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法人的船舶。但是,在該法人的注冊資本中有外商出資的,中方投資人的出資額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2013年,在報送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創新試點方案時,天津市東疆保稅港區曾嘗試將中方出資最低額限制降至25%,但交通運輸部交函海(2013)161號復函明確表示該最低額仍應不變。,相當部分外資出租人無法就融租船舶在中國獲得所有權登記。為此,有的當事人在履行中將船舶完全登記在承租人名下,以規避《船舶登記條例》。
二、現有案件反映出的法律適用問題
(一)登記是船舶融租的一大風險
1.所有權登記風險
物權變動須以一定公示方法表現于外,始能發生一定法律效果。[8]46但是,在融資租賃法律關系中,出租人與承租人成立直接占有—間接占有關系,[9]承租人直接占有租賃物,倘出租人對租賃物擁有的所有權未進行有效公示,將產生承租人擁有所有權的“假象”,不可避免地造成風險。
當然,由于船舶屬于特殊動產,存在所有權專門登記機構,與機器設備等動產的融資租賃尚有一定區別。不過,考察顯示,船舶公示仍是船舶融租的一大風險。這是因為,如前所述,出于種種原因,船舶所有權可能登記在承租人名下,使得名義物權與實際物權發生分離②又稱為法律物權與事實物權,前者指權利正確性通過法定公示方式予以推定的物權,后者指不存在交易第三人情況下能夠對抗法律物權的物權。除登記的外資出資限制規定可能導致名義物權與實際物權分離外,出租人為逃避其他責任,也有可能對此進行特別約定。譬如,根據海商法的體系,在發生油污損害時,依照《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及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船舶所有人(而非光船承租人)必須承擔賠償責任。,[10]加深承租人即所有權人的外觀表征,為其轉賣船舶提供便利。
如上章所述,名義物權與實際物權發生分離,一個主要原因在于《船舶登記條例》第2條的出資額強制規定,這種法律風險相當嚴重。出租人在此無疑陷入兩難境地。而若這類糾紛訴至法院,審判上也面臨兩難境地,一方面,如證據清楚事實充分,法院將判決出租人享有所有權,另一方面,該判決確認的所有權卻無法在中國獲得登記,這將嚴重影響判決的嚴肅性。
2.光船租賃登記風險
實踐中,根據相關部門通知③《交通運輸部辦公廳關于規范國內船舶融資租賃管理的通知》(廳水字[2008]1號)及行業實踐,船舶融租承租人多以光船租賃形式獲得經營權登記。但光船租賃與船舶融租性質差異明顯:光船租賃只有兩方主體,而船舶融租則存在供貨人(回租模式除外);光船租賃期滿后船舶所有權不會歸屬于承租人所有(附租購條款除外④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簡稱《海商法》)第154條。),船舶融租一般則賦予承租人期滿留購選擇權;光船租賃出租人負有交付時船舶適航責任⑤參見《海商法》第146條。,船舶融租出租人則不負包括此種責任在內的一切瑕疵擔保責任。此外,光船租賃履行期間,出租人欲對船舶進行抵押,需經承租人事先書面同意①參見《海商法》第151條。。而依據《融租解釋草案》第12條,船舶融租出租人欲轉讓、抵押船舶無需承租人同意,只對未及時通知承租人造成的損失負責②該條規定:“出租人轉讓、抵押租賃物或者轉讓其在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的部分或者全部權利,受讓方、抵押權人以此為由請求解除或變更融資租賃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租人存在前款行為而未及時通知承租人造成承租人損失,承租人請求出租人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由上可見,在融資租賃登記為光船租賃的情況下,存在一定風險,首先,出租人可能因船舶不適航承擔賠償責任與解約風險;其次,杠桿融資租賃中,出租人自有出資所占船舶價值一般較少,其他出資來源于銀行等處,需要以船舶抵押,而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局《關于融資租賃船舶登記有關事項的通知》將光船租賃登記的形式等同于實質法律關系,強調船舶融租出租人在船舶設置抵押權應事先取得承租人書面同意,換言之,如出租人抵押未獲得承租人事先書面同意,則無法以船舶抵押并獲登記,這事實上混淆了船舶融租與光船租賃的性質,也不利于杠桿融資租賃的開展。
(二)承租人擅自處分船舶時善意取得認定有一定難度
善意取得是民法上為維護交易秩序,保護第三人的信賴利益而創設的制度,根據該制度,即便處分人是無權處分,但只要符合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第三人就可以取得標的物物權。船舶屬于特殊動產,其物權變動采取登記對抗主義。一旦實際所有人未進行所有權登記,將為承租人處分船舶提供便利之門,也將導致第三人可能善意取得船舶。不過,在審判中,判定善意取得存在一定的難度。問題主要集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簡稱《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合理對價”是否應實際支付?現代船舶交易經常突破買賣這一經典形式,采取增資擴股、再融資等手段,此時應如何判定善意取得?
(三)對承租人根本違約的判定標準值得探討
所謂的根本違約,指“違約如此地重大和重要,以至于受害當事人有理由認為整個交易已經落空”或“一方的違約致使另一方定約目的不能實現”。[11]如當事人構成根本違約,則對方有權要求解除合同。考察范圍內的案件均為承租人違約,其責任基礎是《合同法》第248條“承租人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不支付租金”,但這里的租金是否有期次與數量的要求?法律未做明確規定,實踐中不好操作。自然,當事人也可自行約定“根本違約”情形。合同的這類約定多種多樣:有的約定承租人連續兩期或累計三期未按本合同約定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視為承租人根本違約,也有的約定只要一期不履行即構成根本違約。此外,如第二章所述,有合同將違反“陳述與保證”條款也視為根本違約處理。這種處理與海上保險合同中的“保證”條款有類似之處。但眾所周知,海上保險合同的保證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立法者為防止風險陡然增加而保險人卻一無所知或者是難以舉證等情形而特別設立的一種制度,[12]而就船舶融租合同而言,雙方權利義務、履行先后順序等因素與海上保險合同均迥然不同。是否可以建構船舶融租的“保證”制度,進而認定違反該條款構成根本違約,有待研究。
(四)出租人行使救濟渠道的方式需敦清
在融資租賃關系中,出租人享有的僅為名義所有權,占有、使用、收益權能均從本權中分離移轉給承租人,加之出租人在專業技術上天然不具優勢,故法律為保護出租人,設置了一系列救濟途徑,其中尤以《合同法》第248條最為重要。該條第二句規定,承租人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賃物。就“也可以”一詞,實踐存在爭議,即:兩種救濟途徑是否可同時適用,還是只能選擇其一?考察范圍案件中,有的案件③參見(2011)津海法商初字第523號案件。在合同中明確表示,如承租人違約,出租人有權解除合同并收回船舶,同時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遲延違約金以及其他款項和費用。如果當事人同時起訴要求支付全部租金及船舶取回權,是否應基于合同條款對其訴請予以支持?
(五)涉案合同性質判定標準需進一步厘清
考察范圍內,往往發生對涉案合同性質判定的問題,尤其是如何區分船舶融租合同與借款合同。現有案件判斷標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類:一是款項發放對象標準,如“出租人”直接向“承租人”發放款項,認定其為借貸的可能性便大一些;二是船舶購買及登記情況標準,如“承租人”自行購船,并將所有權登記在自己名下,認定其為借貸的可能性便大一些;三是履約行為標準,“出租人”與“承租人”的履約行為是否可表明合同性質——譬如,在一起案件中①參見(2004)桂民四終字第17號案件。,“出租人”出具催收逾期貸款通知書,標明發放款項是貸款,“承租人”亦無異議,說明雙方均認可合同的貸款性質。
但是,也有的案件②參見(2003)廣海法初字第287號案件。,出租人直接向承租人支付款項,承租人在收到這筆投資款后,自行與供貨人簽訂購銷合同,并將其登記在自己名下。法院卻確認該案件為船舶融租而非借款,僅因出租人無經營資質,方認定合同無效。因此,實踐中對合同性質的判斷標準仍需進一步厘清。
三、船舶融租糾紛法律適用問題解決對策
(一)審判基本準則
船舶融租法律關系中,出租人通過提供融資獲得利息收益,承租人通過接受融物獲得使用收益;為了擔保債權實現,出租人享有船舶名義所有權,為了確保船舶發揮效用,承租人享有不受干擾的船舶使用權;作為邏輯結果,出租人不因承租期間船舶對他人造成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害承擔責任,承租人應對承租期間船舶產生的供油費用等債務負清償責任;就租金給付而言,承租人交納的租金相當于或大體相當于船舶價值,故一旦租約到期,承租人擁有留購選擇權,這一選擇權屬約定形成權,出租人負容忍義務。[13]可見,雙方的關系實為動態的利益平衡關系,無論是承租人將船舶私自處分,還是出租人取得超過租金的高額利益,都將導致平衡關系的破壞。《合同法》第249條的規定正反映了這點③該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租賃期間屆滿租賃物歸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已經支付了大部分租金,但無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賃物的,收回的租賃物的價值超過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費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還。”。因此,維持當事人利益平衡應是審判船舶融租案件的基本準則。
(二)有關融資租賃登記問題
登記問題涉及到交易安全與秩序,關乎船舶融租業的發展,應該予以高度重視。在目前情況下,從司法角度而言,筆者認為應做到如下幾點。
1.應在個案裁判中注意區別法律物權與事實物權,在有優勢證據支持情況下尊重事實物權
出于意思自治考慮,當事人間可對所有權歸屬與登記進行約定,且船舶物權登記并非最終物權歸屬依據,不具設權作用,而僅具證權作用,[14]不應貿然將當事人的事實物權約定認定為無效。即使當事人間對所有權的約定系出于對《船舶登記條例》第2條外資出資額強制規定的擔憂,也不能一概認定其屬于惡意規避法律。
2.尊重新興的融資租賃登記系統
2009年7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簡稱征信中心)開始上線運行融資租賃登記系統,并發布《融資租賃登記規則》(簡稱《登記規則》),實踐中,無論是金融租賃公司還是內資租賃公司、外資租賃公司,均可在該系統上進行登記。租賃物范圍包括機器設備等非消耗性動產,也包括船舶在內。據了解,登記系統中現已存在一批船舶登記信息。登記內容依據《登記規則》第12條來看,并非所有權登記,而是包括承租人、出租人信息、租賃物描述、登記期限等在內的債權登記。
融資租賃登記系統的興起為船舶融租交易安全提供有力保證,根據登記規則,任何機構、個人在注冊為登記系統的用戶后,均可查詢融資租賃登記信息。因此,如若船舶進行相應登記,即使承租人以登記所有人的身份轉賣船舶,與之進行交易的相對人也可查到船舶融租登記,從而降低交易風險,同時保護了所有人與第三人利益。但遺憾的是,征信中心登記效力尚未得到法律的正式認可。這方面率先取得突破的是天津地區,2011年11月2日,天津市金融辦、人行分行、商務委、銀監局發布通知(簡稱《四部門通知》),要求各融資租賃公司在天津辦理融資租賃業務時,應在征信中心辦理融資租賃權屬狀況登記。通知同時規定,銀行、各融資租賃公司等十二種機構辦理資產抵押、質押、受讓等業務時,必須登陸公示系統查詢權屬狀況。據了解,雖然該通知只有倡導性作用,但仍大大減少了融資租賃潛在風險。而《天津指導意見》則賦予征信中心登記對抗第三人的效力④該指導意見規定,從事融資租賃交易的出租人,應依照《四部門通知》的規定,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融資租賃登記公示系統”將融資租賃合同中載明的融資租賃物權屬狀況,予以登記公示。未經公示,不得對抗《四部門通知》中所列機構范圍內的善意第三人。。因此,征信中心登記在天津司法審判中已獲得認可。今后,應借融租解釋制定的契機,正式確認征信中心登記的效力。筆者注意到《融租解釋草案》第13條第2項已對此做出規定,該規定順應實踐,應在正式條文中予以維持。并期待今后《融資租賃法》能采納這一司法經驗。
3.在尊重現登記制度基礎上,建議海事部門加強登記監管,并適時建議相關部門對其進行必要的修改
審判工作應遵照與尊重《船舶登記條例》現有規定,但為防范交易風險減少糾紛,針對當事人將船舶所有權登記在承租人名下的情形,可以采取與海事部門溝通、進行司法建議等方式,建議海事部門加強相關登記監管、提示出租人分離名義物權與法律物權可能的風險。
另一方面,從應然角度而言,現有登記制度有修改的必要:第一,《船舶登記條例》第2條有關外資出資額的強制規定已滯后于時代發展。不當限制國外金融資本進入船舶融租領域,不利于中國航運企業獲得資本,最終將不利于中國航運事業的發展。同時,也將為惡意承租人擅自處分船舶提供可乘之機。根據《中國入世議定書》附件九,至2005年3月中國融資租賃市場基本對外開放,現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逾12年,船舶登記仍對外資比例做如此高的要求,不符合世貿全面開放的精神。僵化的規定與現實的沖突迫切需要解決。今后,應在繼續尊重《船舶登記條例》基礎上,適時提出建議,敦促國務院對該條例進行修改,降低或取消外資出資比例要求。第二,光船租賃與船舶融租有本質不同,在將來融資租賃登記正式被司法解釋予以確認后,應建議廢止船舶融租以光船租賃形式登記的做法。并應建議有關部門在實踐中探索征信中心與海事局登記系統的統合銜接,避免登記與查詢的不必要繁瑣。
(三)有關善意取得問題
1.有關對價是否應實際予以支付
筆者傾向于肯定。理由在于: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一書認為,受讓人在取得財產時,必須以相應的財產或金錢支付給出讓人。[15]故而是否支付對價,是判斷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必要條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最高審判機構的觀點。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支付合理價款,將導致很多實質上無償、形式上有償的轉讓為法律所保護,有違善意取得制度宗旨。[16]
2.增資擴股與一船二融情形下的善意取得認定
筆者認為,善意取得的規則是共通規則,應統一按《物權法》第106條予以判定,不存在特殊善意取得。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7條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編著的評注書來看,[17]公司因出資而善意取得財產所有權,必須符合下列要件:公司受讓財產時為善意;出資財產轉讓價格合理;出資的財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至公司名下,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公司。如果公司主張依據增資擴股取得船舶所有權,但其注冊資本長期未發生變動,且亦無證據證實轉讓方與受讓方就船舶存有其他經濟補償,則不應視為受讓方支付了合理對價。
就一船二融而言,雖然與一物二賣在名稱上相似,但由于船舶所有權歸屬第一出租人所有,一船二融實際仍是無權處分與善意取得問題。此時,若第一出租人對船舶已進行所有權登記或融資租賃登記,則第二出租人不能取得船舶所有權。若第一出租人既未登記其所有權,也未登記融資租賃信息,則應分情況討論:首先,如第二次融資租賃亦未登記,由于船舶占有未發生移轉,僅產生占有改定,根據通說,占有改定不發生善意取得①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征求意見稿)》第21條第一種意見。。[8]91,[18]其次,如第二次融資租賃進行了登記,由于船舶所有權與融資租賃登記均采登記對抗主義,故只要不存在惡意串通,第一出租人不能對抗第二出租人。
(四)有關根本違約的認定
筆者認為,就根本違約而言,不能完全依賴于融資租賃合同的相關約定。而應根據合同的目的,結合違反義務的性質分別予以判定.
第一,就拖欠租金到達何種程度構成根本違約,如有約定應予以尊重。即使當事人負有六十期租金給付義務,僅有一期未予支付亦同。這是因為,租金支付構成融資租賃的主給付義務,延期支付經催告不履行構成對合同根本目的的違背;融資租賃合同是商事合同,參與者均為商人,應具有較高的風險意識,法律不予以特殊保護②與之相比照的是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為了保護消費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38條第2款規定:“合同法有關買受人未支付價款達到全部價款五分之一時出賣人有權解除合同的規定是下限型規定,如出賣人約定解除條件低于全部價款五分之一,損害買受人利益的,買受人有權主張該約定無效。”。
在不存在約定的情形下,審判需要固化標準,參與過《合同法》立法的同志認為,承租人連續兩次在租賃期間未支付租金的,出租人才有權請求支付全部租金。[19]這一標準值得肯定,但應再考慮拖欠租金的數額標準,盡快以司法解釋方式予以確定。《融租解釋草案》第16條對《合同法》第248條予以明確,從商事法的角度而言,具有重大意義。
第二,就“陳述與保證”條款而言,不能采取海上保險合同“保證”條款相似的解決方法。因為船舶融租合同與海上保險合同存在明顯不同,而且海上保險合同規定保證條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風險遠遠大于船舶融租合同。因此,法院應本著《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則,視程度而定,對船舶融租合同中的“陳述與保證”條款予以必要調整。如該條款對承租人約束太過,達到明顯破壞雙方利益平衡的程度,則應依照《合同法》第40條格式合同加重對方責任的規定,排除相應約定,但這不意味著違反該類條款無需承擔任何法律后果,而應視該條款保障的義務類別確定違約責任。譬如,違反“船舶經營區域”陳述是對從給付義務的違反,可以責令糾正并課以損害賠償。而違反“承租人進行投資應予通知”保證的,是對附隨義務的違反,通說認為不得單獨提出履行請求,只能請求損害賠償。[20]
(五)《合同法》第248條兩種救濟途徑的行使方法
筆者認為,《合同法》第248條規定的兩種救濟途徑只能擇一行使,理由如下。
第一,1988年《國際融資租賃公約》所確立的法律原則和規則已得到廣泛認可,實際上已成為國際上有關融資租賃交易的普遍性實踐。[21]77該公約第13條明確規定,支付全部租金與解除合同取回租賃物只能選擇其一行使。中國雖不是該公約成員國,在解釋上可參考其規定。
第二,從出租人與承租人利益平衡而言,若準許出租人同時行使解除合同取回租賃物與支付全部租金兩種救濟渠道,將導致出租人獲得遠高于合同正常履行情況下所獲利益。尤其應注意,船舶融租期限一般遠低于船舶預期壽命,且合同中存在一些對承租人不公平的條款,例如某些“陳述與保證”條款,出租人完全可能受利益驅動,在承租人輕微違約情形下,依約認定其構成根本違約而同時請求兩種救濟途徑。
第三,有人提出,《合同法》第248條并非強制性規范,如果合同有約定,允許出租人同時行使兩種救濟途徑,實質相當于出租人以支付全部租金形式主張懲罰性違約金,對此應基于意思自治原則許可。實踐也存在一些支持出租人按約同時行使兩種救濟途徑的案例①如(2005)佛中法民四初字第126號、(2005)盧民二(商)初字第717號,但這些案件為一般融資租賃案件。。但筆者認為,基于合同正義的要求,不能放任當事人以意思自治為由約定遠超過損害的違約責任,且中國采取的是損害填補原則,根據《合同法》規定,對過分高于損害的違約金,人民法院可應當事人要求適當減少。實踐中,解除合同計算出租人損害賠償的公式一般為:正常履行出租人可獲得的全部權益(即全部租金+手續費)減去已經收取的租金及違約金減去提前收回船舶的期限利益②參照(2011)津海法商初字第523號案件的計算方法。。超出這一范圍的賠償請求權,除出租人成功證明還存在其他“可預期”損失外,筆者認為一般不應予以支持。
《融租解釋草案》第26條亦明確了兩種救濟途徑不能同時行使,但令人費解的是,該《融租解釋草案》第27條規定如果支付租金請求勝訴后,承租人不履行,出租人有權另行起訴請求解除合同收回租賃物,該規定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浪費司法資源,有待商榷。
(六)應以當事人可查明的意思為基準,依照各種因素判斷當事人間是否構成融資租賃關系
上述實踐三個標準中,第一,即使出租人直接將款項支付給承租人,也可以理解為回租的一個環節,只不過該筆款項具備預付購船性質③當然,回租也可作為掩蓋貸款實質的形式。。[21]135不過,只要承租人與出租人之后約定船舶歸出租人所有,應肯定回租成立。第二,即使自行購船并將所有權登記在自己名下,但如上文所述,登記所有權不一定等同于實際所有權,且實踐中亦存在此類型船舶融租。因此,判斷標準中,“直接支付”與“登記歸屬”都不是決定性的。關鍵標準應是透過履約行為可查知的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即第三標準)。但該標準非常概括,仍有必要依賴融資租賃的本質,就當事人履行合同的各個環節予以判斷。筆者在此提出幾個判斷標準供參考:一是是否存在單獨的購買/建造合同;二是是否購入并使用融租合同約定的船舶;三是是否對出租人享有船舶所有權存在約定。該約定不一定以登記方式體現,也可以私下協議;四是當事人約定的租金總額是否相當于或大體相當于船舶價值,如當事人收受款項后購買與約定船舶價值完全不相當的船舶,則不符合該標準,或者雖然當事人購買的船舶賬面價值大體等同于租金總額,但查知船舶明顯高估的,也不符合上述標準。當然,這里必須要補充的是,即使認定該法律關系不構成融資租賃關系,從保護商事交易的角度著眼,也不宜輕易將其認定為無效,除非其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規定。
四、結語
船舶融租方興未艾,對航運業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因登記制度的徹底完善尚需一段時間,今后法院還將面臨擅自處分融資船舶出現的糾紛;因融資租賃業的急速擴張,新類型的融資糾紛如杠桿型融資租賃糾紛、轉租型融資租賃糾紛、出賣人—承租人糾紛也可能出現。
在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完備的情況下,應進一步總結實踐中的審判經驗,基于承租人與出租人利益平衡的原則,在個案中注意區分事實物權與法律物權,對征信中心登記系統予以尊重,同時,在尊重現有登記制度前提下,適時建議修改之;依據《物權法》等相關規定判定融資租賃案件中的善意取得;不完全依賴于融資租賃合同約定判定根本違約,而應根據合同的目的,結合違反義務的性質分別予以判定,明確《合同法》第248條規定的救濟途徑只能擇一行使,且一旦選定不能變更,最后,就融資租賃的認定,應以當事人可查明的意思為基準,依照各種因素判斷當事人間是否構成融資租賃關系。
[1]SCHROTH P W.Financial leasing of equipment in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10(58):325.
[2]UNIDROIT.Report on the contract of leasing(Study LIX-Doc.1)[EB/OL].[2012-03-30].http://www.unidroit.org/english/studies/study59/main.htm.
[3]中國租賃藍皮書編輯部.中國租賃藍皮書——2012年中國融資租賃業發展報告[EB/OL].(2013-03-29)[2013-04-17].http://www.flleasing.com/onews.asp?id=6130.The Editorial Office of China Lease Blue Paper.China lease blue paper[EB/OL].(2013-03-29)[2013-04-17].http://www.flleasing.com/onews.asp?id=6130.(in Chinese)
[4]鄭雷.船舶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8.ZHENG Lei.Study on the legal issues of ship finance lease[M].Beijing:Law Press,2012:38.(in Chinese)
[5]王巖坡.融資租賃合同案件的審理[J].法學,1991(7):13.WANG Yan-po.The trial of the finance lease contract cases[J].Law Science,1991(7):13.(in Chinese)
[6]吳德橋.融資租賃案件的特點及審理[J].人民司法,1995(3):25.WU De-qiao.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ial of the finance lease cases[J].The People’s Jucicature,1995(3):25.(in Chinese)
[7]孫禮海,賈東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立法資料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37.SUN Li-hai,JIA Dong-ming.Selected legislative materials of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Beijing:Law Press,1999:237.(in Chinese)
[8]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M].5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XIE Zai-quan.On the real rights of civil law(Vol.I)[M].5th ed.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11.(in Chinese)
[9]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M].5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1152-1154.XIE Zai-quan.On the real rights of civil law(Vol.III)[M].5th ed.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11:1152-1154.(in Chinese)
[10]孫憲忠,常鵬翱.論法律物權與事實物權的區分[J].法學研究,2001(5):84-85.SUN Xian-zhong,CHANG Peng-ao.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al rights in jure and the real rights de facto[J].Beijing:Chinese Journal of Law,2001(5):84-85.(in Chinese)
[11]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490.WANG Li-ming.The study of contract law(Vol.II)[M].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3:490.(in Chinese)
[12]司玉琢,李志文.中國海商法基本理論專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692.SI Yu-zhuo,LI Zhi-wen.Study on the theories of China maritime law[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692.(in Chinese)
[13]王澤鑒.民法總則[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97.WANG Ze-jian.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civil law[M].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1:97.(in Chinese)
[14]奚曉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183.XI Xiao-ming.Commentari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the Trial of Cases of Disputes over Sales Contracts[M].Beijing:People’s Court Press,2012:183.(in Chinese)
[15]最高人民法院物權法研究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328.The Study Group of Real Rights Law of Supreme People’s Court.Commentaries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al 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Beijing:People’s Court Press,2007:328.(in Chinese)
[16]王利明,尹飛,程嘯.中國物權法教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148.WANG Li-ming,YIN Fei,CHENG Xiao.A course of China real rights law[M].Beijing:People’s Court Press,2007:148.(in Chinese)
[17]奚曉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司法解釋(三)清算紀要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111.XI Xiao-ming.Commentaries on the 3r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rpor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uidelines of liquidation of Supreme People’s Court[M].Beijing:People’s Court Press,2011:111.(in Chinese)
[18]崔健遠.物權:規范與學說[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234.CUI Jian-yuan.The norms and theories of real rights[M].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11:234.(in Chinese)
[19]李國光.中國合同法條文釋解[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405.LI Guo-guang.Commentaries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hina Contract Law[M].Beijing:Xinhua Press,1999:405.(in Chinese)
[20]韓世遠.合同法總論[M].2 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15.HAN Shi-yuan.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contract law[M].2nd ed.Beijing:Law Press,2008:215.(in Chinese)
[21]劉敬東.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1.LIU Jing-dong.Study on the leg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lease[D].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01.(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