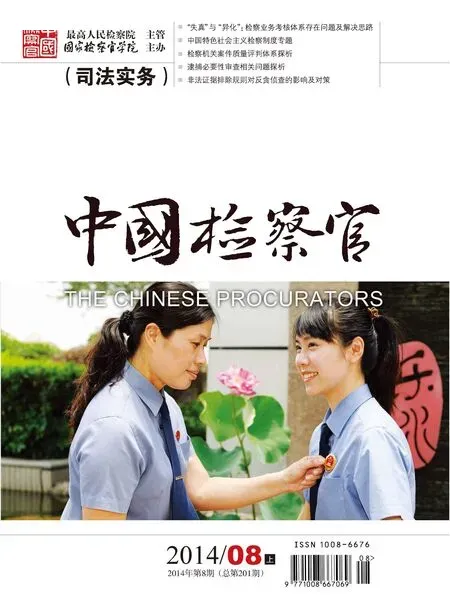司法改革視閾下證明力規則問題研究
文◎郗琳王瑀
司法改革視閾下證明力規則問題研究
文◎郗琳*王瑀*
我國司法改革,自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以來,至今已有16年。期間,社會各界廣泛參與,或立制決策,或身體力行,或獻策獻計,改革雖是一路坎坷,卻也績效顯著。2008年4月26日-27日,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行的“依法治國與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理論研討會上,“大多數與會學者認為,10年司法體制改革無論在觀念更新、制度變革方面都有明顯推進:司法職權配置更為合理,司法制度更為完善,司法效率進一步提高,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司法保障機制進一步完善,司法行為不斷規范,司法人員素質獲得普遍提高,司法在維護公平正義的基礎上更為尊重和保障人權。”[1]過去幾年,諸如2010年趙作海案等系列冤假錯案,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廣泛熱議,以此為契機,我國司法改革進一步深化,其中首推證據制度建設。在2010年“兩高三部”聯合頒布《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和《排除非法證據規定》后,中國政法大學組織了一次研討會,學者高度評價了“兩個證據規定”:“改革完善刑事證據制度的重大成就”[2]、“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3]、“我們國家刑事司法改革的階段性重大成果”[4],等等。甚至有學者認為,“證據制度建設是司法改革首要任務”。[5]
我國司法改革既已成效顯著,實務界和學術界當皆大歡喜。然而,改革亦有飽受爭議之處,在證據立法中,應當首推證明力規則:當下,[6]一方面“司法實踐呼喚、創造、實踐證明力規則”,另一方面,“司法實務界建構證明力規則的主張遭到了學術界的強烈批判”。[7]愈是飽受爭議,愈是見仁見智,真理愈是越辯越明。因此,筆者試以證明力規則為視角,對我國司法改革提出粗淺建議,望盡綿薄之力。
一、中國證明力規則的“冰火兩重天”
如上所述,證明力規則在實務界和學術界遭受著“冰火兩重天”的待遇。在實務方面,“當下中國的司法實踐渴求證明力規則、實踐證明力規則進而創造證明力規則。”[8]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一線法官渴求證明力規則,并實踐證明力規則。有學者進行了實證調研:“當我們深入司法實踐進行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時,我們發現當下的司法實踐是如此重視證明力問題,幾乎所有的一線法官都主張在證據立法中對證明力問題加以規定,甚至希望通過一種事無巨細的方式規定各種證據的證明力,即構建完備的證明力規則。”[9]同時,“疑罪從輕”、“孤證不能定案”等司法實踐傳統,是法官實踐證明力減等規則、補強證據規則和“證據相互印證”等證據規則的現實景象。
第二,在最高人民法院獨自或參與頒布的證據規定中,證明力規則占據很大比例,足見其創設證明力規則意向之明顯、態度之堅定。以筆者對2010年《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的實證分析為例,該規定共有證據規則40條,其中證明力規則相關條款有32條,其比例達80%。[10]有學者對此總結道:“無論是在對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證據的審查過程中,還是在對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鑒定意見、勘驗檢查筆錄、辨認筆錄的評判過程中,兩個證據規定都對法官提出了審查證據證明力的具體要求和方法。而對于證人證言出現自相矛盾、被告人供述出現翻供的情況,證據規定也確立了具體的采信標準。與此同時,對于原始證據與傳來證據、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證明力問題,兩個證據規定也建立了一般性的采信規則。……不僅如此,對于何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對于只有間接證據的案件如何認定被告人達到有罪的標準,以及對于被告人有罪供述的補強等問題,兩個證據規定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我們據此可以斷定,兩個證據規定對證據的證明力所作的法律限制,延續了中國證據立法的傳統。而這種以限制證據的證明力為核心的理念,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影響著中國的證據立法,并逐漸成為支撐中國證據立法的指導性原則。”[11]
第三,地方性證據規定中,證明力規則也占據很大比例。[12]這是一線法官渴求證明力規則,加之上行下效的必然結果。
與實務方面截然相反,當下中國主流證據法學研究者重視證據能力規則研究,對證明力規則的立法規制,持輕視、回避甚至排斥、否定的態度。這種趨勢的形成,與近年來英、美等國證據法的體系、理念及其實踐在我國的傳播,有著很大的關系。[13]近代以來,證據法主流主張,依自由心證對證據證明力進行評判。自由心證制度是“法律對證據的證明力預先不作規定,允許法官在審理案件中自由加以判斷的證據制度”;[14]“其核心內容是對于各種證據的真偽、證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實如何認定,法律并不作具體規定,完全聽憑法官根據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地判斷”。[15]從訴訟證明制度發展歷程來看,自由心證是對法定證據制度的否定之否定,“被認為是西方法制度近代化的標志之一”。[16]據此,中國主流證據法學者主張,“從偏重證明力的證據觀轉向重視可采性的證據觀”,[17]“從對證明力的關注轉向對證據能力的關注”,[18]“在法定證明程序(舉證、質證和認證程序)和可采性規則方面加以規范,對證明力則應當主要以自由證明來確定,少用強制性規范”。[19]
可以想象,當面對立法者創設證明力規則的堅定態度時,部分學者的凝重深思之狀。有人稱“帶有強烈的法定證據制度的色彩”,[20]亦有人稱“是落后的法定證據制度在中國的復興”。[21]不久前,有學者對此總結為:“中國證據立法遵循了一種以限制證據的證明力為核心的基本理念”,并將這一立法理念和趨勢稱為“新法定證據主義”,認為必須“創造條件消除那些促成這一證據理念產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環境”。[22]至此,實務創設證明力規則的堅定態度和如火如荼的干勁兒,與學術界的嘆息、呼喊和斥責,合奏出我國證明力規則的“冰火兩重天”。
二、合理創設證明力規則的理性應然
筆者倡導“接地氣”的改革理念。所謂制度,沒有絕對的最好,只有某一社會發展階段下的最合適。今天,世人審視西歐中世紀的法定證據制度是何等荒謬,然而,在“證人證言是最常用、最重要的證據形式”[23]的時期,它是否是平衡司法公正與效率后的最合適制度呢?上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時期警示我們,任何一種超越社會現實的主義,哪怕是“最優的”,也是不切實際的。
退一步講,假如中國現行司法實踐是一段“扭曲”的過渡形態,無需對其進行策論,而應放眼未來,進行宏觀規劃式的精論。那么,合理創設證明力規則是否有其理性應然呢?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這不僅僅是因為自由心證賦予法官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存在較大隱患,需要予以規制,更因為自由心證的過程是可認知的,對此中外學者均有論述。“自由心證并非一種內在的價值,之所以禁止法律對證據評價活動作出預先規定,其認識論方面的理由僅僅在于,對于這一領域還沒有能力設計出更好的規則”。[24]自由心證的蓋然性不等同于不可知論,“不是所謂的‘主觀唯心主義’,反而恰恰是地地道道的辯證唯物主義”。[25]既然可以認知,而且在法官自由心證的過程中必然存在著事實認定的共性及其相對合理路徑,[26]那么就可以對其加以描述,研究和改進。不可否認,評判證據的證明力,的確因案不同、因人而異,那只能說明證據立法不可對證明力進行機械性量化或限制,比如,“口供是一個完整的證據”,但對諸如此類證明力規則的否定,并不代表要否定所有證明力規則。哪怕沒有絕對的真理,但人類依然在不遺余力地探索那些“相對的”真理,也可以提出“真理具有相對性”、“解放思想”的論斷,一如立法可以規定:“據以定案的間接證據已經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一言以蔽之,在司法改革中,有必要且應該認真對待證明力規則,并予以立法規制,而不是將其省心地拋給那種所謂的建基于“模糊邏輯”的自由心證。
回顧中國證據法學發展史,曾有個別學者認為,相比陪審團審判,中國訴訟模式下法官裁判權并未被實質性分割,不存在制定證據規則的內在要求;同時,法官裁判的獨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杜絕外界干擾,故不存在制定證據規則的外在要求。然而今天,已經找不到任何一個持有類似觀點的專家或學者了。不僅如此,證據規則的發展,已出現從審判向偵查擴張的端倪。[27]
如果再退一步講,假如中國證據立法出現了向落后法定證據制度復歸的趨勢,也不能因為證明力規則的不當,去否定合理創設證明力規則的理性應然,即不能因噎廢食,更不能動輒扯起“自由心證”的大旗,發動一場場對中國證據立法的“狂轟濫炸”。此時,司法改革參與者應該集中精力思考以下問題:創設證明力規則的正當性在哪里?當下中國是否需要證明力規則,需要哪些,又要多少?如何創設證明力規則會更利于當下中國的司法實踐?等等。
三、結語
在當下中國司法改革風雨交加之時,部分改革參與者應嘗試改變一貫的訓誡、斥責態度,不妨先冷靜觀察,再超然思考,厘清改革背后的現實必然和理性應然。對于現實必然,應多加考究和分析,少用極端分析、多用邊際分析;對于理性應然,應多做歷史性研究和試驗。惟有如此,即便改革所使用的“答案”有誤,也不至于在泛意識形態化的批判中找不到問題之所在,喪失掉探究改革合理進路的機會。因此,筆者認為:但凡改革,需接地氣,實事求是,力求實效。
注釋:
[1]《依法治國與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理論研討會綜述》,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4期。
[2]陳光中:《改革完善刑事證據制度的重大成就》,載《檢察日報》2010年6月1日。
[3]樊崇義:《證據兩規定是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載《檢察日報》2010年6月2日;亦見于卞建林:《鑄證據基石,促司法公正》,載《證據科學》2010年第5期。
[4]熊秋紅:《刑事證據制度發展中的階段性進步——刑事證據兩個規定評析》,載《證據科學》2010年第5期;亦見于陳衛東:《兩個證據規定的進步與不足》,載《證據科學》2010年第5期。
[5]張保生:《證據制度建設是司法改革首要任務》,載《中國改革》2011年9月。
[6]中國證據法學學術研究也曾有一段重視證據證明力、輕視甚至否定證據可采性的歷史。
[7]李訓虎:《證明力規則檢討》,載《法學研究》2010年第2期。
[8]同[7]。
[9]同[7]。
[10]2010年《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共有41條,其中證據規定有40條。
[11]陳瑞華:《以限制證據證明力為核心的新法定證據主義》,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6期。
[12]參見房保國:《現實已經發生——論我國地方性刑事證據規則》,載《政法論壇》2007年第3期。
[13]已翻譯成中文的英美等國證據法學者的論文和著作尚且不計,在證據法典譯著方面,有美國《證據法:文本、問題和案例(第三版)》,張保生等譯,《英國證據法實務指南(第四版)》,王進喜譯,《澳大利亞聯邦證據法》,王進喜譯,《英國成文證據法》,熊志海編譯,等等。
[14]卞建林主編:《證據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頁。
[15]易延友:《對自由心證哲學基礎的再思考》,《比較法研究》1998年第2期。
[16]王亞新:《刑事訴訟中發現案件真相與抑制主觀隨意性的問題——一一關于自由心證原則歷史和現狀的比較法研究》,《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17]何家弘:《從應然到實然——證據法學探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頁。
[18]汪建成、孫遠:《刑事證據立法方向的轉變》,《法學研究》2003年第5期。
[19]張保生等編著:《證據法學》,中國政法大學2013年,第36頁。
[20]肖建華主編:《民事證據法理念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該書第18章“證據證明力規則的運用與問題”對民事訴訟中的證明力規則進行了系統的解說分析。
[21]吳丹紅:《證據法學的啟蒙》,《證據科學》2008年第1期,第2期。
[22]同[11]。
[23]參見何家弘:《短缺證據與模糊事實》,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66頁以下,關于“法定證據制度的評析”。
[24]達瑪斯卡:《比較法視野中的證據制度》,吳宏耀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頁。
[25]易延友:《對自由心證哲學基礎的再思考》,《比較法研究》1998年第2期。
[26]“自由心證原則下有罪認定的標準是存在客觀基礎的。這就是在按照法定的程序而進行證據的提出、展示以及圍繞證據的辯論、對質等一系列當事者間的攻擊防御中逐漸形成的要證事實的清晰性、明白性狀態。只有在這種客觀的狀態在解明度與證明度兩個指標上都達到極高的程度時,法官才能作出有罪的認定。”參見王亞新:《刑事訴訟中發現案件真相與抑制主觀隨意性的問題——一一關于自由心證原則歷史和現狀的比較法研究》,《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27]馮俊偉:《刑事證據規則的兩種方式——兼評我國刑事證據立法》,《第四屆證據理論與科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50-57頁。第四屆證據理論與科學國際研討會于2013年7月20至21日在北京召開。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