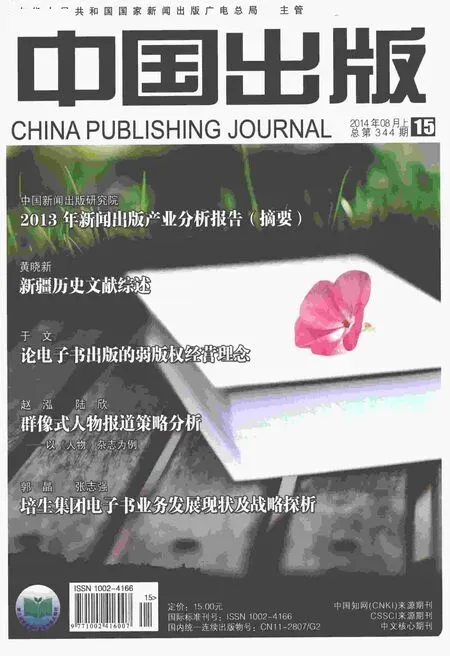從《元畫全集》的編輯談古代繪畫整理出版的探索與實踐
文/王 晴 李介一
中國古代繪畫從產生之日起,即非單純意義的圖形寫貌。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畫。”[1]
誠如斯言,繪畫除了藝術鑒賞性外,它與“六籍”一樣,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是全人類寶貴的物質與精神財富。并且與文字史料相比,繪畫更加直觀、形象和準確。“左圖右史”,圖史互證、互補,古已有之。20世紀70年代,西方史學界發生了新的變化,其中著名的新文化史專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提出了圖像史料一說,他的專著《圖像證史》主要內容就是“關于如何將圖像(images)當作歷史證據來使用”。[2]隨著時代的進步,古代繪畫的史料價值越來越被世人重視。
但古代書畫留存不易,宋周密《齊東野語·書籍之厄》云:“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3]法書名畫亦然。明董其昌《古董十三說》云:“至書與畫,尤當貴重。書以傳意,畫以傳形,用莫大焉,知之者甚稀。自魏晉以上無征焉,以其所藉惟紙與絹也。紙壽千年,絹五百年,極其珍藏防護,數盡自毀;摹勒上石,拓久終壞。”[4]古畫的載體特質與自身的不可復制性,使其保存堪憂,即使“珍藏防護”,最后還是難免“數盡自毀”。在古代,最好辦法就是臨摹,所謂“下真跡一等”。科技發達的今天,全面搜集整理、高質量仿真出版是讓古畫留存后世的最佳方式之一。
基于搶救性保護珍貴的中國古代繪畫遺產、普及性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浙江大學依托在國內外學術交流及藝術史研究學科的優勢,與浙江省文物局合作,啟動了《中國歷代繪畫大系》項目,系統、全面地開展對中國古代繪畫的搜集、整理、研究與編纂出版工作。
這項浩大的國家級文化工程,自啟動以來得到了海內外各收藏機構的傾力配合。2008年12月,《宋畫全集》出版,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全面、最權威的宋代繪畫總匯。2013年12月,《元畫全集》12冊順利出版,《光明日報》《浙江日報》等均作了專版報道,且在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評選中,獲圖書提名獎。
本文以《元畫全集》的編纂出版為例,從入編圖目的調查整理、資源收集、原作拍攝、圖文編輯、印制裝幀等方面,談談對中國古代繪畫整理出版的探索與實踐。
一、普查資料編制圖目,奠定前期良好基礎
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5]入編作品目錄的編制是一項不容忽視的首要工作。
《元畫全集》以前人整理的畫目工具書,如《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國繪畫全集》《中國繪畫總合圖錄》《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續編》《日本所在中國繪畫目錄》《海外所在中國繪畫目錄》《歷代流傳書畫作品編年表》《中國古代畫家和畫目索引》《中國歷代畫目大典》等為基礎,結合國內外近30多年來各文博機構展覽圖錄,以及考古發掘等最近學術研究成果,編制出了海內外博物館藏品目錄的初編。然后聯絡各博物館,實地考察元畫藏品,通過與博物館研究人員討論分析,并征求相關專家意見,最后調整確定入編圖目。特別是在與博物館洽談中,又發現了不少因各種原因從未對外公布過的作品,比如美國弗瑞爾美術館所藏程棨的《摹樓鑄耕織圖》、上海博物館所藏《青影紅心圖》等,這些作品都是館藏后的首次公開出版,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與學術意義。
通過全面調查,精心選擇,合理編排,規范整理,入編《元畫全集》的圖目基本達到準確、全面、詳盡,從而為下一步圖像資源的收集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千方百計廣泛搜集,匯聚最全面圖像資源
眾所周知,元畫存世少,且散佚在世界各地,又由于年代久遠,材質朽損,并涉及文物保護等諸多限制,搜集整理十分不易。
這次《元畫全集》通過多方渠道,共入編元代絹本(含綾本)、紙本繪畫599件,涉及全球104家收藏機構,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弗瑞爾美術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等著名的中國古代繪畫收藏機構。[6]
《元畫全集》項目組不僅輾轉全國各省市縣,還遠赴美國、英國、日本各地洽談聯絡圖像資源授權事宜,僅日本就往返7次之多,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7]《元畫全集》收錄的每一幅圖像,均獲得了相關機構的直接授權使用。特別是已出版的《元畫全集》第四卷第一、二冊,第五卷第一、二冊,收錄日本各公私機構及弗瑞爾美術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所藏元代繪畫作品合計187件。這些海外藏品的出版意義重大,為系統、全面、深入地研究元代繪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真正實現了讓中華優秀文化遺產為天下學子所用。
三、高精品質原作拍攝,呈現最真實的古畫原貌
目前市場上出版的高級美術畫冊一般采用120反轉片或高清數碼片拍攝,近年來,反轉片漸為數碼片取代。而《元畫全集》的原作拍攝,絕大部分采用了8×10英寸大型技術座機拍攝。
兩者相較,高清數碼片的優點在于:操作快捷方便,資金投入少,像數量發展迅速,色彩管理便利。但數碼片有嚴重的先天不足。目前數碼主流采用的兩種成像方式CCD(電荷耦合原件圖像傳感器)成像與CMOS(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圖像傳感器)成像,像數點固定,顏色的位深依靠軟件計算,在表現物體的質感上遠遠趕不上已經發展了100多年的膠片技術。特別是對于中國古代書畫的拍攝成像,它的缺陷比較明顯。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繪畫含有大量的中性灰色,這是中國畫的重要特點,在專業人員眼里,這種水墨畫的灰色有無限的級數,而在數碼成像的片子中,次黑場至灰色部分的色彩層次表現能力遠遠不如8×10英寸反轉片。
8×10英寸膠片拍攝也有其缺點:如器材設備攜帶不便,光源要求高,對攝影師技術要求苛刻,拍攝成本昂貴,沖片還存在一定損壞率,等等。但膠片最大的優勢是它比數碼成像色彩還原準確,對墨色的表現層次豐富,顆粒細膩,能夠更加忠實地再現原作精神。
權衡利弊,最后《元畫全集》的原作拍攝絕大部分采用了8×10英寸膠片拍攝。并且,收錄其中的90%以上的作品,是專門應《元畫全集》的質量要求,由專業攝影師現場拍攝原作而成,從而使得被歲月不斷侵蝕破壞的傳世元畫能以最為真實的面貌得到永久保存。
四、圖文編輯注重品質,構筑學術研究平臺
所謂“宋人丘壑,元人筆墨”,與宋畫尚理相比,元畫更為注重筆墨意趣。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真跡原貌,為從事中國畫創作、藝術研究的畫家、學者提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元畫全集》在圖像與文字編輯上注重提升學術品質,在體例上著重展示原作的完整性,突出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第一,《元畫全集》在編輯上將作品引首、隔水、本幅、題跋、本款、收藏印等都一一呈現,讀者從中可以得到一個整體的、直觀的印象。其中,立軸、冊頁形式的作品,出于多方面的考慮,題簽、天頭、地腳、隔水、裱邊等部分的信息在彩色圖版中并沒有體現,但在黑白版的作品說明中,有整體的配圖展示。這些部分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對進一步理解作品、驗證收藏流傳情況、考訂真偽等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二,每幅作品基本上都以高精度的整體信息圖、原大圖、局部放大圖的形式全面展現。一般來說,手卷整體圖縮小印刷,內容包括引首、隔水、本幅、題跋、本款、收藏印等所有信息,分段圖原則上原大印刷;立軸整體圖縮小印刷,原大圖、局部放大圖選擇體現畫面主體的某些局部,出血印刷;冊頁一般原大印刷,個別精彩作品選擇局部放大印刷。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局部的選取立足于對中國古代繪畫風格的整體把握、深刻理解中國畫筆墨意蘊的基礎上,以求精微準確地還原不同作者獨特的間架結構和筆墨精神,為繪畫藝術創作與研究者提供了在不能接觸原作的情況下,全面、深入、清晰地了解作品的最好條件。
第三,整理出版《元畫全集》不僅在資源的收集上全面地將元代繪畫集中在一起,還依托浙江大學古代書畫研究中心、浙江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等科研機構,組織聘請了海內外藝術史專家學者數十人對收錄的每件元畫作品進行鑒別與說明撰稿。在編輯體例上,除彩色圖版和作品說明外,還有原大印章釋讀、注釋、參考文獻與索引,資料系統詳備,考證嚴謹規范。可以說,《元畫全集》不僅是一部高級藝術畫冊,而且具有一定學術含量與文獻價值,集觀賞性、史料性、學術性為一體。
五、強化高標準印制裝幀,完美再現原作氣息
從資源采集、電子分色、直接制版、高仿真印刷與裝幀等各個環節,《元畫全集》均采用世界頂級技術,并相應制定了國內首個針對高端藝術出版流程的質量技術控制與管理標準。
在掃描過程,使用具有硬件USM(銳化工具)功能的德國海德堡S3900電分機,工作模式采用LAB(全色域空間)掃描圖像信息,以確保寬闊的色域與豐富的色彩。
在校色過程,絕大部分圖片都要經過數百乃至數千步驟的修正調整,達到當今最高級校色軟件的極限。作品的清晰度、色彩,水墨的干、濕、濃、淡層次變化,以及作品氣息的還原度等均以接近原作精神為第一目標。
在制版印刷過程,《元畫全集》采用了日本網屏 公 司(screen)platerite CTP(Computer to Plate直接制版)直接出版技術,超高精度(280Lpi掛網,4000dpi分辨率)仿真印刷技術。特別是以GCR(Gray Component Replacement,灰分替代)分色曲線來精確處理黑版階調,通過不同階調黑版表現墨韻的焦、濃、重、淡、清各層次。同時減少墨色中的三原色成分,使用15%、20%、25%、30%不同黑版起點的GCR曲線來處理不同類型的作品,以達到“墨不礙色,色不礙墨”的藝術效果。
在裝幀設計上,出版社特地從德國訂購具有卓越色彩還原能力和獨特手感的高質量紙張——優麗特質花紋紙(Scheufelen),以達到理想的色彩表現。《元畫全集》裝幀方式為方背精裝配函套。封面裝幀材料選用AAA級真絲面料,聘請廠家根據我們設計的紋樣專門織造。在配頁、上膠、書殼包面、堵頭布等裝幀工序采用了手工制作,工藝復雜。整套畫冊裝幀精美,用材考究,既保留了中國傳統畫冊裝幀的鮮明特色,又展現了現代印制工藝的最高水平。
六、結語
在海內外學術界越來越重視對中國古代繪畫做集成式整理研究的今天,《元畫全集》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收藏界與藝術創作、研究界針對中國古代繪畫資源的“藏用”兩難問題,緩解了文物資源保護與利用之間的矛盾,為后人學習、借鑒與研究元代繪畫提供了詳盡的、可靠的基礎文獻。希望通過《元畫全集》的出版探索,能使更多深藏禁宮、罕見人間的國寶級中國古代繪畫,利用高科技手段,化身千萬,重新展現在全世界人們面前。
注釋:
[1](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M]//唐五代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7:139—140
[2]彼得·伯克.圖像證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
[3]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二《書籍之厄》[M]//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3:216
[4](明)董其昌.《古董十三說》之十二說[M]//古董秘鑒:古玩藝術鑒賞經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26
[5](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1
[6]此項數據包括即將出版的《元畫全集》第三卷第二、三冊,第五卷第三、四冊。
[7]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M]//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