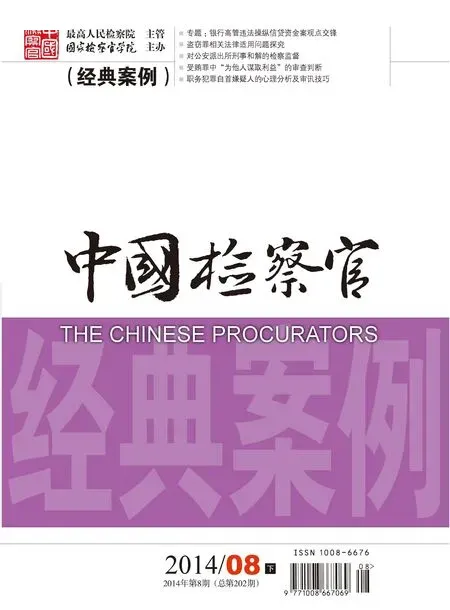主題:對原告未請求的費用法院能否主動納入審理范圍
文◎秦志松趙銳
主題:對原告未請求的費用法院能否主動納入審理范圍
文◎秦志松*趙銳**
案名:李某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申訴案
[基本案情]
2008年3月7日,C市F區中心醫院(以下簡稱中心醫院)對患有心臟病的李某實施了射頻消融手術,術后李某病情未明顯好轉。同年4月2日,中心醫院將李某送到新橋醫院繼續住院治療7天,花費4505.5元。后李某又返回中心醫院繼續治療,至出院時李某還有33087.64元醫療費尚未結清。同年4月22日,中心醫院與李某達成協議:中心醫院補助李某人民幣20000元,并支付李某第二次鑒定費用10000元,在今后衛生主管部門調解或法院裁決后再結算。2008年8月12日,李某以自己遭受人身損害為由將中心醫院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中心醫院賠償其殘疾賠償金等損失共計547357.12元。在李某的訴訟請求中,并沒有涉及醫療費用的部分。審理過程中,經司法鑒定:中心醫院在李某的整個醫療處置過程中有過錯,其過錯與李某的損害后果存在次要因果關系。
[判決結果]
法院于2008年11月18日作出一審民事判決:中心醫院賠償李某人身損害賠償損失116863.6元,其余損失175294.4元由李某自己承擔。中心醫院不服一審判決,向C市第三中級法院提起上訴。C市第三中級法院經審理,于2009年2月9日作出終審民事判決,該判決認為:中心醫院為李某墊付的兩筆醫療費用,確系李某本次治療行為中發生的,故不管李某請求與否,本案均應將此款納入李某損失總金額中一并進行計算。遂判決:(一)撤銷C市F區法院一審民事判決;(二)李某的物質損害賠償金296664.5元,由中心醫院賠償給李某118665.8元(已付57594.14,實際還應支付61071.66元),其余177998.7元由李某自己承擔;(三)駁回李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李某不服二審判決,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2011年5月13日,C市檢察院就該案向C市高級法院提出抗訴。主要理由是:二審法院將中心醫院為李某墊付的醫療費用作為已付款在其應承擔的賠償金額中予以扣除,屬于適用法律錯誤。C市第三中級法院經再審認為:原二審判決將中心醫院在本案訴訟之前為李某墊付的醫療費用納入了本案的審理范圍,客觀上造成了原二審判決審查的費用超出了李某在原一審中起訴中心醫院賠償的范圍,違反了民事訴訟的處分原則,屬于適用錯誤。遂判決:一、撤銷原一、二審判決;二、李某人身損害賠償金共計人民幣291659元,由中心醫院賠償李某116663.6元(已付30000元,實際還應支付86663.6元),其余174995.4元由李某自行承擔。
[爭議焦點]
本案主要的爭議焦點在于,中心醫院為李某墊付的其在新橋醫院住院期間產生的醫療費4505.5元,以及李某在中心醫院住院期間欠付的醫療費33087.64元,在本案中是否應該納入審理和損失計算范圍?
[裁判理由之法理評析]
筆者同意C市第三中級法院的再審判決。理由是:原二審判決的主要錯誤之處,在于違反了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由于原審原告李某并沒有將中心醫院為李某墊付的其在新橋醫院住院期間產生的醫療費4505.5元,以及李某在中心醫院住院期間欠付的醫療費33087.64元的兩筆醫療費用作為自己的損失計算并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同時中心醫院也沒有提起要求李某支付醫療費的反訴,故法院不能對該兩筆費用進行審理和判決。
處分原則是指民事訴訟中,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當事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支配和決定其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處分原則作為當今民事訴訟制度中一項重要而基本的原則,充分體現了民事權利是一種私權的本質特征。因此,不管是奉行當事人主義模式的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奉行職權主義模式的大陸法系國家,都將當事人處分權確立為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原則。
(一)民事訴訟中遵循處分原則的理論依據
處分原則符合民事訴訟中司法權的消極性和終局性特征。根據處分原則,在民事訴訟中,必須由原告提起訴訟請求,法院才可以受理;在審理過程中,法官須受原告提出的訴訟請求范圍約束,不得審理訴訟請求范圍之外的事項。因此,處分原則充分體現了司法權啟動方面的被動性或應答性特征,而且這也是司法活動區別于行政活動和立法活動的一項根本性標志。處分原則有兩個基本的含義:一是沒有當事人發起的“告”,就沒有之后法院的“理”。對此,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9條規定了當事人提起訴訟應當符合的四個基本條件,同時《民事訴訟法》第123條又規定了人民法院應當保障當事人依照法律規定享有的起訴權利,對符合本法第119條的起訴,必須受理。因此,當事人提起訴訟,是民事審判活動得以進行的先決條件。二是“理”的范圍應當嚴格限制在“告”的范圍之內,即審理的對象不能超出“告訴”的范圍,否則同樣就會違背處分原則。
(二)民事訴訟中遵循處分原則的實踐意義
新中國從建立民事訴訟制度,到逐步與世界相接軌,只用了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從照搬蘇聯的民事法律制度到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事法律體系。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我國對“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指導原則過于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一些法官忽略了對民事訴訟中程序公正的價值追求,對當事人處分原則的重視程度還不是很高。在一些審判活動中具體表現為:法院代行了本應由當事人主張和享有的訴訟權利,無視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僅在收案環節有案由上的劃分意義,進入審判環節后,被一些法官加以任意改變和解釋,這些均是沒有充分意識到處分原則重要性的具體表現。通過審視和分析上述案,我們不難發現“重實體、輕程序”的觀點至今還在不知不覺地影響著我們許多法官、檢察官的辦案思路和司法行為。不少法官和檢察官在一個獨立的民事訴訟過程中,總是試圖盡量解決案件中相關的全部紛爭,以達到案結事了的最佳效果。這一出發點固然是好的,但是這些沒有將“審”合理限制在“告”的范圍的行為,有時難免會違反程序公正,侵犯到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因此,在處理民事案件的司法行為中,我們首先應當秉持程序公正的理念,充分尊重和依法保障當事人自主行使處分權,因為只有首先做到了程序公正,才是向司法公正跨出了具有實質意義的第一步。
(三)處分原則在本案中的適用分析
對于處分原則,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3條明確規定為:“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其中,民事權利是指實體性權利,比如當事人可以提起或放棄訴訟請求。訴訟權利是當事人參加民事訴訟的程序性權利,比如當事人在一審判決后可以自行決定上訴或放棄上訴等情形。結合本案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在本案中原告李某沒有提出要求中心醫院支付醫療費的主張,這應當視為李某就自己已發生的醫療費方面的損害賠償請求在本次訴訟中進行了放棄,該放棄行為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且未損害第三人的利益,因而是一種有效的民事權利處分行為。其次,二審法院對原告李某已經放棄的、沒有起訴的醫療費部分損失主動進行審理并予以計算抵扣,這無疑是使得該起案件的“理”超出了“告”的范圍,明顯違背了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最后,中心醫院因醫療過錯給李某造成損害屬于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的范疇,而李某欠付中心醫院的醫療費則屬于醫療服務合同糾紛的范疇。對李某欠付和被墊付的醫療費部分,中心醫院可以通過反訴或是另行起訴的形式要求李某予以承擔,這才是其合法有效的救濟渠道。
綜上,原審法院超越原告李某的訴訟請求范圍,對其未主張的醫療費用徑行審理和判決,違反了民事訴訟法關于處分原則的規定。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408000]
**重慶市涪陵區人民檢察院[40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