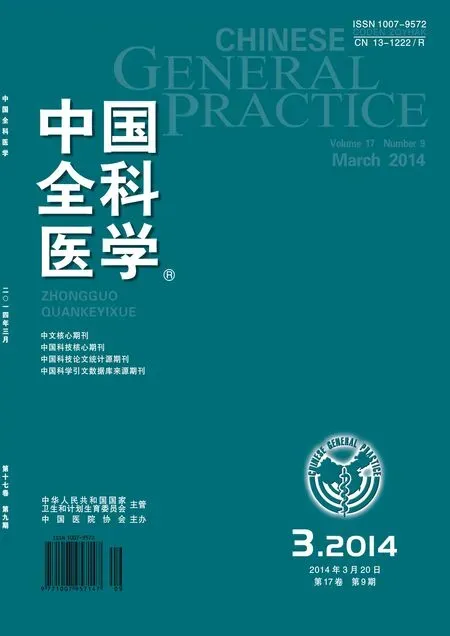分泌性中耳炎患兒手術治療前后炎性細胞因子的變化及其臨床意義
馬翔宇
分泌性中耳炎(SOM)好發于兒童,可致聽力損失,影響語言和學習,從而影響患兒的生活質量[1]。SOM的病因及發病機制非常復雜,近年來雖有大量研究,但仍不能對其充分了解,目前普遍認為SOM的發病機制并非是一種因素作用,而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近年來隨著免疫學技術和理論的發展,關于炎性細胞因子在SOM發生、發展中的作用及意義越來越受到關注[2]。本研究采用ELISA法檢測SOM患兒實施鼓膜切開置管術前后中耳積液和血漿中炎性細胞因子的變化,以探討炎性細胞因子在SOM發病和轉歸中的作用及臨床指導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入選標準 (1)3歲以上患兒,有聽力下降或反復間斷性耳痛或耳閉塞感病史;(2)耳鏡檢查鼓膜內陷或向外隆凸,部分患兒透過鼓膜可見液平面或氣泡;(3)純音聽力測試或聽性腦干反應有不同程度聽力下降;(4)聲導抗圖檢查為“B”型或“C”型,鐙骨肌反射未引出;(5)經正規藥物治療3個月以上病情無明顯改善。
1.2 一般資料 選取我科2009—2011年收治的57例(93耳)SOM患兒(SOM組),均行鼓膜切開置管術治療,且符合上述病例納入標準。其中男35例(55耳),女22例(38耳),男女之比為1.6∶1;年齡為3~12歲,平均6歲8個月;病程為3 d~2年。57例患兒均以家長發現其對聲音反應遲鈍,反復間斷性耳痛或耳鳴及耳閉塞感為主訴來就診,伴或不伴睡眠打鼾癥狀。另選取我院2010—2011年員工的健康子女10例(對照組),其中男6例,女4例,男女之比為1.5∶1;年齡為3~14歲,平均5歲2個月;均無中耳炎病史及其他相關疾病。兩組兒童的性別構成及年齡間有均衡性。
1.3 方法
1.3.1 治療方法 57例(93耳)SOM患兒均在全麻下經手術顯微鏡觀察,于鼓膜前下象限放射狀或弧形切開鼓膜,切口約2 mm,自切口抽吸中耳分泌物,切口止血后置入T形鼓膜通氣管。置管保留時間為3個月~1年。合并有慢性扁桃體炎和/或腺樣體肥大者,同時行扁桃體摘除和/或腺樣體切除術,術后短期應用抗生素和黏液促排劑治療。為避免激素對細胞因子的干擾,本組SOM患兒均未采用激素治療。
1.3.2 中耳積液和血漿樣本的采集及炎性細胞因子的檢測 中耳積液樣本的采集:在嚴格無菌下操作,經鼓膜穿刺抽出積液,密封,標記,存放于-80 ℃冰箱凍存待測。
血漿樣本的采集:分別在術前和術后第5天常規采血,取抗凝靜脈血3 ml,離心分離血細胞,吸取上層血漿,密封,標記,存放于-80 ℃冰箱凍存待測。
炎性細胞因子水平測定: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2(IL-2)、白介素6(IL-6)、白介素10(IL-10)的測定均采用南京凱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ELISA試劑盒,按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標準操作。以NJ-2100型酶標儀(美國InterMed公司),在450 nm條件下檢測各炎性細胞因子的吸光度值。以試劑盒所提供的各炎性細胞因子標準品繪制標準曲線,以各檢測樣本的酶標儀吸光度值讀數與標準曲線擬合獲得對應濃度,再乘以相應的稀釋倍數獲得實際炎性細胞因子水平。當測得的炎性細胞因子水平大于最低標準水平時定為陽性:TNF-α>0.037 5 μg/L,IL-2>0.062 5 μg/L,IL-6>0.062 5 μg/L,IL-10>0.037 5 μg/L。計算平均水平時包括低于最低標準水平的數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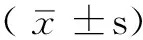
2 結果
2.1 治療前SOM患兒中耳積液炎性細胞因子陽性率 57例(93耳)患兒中,有51例(84耳)成功采集到中耳積液,另外6例(9耳)采集中耳積液失敗。對采集到的84份中耳積液進行炎性細胞因子水平檢測,發現治療前SOM患兒中耳積液中TNF-α、IL-2、IL-6和IL-10的陽性率分別為84.5%(71/84)、78.6%(66/84)、86.9%(73/84)和82.1%(69/84)。
2.2 治療前SOM患兒中耳積液炎性細胞因子與病程的相關性分析 將患兒的病程與其中耳積液中TNF-α、IL-2、IL-6、IL-10的水平做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病程與TNF-α、IL-10水平呈正相關(r=0.387,P<0.05;r=0.484,P<0.01),與IL-2、IL-6水平呈負相關(r=-0.476,P<0.05;r=-0.366,P<0.05)。
以病程14 d為界限,將患兒分為病程≤14 d組(27例)和病程>14 d組(30例)。病程≤14 d的患兒中耳積液中TNF-α、IL-2、IL-6、IL-10水平與病程>14 d的患兒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 治療效果 51例(84耳)患兒治療后中耳積液消失,聽力恢復正常,耳悶脹感、耳鳴消失,聲導抗圖檢查為“A”型曲線,聲反射均可引出。
2例(4耳)患兒治療后中耳積液消失,聽力改善,耳痛、耳閉塞感癥狀減輕,聲導抗圖檢查為“A”型或“C”型曲線,聽力較術前明顯提高,但未達到正常水平。
4例(5耳)患兒術后發生感染,提前拔除鼓膜置管,給予抗生素和激素治療后控制,但聽力改善不明顯。其中2例患兒使用了激素治療,因此治療后未再采集血漿樣本進行測試。
2.4 SOM組與對照組炎性細胞因子水平比較 治療前,SOM組患兒中耳積液、血漿及對照組血漿TNF-α、IL-2、IL-6、IL-10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SOM組中耳積液上述炎性細胞因子水平與SOM組血漿、對照組血漿比較,SOM組血漿IL-2、IL-6水平與對照組血漿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治療后,SOM組患兒血漿TNF-α、IL-2、IL-6和IL-10水平分別為(0.12±0.07)、(0.18±0.17)、(0.20±0.12)、(0.15±0.11)μg/L,與本組治療前血漿樣本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值分別為4.84、7.70、9.55和3.44,P均<0.05)。

Table1 Comparison of cytokines levels in middle ear effusion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ourses of disease

病程(d)TNF-α耳數 水平 IL-2耳數 水平 IL-6耳數 水平 IL-10耳數 水平 ≤14291.19±0.44391.82±0.52312.11±0.68370.68±0.44>14371.98±0.54320.98±0.48421.32±0.59321.74±0.69t值6.32916.90275.26507.7122P值<0.05<0.05<0.05<0.05
注:由于患者個體差異和每個患耳中積液程度和采集量的不同,在實際檢測中,針對每只患耳積液樣本,并不是能夠檢測到所有4種炎性細胞因子的存在,故各炎性細胞因子檢測的耳數是不同的;TNF-α=腫瘤壞死因子α,IL=白介素

Table2 Comparison of cytokines levels in plasma and middle ear effusion between control group and SOM group before treatment

組別樣本數TNF-αIL-2IL-6IL-10對照組血漿100.13±0.09 0.21±0.11 0.13±0.04 0.08±0.08 SOM組血漿570.43±0.46 0.68±0.52△ 0.57±0.31△ 0.31±0.37 SOM組中耳積液*1.63±0.58△▲1.44±0.68△▲1.65±0.81△▲1.17±0.49△▲F值100.5835.5761.2775.34P值0.00000.00000.00000.0000
注:*治療前SOM組患兒中耳積液樣本數分別為:TNF-α 71耳,IL-2 66耳,IL-6 73耳,IL-10 69耳;與對照組血漿比較,△P<0.05;與SOM組血漿比較,▲P<0.05
3 討論
SOM是耳鼻咽喉科常見病,尤其以兒童發病率較高。兒童期腺樣體肥大是引起兒童SOM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腺樣體肥大長期壓迫或堵塞咽鼓管咽口導致中耳腔壓力不平衡和引流障礙,從而可導致中耳炎。另外,小兒咽鼓管長度較短,管腔相對較大,且與水平面角度較小,鼻咽部炎癥易經咽鼓管逆行感染中耳。除此之外,本病還與先天性異常、遺傳性異常、酶的異常、免疫缺陷、畸形、上呼吸道感染、呼吸道過敏、急性中耳炎病史等自身因素以及護理不當、家庭經濟狀況、季節、氣候等外界因素有關。
近年來隨著免疫學技術和理論的發展,關于免疫反應在SOM發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在免疫反應應答網絡中,炎性細胞因子對免疫的調節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環節。有研究表明,在SOM發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的炎性細胞因子發揮了各自不同的免疫調節作用。在SOM發病的早期,促炎細胞因子IL-2可上調發病部位及全身免疫系統的免疫應答,而抑炎細胞因子IL-10和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拮抗IL-2誘導的促炎癥作用,當這種網絡調節平衡被破壞,將使炎性反應進入慢性過程,進一步造成中耳局部的炎性損害。本組SOM患兒的中耳積液和血漿中均檢測到了不同表達水平的炎性細胞因子,說明SOM導致的炎性反應的發生不僅局限于炎癥產生部分,而且已經通過血液和淋巴等循環途徑擴展至全身免疫系統,誘發系統免疫反應。系統免疫反應的激活又可反饋增強局部免疫反應,這可能是SOM遷延不愈的原因之一。在經過鼓膜切開置管術和術后短期應用抗生素治療后,SOM患兒炎性反應消除,同時伴隨著中耳積液的消失。另外,本研究發現在SOM的不同病程中,中耳積液中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水平有所差異。在病程早期(病程≤14 d),IL-2和IL-6呈現高表達,而在病程后期(病程>14 d),TNF-α和IL-10則呈現高表達;且病程與中耳積液中TNF-α、IL-10水平呈正相關,與IL-2、IL-6水平呈負相關。
IL-2是最主要的炎性細胞因子,可誘發多種免疫細胞的激活。在病程早期,炎癥局部產生的高水平IL-2可誘導局部T淋巴細胞大量活化增殖,并刺激活化的T淋巴細胞分泌更多的促炎細胞因子,上調機體免疫反應,活化細胞因子免疫調節網絡,并誘導全身免疫反應。一般認為,IL-6主要與疾病的早期相關,抗原提呈細胞刺激相應的T細胞克隆可產生大量IL-6,并與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還有學者認為,高水平的IL-6可以抑制TNF-α的產生[3]。TNF-α是一種單核因子,主要由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產生,可通過提高中性粒細胞的吞噬能力,增加過氧化物陰離子產生,引起組織損傷。在病程早期,IL-6可對TNF-α的產生具有抑制作用,病程后期IL-6水平降低,伴隨著對TNF-α的抑制解除,TNF-α呈現高表達狀態。IL-10是典型的細胞因子合成抑制因子,有研究表明IL-10在中耳滲出液中的高表達易誘發慢性炎癥狀態,可能在調節中耳局部黏蛋白的分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本研究發現在病程后期SOM患兒中耳積液中IL-10水平較病程早期增高,可能是作為主要的抗炎性細胞因子參與局部免疫的負性調節。
本研究結果顯示,SOM患兒中耳積液中TNF-α、IL-2、IL-6、IL-10水平均高于SOM患兒及健康兒童血漿中水平;同時,SOM患兒血漿中IL-2、IL-6水平也高于健康兒童血漿中水平。治療后,隨著炎癥狀況的逐漸消失,SOM患兒血漿中各炎性細胞因子的水平明顯回落,顯著低于治療前SOM患兒血漿中的水平。
兒童SOM發病的多因素性決定了其治療應采取綜合治療的原則。2004年美國兒童學會、美國家庭醫師學會和美國耳鼻喉頭頸外科學會發表的“分泌性中耳炎的診斷和處理指南”[4]提出的治療推薦:嚴密觀察,臨床醫師應嚴密地觀察處理尚無危險的患兒,從分泌物的發生或診斷之日起,一直觀察3個月。藥物治療方面,抗組胺藥和減充血劑對SOM無效,不推薦使用;抗生素和皮質類固醇無長遠期效果,也不推薦使用。而對于病程較長,保守治療效果不理想,有過敏性體質,中耳滲出液較稠厚,鼓膜較厚,嚴重鼓膜內陷和粘連者,為避免發生粘連性中耳炎、鼓室硬化或膽固醇肉芽腫等嚴重并發癥,應不失時機地進行手術治療。SOM患兒自控能力差,絕大多數無法配合局麻下鼓膜穿刺術,因此鼓膜切開置管術是手術治療的首選方法,配合腺樣體切除術,療效顯著[5]。其主要治療作用為:引流鼓室內積液;平衡鼓室內壓力;防止鼓室粘連。鼓膜切開置管術的并發癥主要有提前脫管、術后感染、管腔堵塞、脫管后鼓膜穿孔不愈等。脫管的發生與鼓膜切口的大小、手術操作的熟練度以及置入的鼓膜通氣管的形狀有關。目前我科使用的程馮斜口鼓膜通氣管兩側均有防止脫管的邊緣突起,可有效預防脫管發生。其他手術并發癥均與感染有關。本組2例治療無效的患兒均是因為患兒術后不遵醫囑,擅自游泳引起術區感染,導致耳漏及脫管發生。因此,術后嚴格禁止術耳進水是防止繼發感染的關鍵。
綜上所述,在兒童SOM的發生、發展和預后過程中,炎性細胞因子可能起重要作用;炎性細胞因子可作為兒童SOM發病和治愈診斷的輔助指標;鼓膜切開置管術治療兒童慢性SOM的治愈率高,療效顯著,并發癥少,值得在臨床中推廣。
1 黃選兆,汪吉寶.實用耳鼻咽喉科[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837-846.
2 李潔,趙守琴.免疫調節相關性細胞因子在分泌性中耳炎中的作用[J].國際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雜志,2008,32(3):144-146.
3 林國武,黃維國,姜鴻彥,等.一氧化氮及兩種細胞因子在分泌性中耳炎中耳積液中的表達及意義[J].中華耳鼻咽喉科雜志,2000,35(1):23-25.
4 Neff MJ,AAP,AAFP,et al.AAP,AAFP,AAO-HNS release guideline on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otitis media with effusion[J].Am Fam Physician,2004,69(12):2929-2931.
5 李華斌,許萬云,邢光前,等.鼻內鏡下腺樣體切除術對兒童慢性鼻竇炎和分泌性中耳炎轉歸的影響[J].臨床耳鼻咽喉科雜志,2005,19(13):596-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