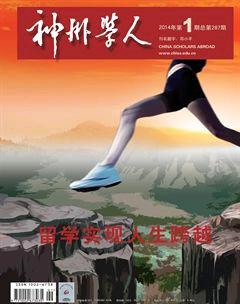我住在畢沙羅的畫里
李冉
世人都聽說過電影取景地,可19世紀印象派畫家畢沙羅駐英期間作品中的取景地,你知道都在哪里嗎?信不信由你,我不僅知道,甚至還幸運地“住在畢沙羅的畫里”呢!
卡米耶·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1830-1903)是一位頗有威望的法國印象派大師,不僅曾是莫奈的戰友,也是唯一一位參加了印象派8次展覽的畫家,可謂是印象派大家庭里最堅定的家長和印象派的“摩西”。他的平和、謙遜與熱情總是令人尊敬,更被高更和塞尚尊稱為他們的老師。
無論何時,畢沙羅始終堅持在畫布上發掘生活的風俗之美與自然之光。在他的作品里人們找不到對歷史宗教等題材的依賴,看到的都是戶外的街頭和鄉村、教堂與馬車。陽光下的自然感觀和色彩沖撞總是最先搶過觀眾的眼球,看似隨意的筆觸總能在精準描繪對象的同時俘虜觀眾的欽佩,使跳動的調皮光線被永久地記錄在畫布之上。
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畢沙羅曾被迫遷至英國倫敦,并受到英國風景畫家康斯太勃爾、透納作品的啟示,他的色彩變得更加歡快敞亮。而他在倫敦度過的近1年時間里所創作的多幅作品,也深受英國人的喜愛。
在倫敦國家畫廊里保存著據說是畢沙羅在英期間創作的最大幅的油畫作品《錫德納姆林蔭道》(The Avenue,Sydenham),因為它表現的是畫家眼中倫敦東南部錫德納姆地區早春時節的俏皮風景,特別受人喜愛。說實話,我在欣賞畫作時總是更關注畫家的技法和色彩,并沒有特別留意作品解說板上的內容。但去年這次卻很難得地一眼就盯上了解說中的“Sydenham”,當時真把我驚得虎軀一震。我那時正借住在老朋友羅杰家中,而羅杰家就坐落在Sydenham!畫面上的這條林蔭道就在他家街道附近!怎么這么巧啊?!
“你很喜歡這幅畫嗎?我也是。在畫里我們的倫敦看起來非常可愛,對嗎?”身邊的一位充滿笑意的金發管理員驕傲地問道。
“是的!非常喜歡!而且我剛剛發現,我目前正住在離畫中街道很近的地方!”我激動了!
“我的上帝!那可太棒了!”聽了我的話,這位女士的大藍眼睛像擦了上光油一樣锃亮起來,“多令人羨慕啊!而且我一定要告訴你,這個地區基本還保留著當年畫家作畫時的面貌,你會發現像這教堂一樣的許多地方現在都還在呢。”
這可真讓我的小心臟被連續電擊了好一陣:“太感謝了!我應該馬上去看看!”
在火速搭車沖回錫德納姆時我還很自豪地保持了理智,先在當地圖書館下車想查查資料。沒想到,我剛向管理員打聽了半句“請問有沒有關于畢沙羅……”(后面的“的書”兩個字根本就沒給機會而被活活憋回去了),本來盡顯深沉的卷發管理員突然像沖刺撞線一樣從轉椅上向我彈過來:“哦!您是說畢沙羅嗎?我們這里一直以他為驕傲!他曾在這里創作了不少本地可愛的風景作品!”這話真是撞在我心坎兒上了,于是趕緊說明來意,并請管理員做了簡介,借到了推薦書目(包括畫家自傳和畫冊)。末了,幾位管理員(在聊天過程中不知不覺又湊過來,至少4位管理員向我動情地做著描述)還好心地告訴我:“你會在左邊路口白底紅磚的房產公司外墻上看到由政府頒布的藍色圓形飾板,紀念這位藝術家曾在本區居住創作。”
經過多位熱情人士的指點,我終于呼哧帶喘地站在了畢沙羅當年作畫的地點——Lawrie Park Avenue。在這條離我暫住之地僅2分鐘車程的街道對面,Saint Bartholomew教堂還是像畫中一樣顯眼。雖然1830年修建的它如今比畫里的更滄桑,結構也有些小修繕,但力度依舊。街道兩旁的幾顆橡樹依然富有扭動的線條,只是比曾經更加強壯。柏油馬路取代了畫面里的磚土路面,還“長”出了兩排苗條路燈,但畫面中青翠的草坪如今依然喜人。曾經的紅磚老房旁邊如今更是蓋起了新鄰居。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畫中的馬車如今已經退休,接替它的則是一輛輛輕便可人的私家汽車,我還曾在這些私家車里看到了憨豆先生心愛的老款MINI車。
據說這里的景色令畢沙羅非常鐘情,還特意委托情婦在1897年故地重游以視安好。同時,在他寫給侄女的信中還提到過這幅作品:“這幅畫被畫廊保管得很好,而且得到了比我預想還要好的贊譽。它總讓我充滿激情,這種狀態是我一直在尋找著的。”
帶著同樣的激情,我急切地回到羅杰家與他分享下午的驚奇游記。
“羅杰你猜,我今天發現了一件什么不得了的事,那位很有名的畫家畢沙羅曾經畫過你家附近的景色呢!我剛剛從那條Lawrie Park Avenue回來。”
剛從花園修剪完薔薇枝回來的羅杰倒是不緊不慢地沖了一杯咖啡,從半月形眼鏡后面向我瞇著笑眼說:“哦,我很高興你發現了我們這里這個可愛的小‘秘密。也許你還會注意到,這位畫家還畫過另一張《錫德納姆山附近》的作品?說實話,我們現在待的這座房子,還很幸運地出現在這幅畫里了呢。”
“你是說畢沙羅曾畫過這座房子?!”
“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正住在畢沙羅先生的畫里。”
我真是要氣絕了啊!作為一個年輕藝術家,這種難得的事情簡直太刺激了!
這幅《錫德納姆山附近》被創作在一個17×21英尺(43.5×53.5cm)的標準10號油畫布上,如今幾經輾轉被保存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福特沃斯的金貝爾美術館(Kimbell Art Museum)南廳。
當這幅作品展現在眼前時,觀眾的眼球總是率先被前排的三棵橡樹吸引。這左兩棵右一棵的橡樹不僅創造了一種傳統的色彩濃重感,還加強了畫面的景深感。據說畢沙羅當年從畫家柯羅和其他幾位法國風景畫家的創作中學到了這樣的表現手法。這種設計使畫家得以對風景中的一些小因素進行深一步的強調。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畫面中的這三棵橡樹今天依然存在,盡管現在很難再從畢沙羅當年創作的角度看到它們,因為如今它們周圍蓋起了錫德納姆山火車站,并被無數的新生綠蔭包圍著。據說這三棵橡樹附近的地皮曾被人買下,中途無論蓋房還是拆遷,地皮主人始終堅持“一定要保住這三棵大橡樹”。如今這些橡樹依然挺拔在錫德納姆山車站入口外的停車場旁。這是我第一次去羅杰家拜訪時的約見地點,當時實在沒有想到這幾棵橡樹居然還有這樣一段佳話。
畫面中間的部分,有一串點綴在綠地邊緣的小房子很吸引人,這些或紅或白的小房子,包括它們的花園至今仍被保留著,盡管大多數都經過翻新整修。而我的朋友羅杰的房子,就位列其中。據羅杰說,當初他決定買下這幢房子時(那會兒他還是個年輕小伙兒),房主是一位耄耋老太太,而據說這位老太太又是早年從她父親手中繼承的這棟房子。所以如此向前推算,當畢沙羅揮筆作畫時,這座房子里當時應該正住著那位老太太和她的家人們。而在140多年之后,作為藝術家的我,也難得幸運地住進了這幢畫家筆下的房子里!
雖然現在羅杰的房屋從外部顏色上來看和油畫里的有些區別,特別是經過翻新和極少間斷的雨水的侵蝕,磚墻顏色不僅變深而且苔蘚茂盛,但從基本結構和位置來看,當年畫里的房屋幾乎面貌依舊。如今天冷時分,房子里的壁爐依然可以使用,從煙囪里冒出的暖煙和百十年前一模一樣。花園里的綠地一直青翠盎然,如果一定要說的話,倒是比曾經更多了一些精心栽培的冰球月季、矮薔薇、藍鈴草、栗子樹和很多甚是調皮的小松鼠。和房屋的歷代主人一樣,羅杰這輩子也在花園里傾注了不少心血。幾乎每天都要抽出一小時修剪月季,經常性地匍匐在地照顧幼苗,春天時會為“炫耀著自身奇異光輝的藍鈴草們”倍感驕傲,入秋后也為收拾那些“被調皮松鼠們把玩得滿地亂滾的大小栗子”而頗感頭疼。
住在羅杰家的兩個月里,每天早上推開窗戶,我就能對著畢沙羅當年作畫時的方向欣賞到他眼中的風景。在天然的色彩搭配之下,各種綠色閃爍著點點熒光,各色紅葉點綴其間堪比團團火球;陽光下色彩光鮮,蒙霧中若隱若現;獵犬沖過林地去好奇地探索,火車穿過橋洞帶來遠方的客人。如今的景色幾乎完全與當年畫家筆下的風景重疊,時間在這里流逝的速度明顯放慢,使人打開一扇窗門,能看到兩個時代。縱觀現實和歷史、藝術與人文,無論如何,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畫家,能有幸住在畢沙羅的畫里,領會畫家的情懷,真是太好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