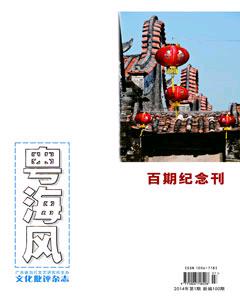粵海勁吹爭鳴風
國慶前夕,接到徐南鐵先生來信,要我為《粵海風》的百期紀念寫一篇小文。說實話,這些年由于我不斷陷入《香港小說史》、《張愛玲論》、《周作人論》等“學術泥潭”中,拔不出腳來,根本未能為《粵海風》寫稿,說來很對不住南鐵兄。既然南鐵兄不計前嫌,以德報怨,我還敢再躲懶、不效命嗎?我想到了一個題目:《粵海勁吹爭鳴風》,就此寫上幾句。
《粵海風》百期中,我的印象是頗為重視藝術爭鳴的。百期優點自然很多,當然不止重視學術爭鳴一點;但這一點卻特別為我所喜愛。我是一個喜歡學術爭鳴的人,2005年我特意編輯、出版了一本《袁良駿學術論爭集》(北京文史出版社),搜集了我從《要客觀地評價曹操——向郭沫若先生請教》(1959)至2004年四十多年間的五十多篇爭鳴文章。這本《論爭集》中的《通俗,豈與高雅無緣》、《丁玲 ,不解的恩怨與謎團》、《金庸先生對中國文學史的一個誤解》、《“周作人熱”與“漢奸有理”論》諸文,正是在《粵海風》上首先發表的。有念及此,我真是對《粵海風》、對南鐵兄充滿了感激!發表這些爭鳴文章,需要很大的學術氣魄,溫文爾雅、兩面玲瓏的先生和刊物是無法做到的。這里存在著一個重大的學術分歧。
在我們的古代先賢看來,“當仁不讓于師”。即使老師的觀點有錯誤,也要勇于糾正,“不讓于師”。西哲也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里,有一個東西方學術大師的契合點:既主張尊師重道,也提倡“不讓于師”。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才能開辟學術發展的最佳境界。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百舸爭流,正是一個最好不過的生動例證。被譽為“中國文藝復興”的“五四”時期也正是這樣,除了流派紛呈外,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也直追春秋戰國。1935年,在蔡元培、胡適之、魯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十卷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其中的《文學論爭集》盡力收錄了各家各派(包括“五四”新文學的反對派)的學術觀點,充分反映了“五四”文學革命中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
新中國建立之前直至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之前,毛主席、黨中央是大力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雙百方針”的。可惜的是“反右派擴大化”破壞了良好氣氛,百家爭鳴變成了“一家獨鳴”。“文革”的十年浩劫則造成了更加慘重的局面。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斗爭擴大化成為歷史,“雙百方針”重新得到了貫徹,成績是顯然的。然而,絕不可以低估“反右”、“文革”的創傷和陰影,百家爭鳴事實上存在著不少障礙。比如,“文革”過來的一批老學者不僅有“文革”余悸,而且有“文革”余痛,讓他們點名道姓批評那些與自己觀點相左的老學者、老朋友,不能不一再躊躇,掂量再三。比如,我公開點名批評范伯群兄的“兩個翅膀論”偏袒“鴛蝴派”,誣陷“文學研究會”,就是下了不惜斷交的決心的。結果,他的某些高足還是誣我是什么“文革遺風”,豈非冤哉枉也!再比如,文壇上一度出現了幾位“痞子作家”,他們拿罵人當飯吃,不管死的活的,逮誰罵誰。而且,專揀權威罵,權威越大(比如魯迅)罵得越來勁。他們有一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誰!”經他們一攪和,誰還敢點名批評別人?這些人的罵人,自然是一種“酷評”。然而,正常的點名批評,也往往蒙上“酷評”的惡滄了。魯迅曾說:“說婊子是婊子這不是罵,說良家女子是婊子這才是罵(《致肖軍》1935.1.4)。有幾個人記得魯迅這句名言?還有,“不讓于師”的同時,我們的老祖宗也大講“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當然有偉大的哲學價值,但用在學術批評中絕對不起好作用。周作人、沈從文等先生三十年代對魯迅的批評之一,就是嫌魯迅不務正業,大搞文學批評。時至今日,這樣的觀點還有沒有呢?恐怕很難說沒有吧!
障礙歸障礙,爭鳴歸爭鳴,為了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必須把學術爭鳴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這里,我想到了已經作古的雜文家何滿子先生,他對新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的點名批評,真是尖銳潑辣,蕩氣回腸!當然,他老先生曾經說過“不讀金庸也可以批評金庸”,這當然是不對的。但他并非一點不看金庸,只不過不像老朽那樣,一本一本拜讀過全部金庸作品罷了。
“粵海勁吹爭鳴風”,我衷心希望《粵海風》成為“南方巨柱”,在倡導百家爭鳴中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