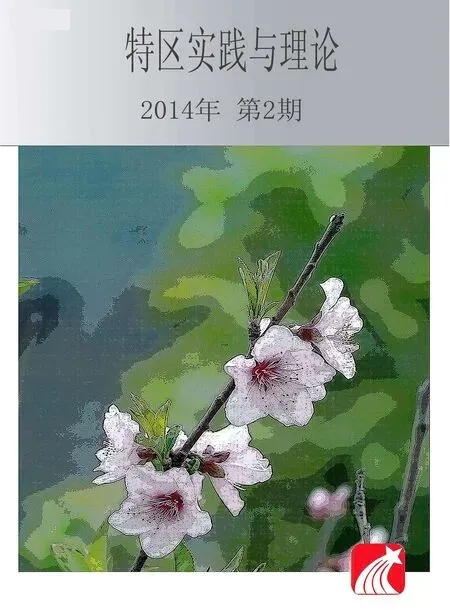中英兩國戒毒模式對比
楊細桂
2013年底筆者赴英國參加了由中國司法部舉辦的戒毒培訓班,期間,先后考察了英國戒毒體制、戒毒機構整體運作模式等,本文就此次學習考察的感受與思考,對英國的戒毒體制及模式進行分析研究,借鑒其先進經驗,以期對我國當前的戒毒工作有所裨益。
一、英國戒毒體制綜合考察研究
(一)法律建設與司法管轄
以2001年為例,英國吸食毒品人數占其總人口的7.4%,大約1180萬人曾經服用過違禁藥品。更為嚴重的是,21世紀初以來,由于合成毒品開始在全球泛濫,使得禁毒工作形勢變得更為復雜和艱難。伴隨吸食毒品人數的不斷增多,由此引發的違法犯罪行為也日益劇增,社會治安受到嚴重影響,家庭問題顯著增多。為此,英國政府與社會開始反省毒品危害和關注禁毒工作,從20世紀70年代起,英國先后制定了《不當使用藥品法》、《藥品分類管理法》、《警察與犯罪證據法》等一系列法律,以此來規范政府部門、警察機構和社會組織有效開展毒品管控工作。
目前,英國的法院體系大體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為脫胎于上議院的最高法院,第二層級為次高法院,亦稱上訴法院,第三、四層級法院中,民事法院分為郡法院和專業法庭;刑事法院分為刑事法院和治安法庭。英國治安法庭是較為特殊的法庭,其法官并非職業法官,而是根據陪審團制度,由法庭工作人員從所在社區具備相關資質的公民中抽簽確定三人作為法官。治安法庭主要審理簡易案件、青少年案件和家庭案件,并負責將其受理的青少年重罪案件或者性質較復雜案件轉呈刑事法院。目前,治安法庭承擔了全英90%以上的案件,所審理裁定案件的刑期一般不超過6個月,而幾乎所有的涉毒案件由該類法庭負責審理。
(二)戒毒機構設置及運作
英國戒毒機構主要包括監獄、公立戒毒中心以及類似“生命線組織”的非官方性社會戒毒機構等三大類別。雖然三者分別隸屬于監獄系統、公共醫療系統與民間社會組織,但在日常戒毒工作中相互建立了緊密協作關系。
英國共有154家監獄,每一個監獄內都設有戒毒中心,目前共有4.9萬名在押犯人自愿加入戒毒當中。凡在押犯人自主提出戒毒訴求的,獄方都會為其提供相應的戒毒服務,涉及戒毒的所有費用均由政府承擔。英國監獄刑釋人員再犯率為46%,而涉毒成人犯再犯率高達56.3%。因此,英國戒毒研究認為,監禁戒毒不但成本高而且戒毒效果也不如社區治療戒毒的好。
公立戒毒中心由政府按照行政區劃設置,中心內分設雷達部、護理部、康復部等不同職能部門,主要依據吸毒者成癮程度開展應急處理、藥物治療和心理干預等戒毒工作。雷達部主要針對被地方警察送達的酗酒滋事和吸毒犯罪者開展戒除酒癮、毒癮工作,一般會待其清醒時與之簽訂戒毒合同,約定權利義務、戒毒期限、戒斷目標及其它事項。中心收治更多的還是因吸毒犯罪而選擇“辯訴交易”程序的吸毒人員,一般需要等待5到7周才能入住此類中心。這些因“辯訴交易”免受牢獄之災的吸毒者,都必須接受有關機構和工作人員的跟蹤調查,身上會安裝一個特制的電子科技產品,一旦未經許可越出劃定的活動范圍,會即時招來警察的特別“關照”。
英國非官方組織開辦的戒毒機構大約有25家,彼此間存在競爭關系。此類機構一般不設病床,只對特定對象提供戒毒知識支持、心理輔導、社交網絡搭建、職業技能培訓、就業推薦,以及對青少年學生開展戒毒宣傳等。機構運維費用除向戒毒者收取外,也會接受社會捐贈,同時還會游說及獲取地方議會和政府的相應支持。
另外,英國政府也高度重視社區戒毒工作,一般以一個社區戒毒中心為核心,覆蓋到附近社區,吸引上百名吸毒、嗜酒等非健康人群參與其中。在所有戒毒社區中,均配備有一名專職工作者,負責聯絡、組織等事務。目前,這類人員的年薪固定為3萬英鎊,而參加社區戒毒者則須由其本人承擔房租、水電等費用。
(三)戒毒工作的政府投入與社會評價
在工黨領袖布萊爾擔任首相期間,英國政府十分重視戒毒工作,于2001年成立了英國戒毒政策戰略委員會,其職能大致相當于我國國家禁毒委員會。英國中央政府每年向該委員會撥款8億英鎊,主要用于戒毒工作政策宣傳、戒毒人員治療、職業技能培訓以及戒毒工作研究等。英國每年投入戒毒工作的經費高達約150億英鎊(其中包含戒酒費用開支,因為英國將戒酒、戒毒一并納入和同等對待),其中還不包括戒毒機構運作及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據介紹,英國政府每年為每一名監獄服刑人員支付的費用約為3.5萬英鎊;而加入公立戒毒中心及參加社區戒毒者,每人可獲得2000英鎊的資金資助,由社區組織按實際產生費用轉撥給相關戒毒機構。但是,如果戒毒人員因復吸后再次戒毒的,則全部戒毒費用由其本人或家庭承擔。
2011年以卡梅隆為首的保守黨執政后,英國政府的戒毒政策作了非常大的調整,2012年取消了專門的戒毒政策戰略委員會,其職能被拆分到醫療、警察、教育等多個政府部門。受困于當前經濟不景氣之現狀,英國政府大幅削減了中央政府的戒毒經費,轉而將戒毒工作視為社會事務全部交由地方負責。當然,這也與前工黨政府戒毒政策與戰略已取得的顯著成效有相當大的關系。
據了解,英國社會對政府禁毒工作普遍認可和支持,但也有部分民眾認為在具體操作方面仍有不公平的現象。例如涉毒犯罪人員一旦成功實現“辯訴交易”,在進入公立戒毒中心后每人可獲得2000英鎊的政府戒毒資金支持,而沒有犯罪的嗜毒者自愿再次戒毒卻需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費用。
二、中英兩國戒毒模式對比
(一)法律定性不同
我國《禁毒法》作為我們開展戒毒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據,明確表明吸毒者既是違法者,也是受害者和病人。這就開宗明義地表明,吸毒人員首先是違法者,必然要使其付出應有代價,得到應有懲罰。
在英國,人們并不將吸毒行為視為違法。依據《藥品分類管理法》,英國政府將所有藥品分為A、B、C三類:A類包括海洛因、可卡因等毒性特別強的毒品;B類包括安非他命、鴉片等毒品;C類是其他弱一點的毒品。A類藥品以7克為限,B、C兩類則逐漸遞增。以A類藥品為例,若持有或攜帶不超過7克A類藥品的視為自用,超過此限度的才會招來警察的麻煩。英國政府會不定期更新藥品分類目錄,甚至將酒、煙也列入目錄管理范圍當中。他們認為,政府的責任是打擊毒品犯罪,而不是禁絕毒品。吸毒行為本身不違法,只有當吸毒者的相關行為危害社會與公共安全、危害他人生命與財產安全時,才會受到法律追究。因毒犯罪而遭逮捕后,有60%的吸毒者通過“辯訴交易”程序來逃避牢獄之災,選擇在社區、“生命線組織”等戒毒機構或公立戒毒中心接受戒毒。
(二)職能定位不同
我國《禁毒法》規定,公安與司法行政機關均可設置強制隔離戒毒所,對吸毒人員實施強制隔離戒毒。這就表明戒毒機構與戒毒者之間是一種“強制與被強制”、“管理與被管理”的法律關系,戒毒場所對戒毒者負有管理職責,對其人身安全承擔監管責任。
在英國,則是所謂“不自愿、無戒毒”,即便有人因吸毒違法犯罪,如果當事人不愿意,就是進了監獄也照樣可以吸食毒品。據介紹,最近幾年,英國每年逮捕的涉毒犯罪者為18萬人,近半數沒有納進戒毒措施當中,而納入戒毒措施的,個人自愿與家人強制的各占一半。戒毒者與戒毒機構之間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兩者之間是平等的,不存在管制問題,彼此權利與義務及其法律責任都在所簽合同中作了明確約定。除監獄外,戒毒機構普遍將戒毒者視為“客戶”,并希望通過提供最好的服務以取得更好、更廣泛的社會聲譽,借此爭取潛在客源并從地方政府、議會博取更多資源。
(三)管理主體不同
我國的強制隔離戒毒場所分別隸屬于各地公安機關或司法行政部門,其工作人員均是由政府招聘、培養、使用和管理,列入公務員序列并實行職級分類管理。基層管理人員相當大程度上仍是管理、教育、心理輔導與習藝勞動組織等多種責任“一肩挑”,真正的心理學與教育學專才并不多,而這種封閉式的戒毒管理模式也難以獲取社會資源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參與。
在英國,戒毒機構的工作人員超過一半是曾經的吸毒者,因為英國人認為只有他們才能真正了解戒毒人員的實際需求和心理變化,也因此才能夠提供最適切的服務。擁有750名專職戒毒工作人員的“生命線組織”,是一家英國最大的非政府組織開辦的戒毒機構,機構C E O就曾有25年的吸毒史,而相當多的社工也是戒毒成功后轉而自愿過來幫助工作的。戒毒機構當中的心理師與醫護者占比過半。至于職業技能培訓工作,他們主要委托下游組織或中小企業負責。根據戒毒者的需要,戒毒機構會及時與監獄、警察、醫院、社區、企業、學校及家人聯系,且非常容易獲取各方面的支持。
(四)戒毒理念不同
我國《禁毒法》頒行僅僅5年多時間,基于吸毒人群既是違法者又是受害者和病人這一法律定性,對于如何開展戒毒工作,各地尚處于摸索和試點階段。《禁毒法》規定強制隔離戒毒時間一般為兩年,雖然可以使吸毒人群較長時間擺脫毒品,藉此也有效減少了社會管理成本,但某種意義上會阻隔吸毒人員與社會的聯系。實際工作中,我們十分關注吸毒人員如何與社會互動聯絡、如何喚起家人對其親情關懷、如何為吸毒者謀求一份穩定工作,以此鞏固和提高戒毒效果。
在英國,人們普遍認為吸毒現象是社會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幫助吸毒者戒斷毒癮應該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無論政府部門、社會機構還是各類企業,均樂于為戒毒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目前,英國各戒毒機構一律采用“十二步戒毒法”開展工作,此種方法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礎上。據介紹,英國戒毒研究表明,參加積極的社會交際者戒斷率比不參加者要高27%,他們認為:面對毒品誘惑,人的抵抗力是有限的,但有了親友與社會關心,人的內心可以變得更為強大;心理輔導與高度頻繁的心理干預能給吸毒者提供最好幫助;職業技能培訓既能提高其自信心,也可以為其謀生創造更好條件。戒毒機構十分尊重戒毒者的個人隱私權,除公眾場所外,一律不安裝監控攝像頭;對于吸毒導致的精神病患者,除非明顯帶有攻擊傾向者須送專門的精神病院外,戒毒機構通常會根據疾病程度的不同,安排1至3名工作人員24小時跟蹤照管,決不會使用約束手段來對待。社區健康中心在戒毒工作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根據吸毒者使用毒品的類型采用不同的替代藥品予以治療,認為使用美沙胴、丁丙諾菲等替代藥品比生硬的強制脫離非法藥品的“干戒”更人道、更有效果。
(五)評估標準不同
目前,我國尚沒有明確而權威的戒斷標準及戒斷率評估數據,但以近年來廣東省有關機構組織實施的跟蹤回訪調查問卷設計來看,傾向于將三年內無復吸者認定為成功戒斷者。
在英國,其專家學者提供的戒斷率為29.6%,他們主要依據戒毒合同的約定來進行評估,同時也會進行跟蹤調查來檢查戒毒效果,通常是根據“六個月內有無復吸、有無固定住所、有無穩定工作、有無恢復和諧的家人關系”等標準來認定。
三、啟示與借鑒
(一)基層組織應履行好應有責任
我國《禁毒法》對戒毒措施有明確規定,除個人自愿戒毒和強制隔離戒毒外,還有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作為重要補充,各項措施之間應該做到無縫銜接。《禁毒法》實施5年多來,現實情況是公安機關對查獲的吸毒者一般首先會責令其社區戒毒;同時,強制隔離戒毒所在認定身體狀況不適宜繼續強制隔離戒毒時,也可以將強制隔離戒毒人員變更為社區戒毒。但由于各種原因,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仍然無法有效得到落實,一些本應由街道(鄉鎮)、社區(村組)負起監管責任的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人員難以有效掌控,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實質上可以說是有名無實。對此,建議立法機關通過檢查《禁毒法》實施情況,督促相關基層組織切實擔負起法律責任和義務。
(二)讓社會企業更多參與到戒毒工作中來
實踐證明,通過職業技能培訓,讓戒毒人員擁有一技之長以增加其謀生能力,是提高戒毒效果的重要保證。受制于師資、場地、經費及社會就業需求信息滯后等諸因素,目前,強制隔離戒毒場所職業技能培訓條件十分有限,培訓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為此,建議引導和鼓勵各類社會企業積極參與戒毒工作,為戒毒人員職業技能培訓和就業提供必要支持。例如,可從社會責任和經濟補償兩方面考慮,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方式,通過自主報名和擇優選擇等形式,鼓勵部分既有社會責任心、又有用工需求的企業,加入到戒毒人員職業技能培訓工作中來。強制隔離戒毒場所可將獎勵減期時間視為戒毒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時間,讓這部分人提前進入到社區企業中,并借助電子科技手段履行適度的管理責任,對惡意違反企業管理制度者可收回場所繼續執行剩余期限。這樣既可以更好調動戒毒人員的積極性,還可以有效促進其就業,減少因就業困難造成新的社會危害。
(三)充分發揮專業戒毒機構職能作用
強制隔離戒毒所除履行好對所內戒毒者管理教育職責外,還可以同街道(鄉鎮)及其轄區社工組織建立緊密的工作關系,憑借自身優勢與自愿戒毒、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等社會機構建立密切協作關系,在戒毒者身體康復與心理輔導等方面提供幫助。同時,強制隔離戒毒場所應該加大力度調整工作人員結構,走專業化戒毒之路,吸收更多心理學、教育學、醫護學等專業人員進入場所工作。隨著街道、社區等社會參與度的提高,場所可以繼續深化與外部社會的聯絡,將專業技能滲透到社會戒毒組織的最末端,引領全社會共同關注和推進戒毒事業。
(四)調整禁(戒)毒宣傳工作思維模式
對于戒毒宣傳工作,往往媒體宣傳某類型毒品的危害,此類非法藥品必定價漲需增;而一旦對該類藥品實施嚴格管控,新的更為復雜的同類藥品就會不日問世。因此,有關專家認為針對特定藥品的宣傳,只會增加戒毒難度而不會促進戒毒工作,且結果往往事與愿違。這一現象是因為人們的好奇心理、從眾心理、對社會管理的預期心理在特定情況下會高度重疊,特別是在現代互聯網等科技手段和傳媒影響下,不少辨識能力不強的人會誤將吸毒當成時髦,從而走上吸食非法藥品的歧途。對此,我們不妨改變一下傳統的禁毒宣傳模式,比如適當減少電視宣傳頻次,特別是減少對低齡人群的涉毒宣傳活動,同時,在宣傳內容的選材方面,應當多宣傳成功脫毒者,宣傳社會中支持戒毒事業的企業家等正面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