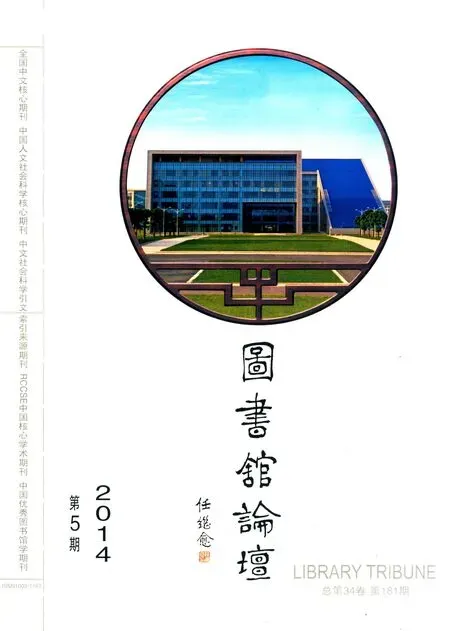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的歷史演變及其特點
王靜芬
1 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精神溯源
在美國的建國史中,《五月花號公約》《弗吉尼亞權利法案》《獨立宣言》和《美國聯邦憲法》作為初始重要的文件體現著契約、自治和平等精神。其中,《弗吉尼亞權利法案》的基本精神是人的平等性,并闡述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其他各州權利法案的示范”[1],“如同一座燈塔”[2]對其后許多政治文獻產生影響,如1776 年的《獨立宣言》、1787 年的《美國聯邦憲法》 乃至1791 年的《美國權利法案》[3-4]。
美國圖書館協會委員會(ALA Council)于1948 年6 月18 日發表了《圖書館權利法案》(The Library Billof Rights)(以下簡稱“《法案》”)。作為一種歷史產物,《法案》必然帶有社會發展階段的特點,承襲美國歷史傳統精神和價值取向。“可以肯定的是,佛雷斯特·斯波爾丁在使用‘Library’s Bill of Rights’這個題名時,可能受到了英國1689 年頒布的確立君主立憲制的憲法文件《權利宣言》 和美國1791 年通過的憲法補充文件《美國權利法案》 (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甚至美國1776 年起草的《弗吉尼亞權利法案》(The Virginia Declarartion of Rights)的影響,因為這些權利法案是美國人研究和起草有關‘權利’文件的基本文獻和依據”[5]。
2 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的歷次修訂及內容
2.1 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的誕生背景
《法案》提出的背景事件可以追溯至1937年,當時的美國社會正遭受經濟大蕭條的沖擊,對言論的限制以及圖書審查制度的控制相當嚴格。蒙大拿州立大學圖書館館長飛利浦·基尼(Philip O. Keeney)因不愿意剔除校方要求的具爭議性圖書而遭到解雇[6]。這一事件引起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的注意,ALA 的圖書館員薪資、職員及職位委員會(Board on Salaries,Staff,and Tenure)向蒙大拿州立大學校長提出抗議,要求校方尊重圖書館員的專業以及權利。但是因為當時社會對于圖書館員的專業認知不足,協會抗議的影響力不大。1938 年,愛荷華州德梅因公共圖書館(Des Moines)館長佛雷斯特·斯波爾丁(Forrest Spaulding)有感于自由言論的限制以及圖書審查制度所造成的日益偏執的觀念,必將影響該館所服務的讀者權利,因而提出了《免費公共圖書館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 for the Free Public Library),其內容為:(1)由于圖書和其他讀物的購置得到公共資金的資助,因而選書應以德梅因市居民的利益及其興趣為立場,不應以作者的種族、國籍、政治或者宗教觀點作為選書標準。(2)在圖書館可收集的資料范圍內,對存在不同觀點并有爭議的問題的圖書應平等地對待。(3)對組織、宗教、政治、兄弟會或者地方社團的正式出版物或宣傳品,其收集不應有所區別,而應將其視為饋贈并供讀者取用。由于購置圖書和讀物的經費貧乏,圖書館不可能購置所有團體出版物。如果僅購買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另一部分,存在歧視之嫌,因此,必須制定這一政策。(4)應以平等原則向所有非營利團體提供圖書館會議室,不收取費用,不應排斥任何人[7]。這個法案主要從四個方面來闡明圖書館的服務政策:(1)選書立場,應平等地選擇讀物;(2)對爭議問題的處理,應平等地面對有爭議的圖書;(3)對各種組織或社團出版物或宣傳品的收藏政策,應平等地收集社團贈品;(4)會議室的開放原則,應基于平等條件開放圖書館會議室。這四個觀點全部都提到一個詞:平等,針對社區圖書館館藏以及館舍的利用做出平等服務的政策規定。
這一法案對當時的美國公共圖書館服務提供了一個示范樣例。這并不是僅限于某一社區圖書館的問題,而是整個美國的圖書館共同面臨的問題:如何限定及保護圖書館的平等權利。這一法案最終由德梅因公共圖書館理事會提交到美國圖書館協會理事會予以審議,并最終成為《法案》的雛形。
觸動ALA 并使之制定讀者服務原則和政策的事件是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環境下,社會上出現的禁書毀書事件。1939 年,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美國社會紀實文學《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出版。這部長篇小說著重描寫加州中西部農業民工被農場主壓迫的困苦狀況,反映美國一代破產農民怎樣向產業工人轉變的現實問題。美國各州統治集團對此相當不滿,施壓于公共圖書館。伊利諾伊州、新澤西州和加州等地區圖書館被迫將這部小說列為禁書。同年,據加州的報章報道,當地政治委員波默羅伊(Harold Pomeroy)曾非常自信地說:“本州協會將支持在公共圖書館禁止這本書的任何行動。”[8]而加州克恩縣免費圖書館(Kern County Free Libary)館長倪芙(Gretchen Knief)則提出:“這樣的審查制度將是圖書館歷史上的第一例。讓我擔憂的是‘它能在這里發生’。如果這本書被禁止,那么明天什么書將會被禁呢?”盡管言辭懇切,但倪芙迫于董事會的壓力,最終還是將此書從總館和分館的書架上抽離[9]。由禁書事件引發的圖書審查逐漸發展為對圖書館服務價值和傳統的挑戰。重視圖書館權利的呼聲日漲,推動了美國圖書館協會以《免費公共圖書館權利法案》為藍本,經適當修改后,成為《法案》的1939 年版本。
2.2 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的修訂歷史
為了更好地宣傳圖書館權利以及確立原則,1940 年ALA 理事會建立了智識自由委員會(the Intellectual Freedom Committee,IFC)。IFC是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和《法案》,由ALA 理事會通過,為保障圖書館用戶、圖書館以及圖書館員的權利而建立起來的。當發生觸及知識自由以及審查問題等的事務時,IFC 將與ALA 其他部門和工作人員開展緊密合作[10]。1944 年,IFC 主席卡諾夫斯基(Leon Carnovsky)在向ALA 理事會提出的報告中指出:只有極少數的干擾圖書館員選書的事件得到報道,這可能意味著沒有事件發生,也可能意味著圖書館員并不在意這些干擾的報道,甚至可能意味著圖書館員在圖書選擇政策上相當謹慎,在可能遇到干擾之前就規避了事件的發生[11]。這個報告內容暗指ALA 應該重視圖書館選書的標準和立場。同年,約翰·卡爾森(John Roy Carlson)的《內幕》(Under Cover),和莉莉安·史密斯(Lillian Smith)的《奇異的果實》(Strange Fruit),都因有悖于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而被列為禁書。其中,《內幕》描述了20 世紀30 年代末40 年代初美國法西斯主義組織的情況,《奇異的果實》描述了分別屬于黑人和白人兩個種族戀人之間的愛情。面對1944 年的禁書風波,IFC 主席卡諾夫斯基提議修訂《圖書館權利法案》的第一條款,最終得到通過。1944 年版本增加了這樣的內容:“圖書館不應僅僅因為一部分人的不贊同而移除或禁止描述確切事實(factually correct)的圖書。”[12]1948 年,在IFC 主席博寧豪森(David K. Berninghausen)的提議下,ALA 理事會通過了對《法案》的修訂。
1950 年,隨著麥卡錫主義影響的擴大以及新媒體的出現,ALA 理事會面臨新的問題。伊利諾伊州的皮奧里亞公共圖書館(Peoria Public Library)因為提供《邊界》 (Boundary Lines)、《手足情》 (Brotherhood of Man)和《蘇聯人》(Peoples of the USSR)三部電影予以流通,遭到伊利諾伊州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Peoria American Legion)的反對,并向圖書館施壓,要求移除這些館藏。由于《法案》的條款只針對圖書和其他讀物,并未明確包括非紙質資源,因此,一些圖書館員認為《法案》僅適用于紙質文獻,而對非紙質文獻的審查制度采取漠視態度[13]。有見及此,ALA 在1951 年仲冬會議上補充了對法案適用范圍的說明:“《圖書館權利法案》應適用于圖書館收藏或使用的所有供交流的資料和媒體。”[14]
1961 年,ALA 對讀者自由平等地使用圖書館的權利作了明確聲明:圖書館不得因讀者的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觀點而拒絕為其服務。1965 年,ALA 在華盛頓仲冬會議前的一次針對知識自由的預備會議上,集中討論了“擁有充分事實根據、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圖書或者其他讀物不應因其黨義或者教義的不同被宣布禁止或被剔除”這一條款。與會者對該條款的批評源于一個真實案例:伊利諾伊州貝爾維爾(Belleville)的一位天主教圖書館員拒絕將新教徒的出版物《教會與國家》(Church and State)列入館藏,并且援引了《圖書館權利法案》的這一條款作為他的正當理由[15]。此事例說明條教中“擁有充分事實根據、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這一表述而且也容易被濫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圖書館的館藏作了不必要的限制。根據該會議討論的結果,ALA 在1967 年對《法案》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訂。
1980 年修訂的《法案》在內容上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文字表述上的精簡和調整,重點仍強調對館藏選擇的平等中立,對個人平等使用圖書館服務的權利予以保護,以及公眾使用會議室的平等原則。1996 年《法案》的內容沿用了1980 年的版本,重申應取消對年齡的限制和歧視。
《法案》是一份指導美國圖書館服務的基本原則聲明[16]。在實際工作中,還需要有明確的操作指引來解決具體細節問題。因此,IFC 起草并獲ALA 理事會批準,頒布了一系列對《法案》的闡釋、Q&A 等文件,并陸續對闡釋文件予以修訂。
2.3 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修訂內容分析
《法案》自1939 年6 月19 日由ALA 理事會通過最初版本,隨后歷經了1944 年10 月14 日、1948 年6 月18 日、1961 年2 月2 日、1967 年6 月27 日、1980 年1 月23 日,以及1996 年1 月23 日的6 次修訂。每次修訂無不是伴隨著社會和歷史的發展,針對圖書館實際工作中對法案原則的存疑,是圖書館界為讀者爭取平等權利的積極響應。其中,1948 年和1967 年的版本修改幅度較大。
1948 年《法案》的修訂情況:(1)卷首語為“美國圖書館協會理事會重申其信念,以下基本政策應該成為全部圖書館服務之指導”。這一修訂簡化了制定法案的目的,明確其為適用于全部圖書館服務的政策,使之具有廣泛而普遍的指導意義。(2)第一條款修訂為:“作為圖書館服務的職責所在,挑選的圖書和其他讀物應基于社區中所有民眾的興趣、信息和啟迪教化,任何資料不可因為作者種族、國籍、政治或宗教觀點不同而遭排斥。”與1939 年相比,一方面強調圖書館在館藏選擇上負有責任,應該予以重視;另一方面也指出圖書館在這方面應該具有主動性。文字上刪除了之前“源于公共資金的資助”的字句,使該法案的原則適用于各種類型的圖書館,強調資源獲取與選擇的平等與公正,并確立選書的原則是基于所在社區的“全體民眾(all people)”的興趣、資訊和啟迪教化。(3)第二條款中,特別提出“擁有充分事實根據、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圖書或者其他讀物不應因其黨義或者教義的不同而被宣布禁止或被剔除”,這是針對當時社會上的一些偏見所做出的修訂。(4)第三條款針對挑戰圖書館平等精神的社會現象,特別提出了“由道德、政治見解的志愿仲裁者或者將建立美國主義強制概念的組織所強烈要求和實施的圖書審查制度,必然受到來自圖書館的挑戰。”這是首次在《法案》 中明確提到“審查制度(censorship)”,表明圖書館反對審查制度的態度,也表明了美國圖書館協會堅持思想自由傳播的立場。(5)新增第四條款,提出圖書館應該聯合各種可能團結的力量,以抵抗外界對思想自由交流和表達的限制,強調圖書館應該捍衛自由的思想交流和充分的思想表達[17]。
1967 年《法案》的修訂情況:首先,第二條款刪除了1948 年版本提到的“擁有充分事實根據、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圖書或者其他讀物”這一表述,文字上更為簡潔,避免出現因不必要的表述而引起的濫用。同時,將原來的“圖書和其他讀物(books and other reading matter)”更改為“圖書和其他圖書館資料(books and other library materials)”,擴大了館藏載體的范圍,延伸至圖書館全部館藏資料;其次,精簡第四條款,擴大可合作對象,共同抵制任何限制思想自由傳播的思想和行為。同時,刪除了第四條款中的“美國人的傳統和傳承”(the tradition and heritage of Americans),避免流露民族主義情緒;最后,第五條款新增了“年齡(Age)”“社會(Social)”兩點,列入不得歧視的聲明中[18]。
2.4 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歷次修訂特點
(1)文字表述精簡化。在針對收藏選擇資源應平等公正的第二條款內容中,1939 年提出“應該公正而充分地選擇各種體現不同觀點的資料”。1944 年特別提出不可剔除“描述確切事實(factually correct)的圖書”。1948 年采用“擁有充分事實根據、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的圖書或其他讀物”的表述。1967 年刪除了這一描述,避免出現可能的濫用。這個修訂過程一方面體現了ALA 能夠及時順應社會歷史的發展,做出相應的政策規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用下定義的方式無法囊括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情況。圖書館學家阿什海姆(Lester Asheim)針對選書原則,提出“在選書時,我們試著明確資料入藏的各種理由;但其實,在審查制度下,你只需要一個理由就可以剔除它”[19]。文字的精簡顯示了《法案》修訂的成熟。
(2)文字去情緒化。《法案》的卷首語修訂了兩次。1948 年的第一次修訂,刪除了“因為世界上許多地區逐漸偏執于限制自由言論,并以審查制度影響著少數族群和個人的(平等和自由)權利”的表述,1980 年的第二次修訂則明確“所有圖書館都是信息和思想的論壇”。此外,在第三條款針對審查制度的立場和態度上,1948 年增加了關于審查團體的描述,但在1967 年的修訂中又刪除了這些文字。這種處理避免了政策在文字表述上的情緒化。
(3)順應社會歷史的發展。在社會上出現禁書風波的時候,《法案》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圖書館應持有的立場和觀點。在面對關于個人平等使用圖書館的討論時,1961 年新增了第五條款:“個人使用圖書館的權利,不得因為其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觀點而遭拒絕或褫奪。”這一補充條款將圖書館服務對象擴大到所有人,包括了少數族群、殘疾人和被監禁的人,種族、宗教、國籍或是政治觀點都不應該成為個人使用圖書館的限制。1967 年在這一條款中新增了“年齡(Age)”“社會(Social)”兩點。1996 年再次重申不可因年齡而令讀者的圖書館使用權受到限制。可見隨著未成年人使用圖書館的服務不斷受到重視,《法案》也相應地做出了指引。
(4)《法案》 精神貫徹始終。雖然《法案》歷經多次修改,但其平等、自由的精神始終如一:第一,平等、自由使用圖書館的權利。盡管社會上存在禁書風波等壓力,ALA 還是堅持圖書館應平等、公正地選擇館藏資源,并呼吁圖書館應挑戰任何審查的壓力。第二,強調圖書館選擇館藏的主動性。始終重視圖書館應基于其服務的社區全體民眾的興趣、資訊需求和實現啟迪教化的目的來進行館藏選擇。這是圖書館服務的職責所在。第三,隨著平等觀念的發展,不斷擴大個人使用圖書館的平等權利。從種族、宗教、國籍、政治觀點,至社會觀點、出身、年齡等各方面堅持圖書館所應持有的平等原則和立場。
(5)《法案》的可擴容性。《法案》作為政策指引,確實無法包羅萬有。在實際工作中,需要有細致而明確的操作指引解決在圖書館服務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因此《法案》 的闡釋、Q&A 等文件,在指導圖書館實際工作中起著重要作用。從最早于1951 年7 月頒布的《標注與等級劃分系統》(Labeling and Rating Systems)[20],到最近于2010 年新增的《在獄人士的閱讀權利》(Prisoners Right to Read)[21],IFC 至今已經頒布了22 條《法案》的闡釋。這些闡釋隨著圖書館界新問題的出現,不斷得到修訂和補充。
3 結語
從《圖書館權利法案》的歷次修訂,可以看到美國圖書館協會對圖書館服務的平等、自由、公正、開放等原則不斷重申和細化說明。其修訂的次數越多,補充的解釋文件越細致,說明美國圖書館政策正隨著社會歷史環境的發展而不斷進行自我調整。隨著《法案》歷史演變的推進,每個時期都為下一次修訂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法案》也不斷得到完善:從實踐中形成指導理論,進而用理論解決現實出現的問題,再次為理論的修訂積累素材。這個循環往復的過程促進了美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和成熟。
[1] 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M]. 鄧正來,譯. 北京:三聯書店,1997:229.
[2] John Kukla,ed.,The Bill of Right:A Lively Heritage[M]. Va. : Richmond,1987:6.
[3] Robert Allen Rutland. The Birth of the Bill of Rights:1776- 1791[M].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1:36.
[4] 張友倫. 美國民主制度的形成、發展和問題[J]. 歷史研究,1996 (2):118- 132.
[5] 程煥文. 圖書館權利的來由[J]. 圖書館論壇,2009(6):30- 36.
[6] Louise S. Robbins, Rosalee McReynolds. The librarian spies:Philip and Mary Jane Keeney and Cold War espionage [M]. Westport,Connecticut: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9:4.
[7] Judith F. Krug, James A. Harvey. A history of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 [J]. American Libraries, 1972(3):80.
[8] [9] Marci Lingo. Forbidden Fruit: the Banning of the Grapes of Wrath in the Kern County Free Library [J].Libraries& Culture,2003 (4):351- 377.
[10]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 Intellectual Freedom Committee (IFC) [EB/OL]. [2013- 09- 09]. http:/ /www. ala. org/ groups/ committees/ ala/ ala- if.
[11] Ruth E. Hammond , Donald Kenneth Campbell,Russell J. Schunk, et al. The Administration of Libraries[J]. ALA Bulletin,1945 (10):389- 394.
[12] Judith F. Krug, James A. Harvey. A History of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 [J]. American Libraries, 1972(1):80- 82.
[13] David K. Berninghausen. Film Censorship [J]. ALA Bulletin,1950 (11):447- 448.
[14] News Roundup — 1951 Midwinter Meeting [J]. ALA Bulletin,1951 (3):93- 99.
[15] Ervin J. Gaines. Intellectural Freedom [J]. ALA Bulletin,1965 (9):785- 786.
[16] 程煥文. 圖書館權利的界定[J]. 中國圖書館學報,2010 (2):38- 45.
[17]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Library Bill of Rights [J].ALA Bulletin,1948 (7):285.
[18] Office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Intellectual Freedom Manual [M]. 2nd ed.Chicago: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1983:14.
[19] Beverly Goldberg,Judith F. Krug. On the line for the First Amendment [J]. American Libraries,1995 (8):774- 778.
[20] ALA Council,Labeling and Rating Systems [EB/OL].[2013- 09- 09]. http:/ /www.ala.org/ advocacy/ intfreedom/librarybill/ interpretations/ labelingrating.
[21] ALACouncil,PrisonersRight to Read [EB/OL]. [2013- 09- 09]. http:/ /www.ala.org/ advocacy/ intfreedom/librarybill/ interpretations/ prisonersrighto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