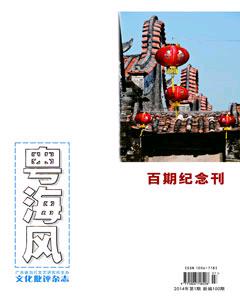來自南方的風(fēng)
樊星
南國(guó)盛開思想文化的奇葩。《南方周末》、《天涯》、《隨筆》,還有作為“全國(guó)首家文化批評(píng)雜志”的《粵海風(fēng)》,以及曾經(jīng)不脛而走,卻終于突然消失的《海南紀(jì)實(shí)》、《街道》,都因?yàn)楦矣谥毖袁F(xiàn)實(shí)的憂患、勇于披露被遮蔽的歷史而在當(dāng)代思想界留下了包括磨滅的清晰足跡。雖然都知道“文革”結(jié)束以后,思想解放、文化多元已成浩浩蕩蕩的時(shí)代主潮,但風(fēng)向的多變常常左右著潮流的漲落,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shí)。不時(shí)也耳聞目睹了一些勢(shì)頭頗好的思想文化報(bào)刊或被寒潮摧折、或被風(fēng)雨襲擾的消息,但這么多年過去了,它們基本上保持了難得的獨(dú)特品格,一直在思想文化界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一現(xiàn)象,值得研究:南方,為什么是南方?
雖然,北方也有北方的人文風(fēng)景,先有《讀書》,后有《炎黃春秋》,還有1990年代曾經(jīng)飲譽(yù)一時(shí)、終于不幸夭折的《東方》(不是民國(guó)年間鼎鼎大名的《東方雜志》)和《方法》,都因?yàn)楦挥兴枷氲匿h芒、文化的新知、獨(dú)立的品格、自由的精神而成為當(dāng)代思想文化的旗幟;盡管如此,南方依然有南方的獨(dú)特風(fēng)采。
南方有南方的人文傳統(tǒng)——那里誕生了康有為、梁?jiǎn)⒊摹白兎ā彼枷牒蛯O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現(xiàn)代中國(guó)政治思想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那里孕育了香港的經(jīng)濟(jì)起飛、深圳的特區(qū)試驗(yàn),為大陸的經(jīng)濟(jì)改革開辟了新的道路;那里的“嶺南文化”(一般認(rèn)為:“包容”、“開放”、“務(wù)實(shí)”、“重商”是“嶺南文化”的精神)自成一派……這幾年的《粵海風(fēng)》專辟“嶺南文派”選刊,對(duì)于進(jìn)一步倡導(dǎo)“嶺南文化”精神,功不可沒。(另一方面,我也覺得相關(guān)的研究似乎還不夠深入,還應(yīng)該有更縱深的展開。)在我看來,這一點(diǎn),是《粵海風(fēng)》的一大看點(diǎn)——突出南方文化的思想建樹,為當(dāng)代的思想文化建設(shè)提供開拓新路的重要參考。
南方還有南方的風(fēng)格——雜花生樹、不拘一格。無(wú)論是談胡風(fēng)、還是憶“文革”,說掌故、還是話當(dāng)今,都能百花齊放、百草競(jìng)長(zhǎng),名家與新銳共同切磋,思想與閑話一起鳴響;沒有“黨八股”,也少有“理論腔”(那些流行的晦澀“理論”也可謂當(dāng)今學(xué)界的一種病);有鋒芒,卻并不變態(tài)(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上多少矯情作秀、動(dòng)輒開罵的“變態(tài)腔”!)……思想開放的年代也是話題泡沫膨脹的年代。如何在這樣的年代里切實(shí)做好思想文化的建設(shè)?既要“反對(duì)黨八股”,也應(yīng)遠(yuǎn)離“變態(tài)腔”。在這方面,《粵海風(fēng)》是不錯(cuò)的。
十年來,我在《粵海風(fēng)》上發(fā)表了幾篇文章,既有《重新認(rèn)識(shí)毛澤東》那樣的思想史論,也有《當(dāng)代文學(xué)中人道主義的命運(yùn)》這樣的文論,還有《為民族主義一辯》這樣的時(shí)論,以及一組關(guān)于“文革”的個(gè)人瑣憶。其中,《為民族主義一辯》曾經(jīng)入選古耜先生主編的《2012年中國(guó)思想隨筆排行榜》一書。感謝《粵海風(fēng)》素未謀面的編輯,為我打開了瞭望思想風(fēng)景的一扇扇新窗。愿它越辦越好,在當(dāng)代思想文化的園地里茁壯成長(zh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