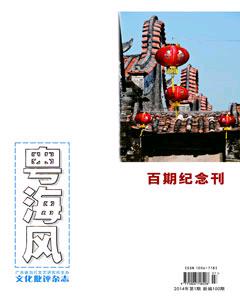八年緣分
吳立昌
我是個老人,但同創刊百期的《粵海風》只有八年緣分,是個新朋友。
初識《粵海風》于2005年夏,因為第四期《延安文人的真誠與說謊》的作者袁盛勇是我的學生,這是他博士論文里的一個章節;2004年畢業后已在某大學任教。文章發表后寄我一本,并問我可有文章,他可以推薦。
我看了這期刊物有關其特色的紹介,先讀卷首《商機無限情有限》,主編從無所不在的商機中敏銳覺察到人文精神喪失的種種弊端,指出“心之最深處,當屬商機鞭長莫及的地方”。再看刊物各個欄目內容,新銳活潑容量大,很吸引我,如“專題”欄內兩篇關于抗戰歷史的記述和評析,史料和史觀都給我不少啟發;“現象”欄兩篇對當前文化征候的評析也很及時。總之刊物讓我耳目一新,愛讀。恰好當時我有篇回憶著名文學理論家葉以群的稿子寫好不久,便給了袁盛勇,很快就在第六期刊出。同期有一篇《祭孔的憂思》,不長,但列入封面要目,可見編者之重視;同時也深得我心,因我也在別處發表過一篇《“讀經”之風不可長》。
我2003年退休時工作未了,直到2006年秋送走最后一屆研究生才徹底回家養老,也徹底擺脫中規中矩的教學科研任務,可以自由自在寫點隨筆之類了。不料命運此時卻來捉弄我,2007年罹患喉癌,切除半喉;次年復發,切除全喉,變成喪失語言功能的殘障人。幸而思維閱讀寫作未受絲毫影響,因此2007—2012年間我又陸續投去六篇,且及時刊出,平均每年一文。我印象最深的是寫《“德”“賽”先生下樓難》,這是我的系列隨筆之一。過去因教學需要翻閱不少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報刊,聯系現實,偶有所感,業余便寫了一些短文,總題為“舊刊今識”,曾刊于《瞭望》、《隨筆》、《文匯讀書周報》等。退休后時間充裕,就想繼續此事。首先重讀《新青年》,寫完一萬二千余字的讀后感,手稿當時還有個副標題“而今又讀《新青年》”。該文發表于2008年第二期,收到刊物已是四月,立即在文末附志幾句:“自1950年代中給報刊撰文至今,本文寫得最痛快,自我感覺甚好。2007年7月上篇寫訖,突罹喉癌,直至2007年12月才完成下篇,2008年2月改定全篇,雖費時半年有余,但頗有意義。” 當時心情很好,不僅因為文章投去立即刊出,有遇到知音之感,而且自以為該文以《新青年》及陳獨秀的主張為貫穿線,聯系九十多年來的社會現實,描述了“德”“賽”先生屢遭挫折的歷史畫面,歷朝執政者對它們不是三心二意,就是陽奉陰違,甚至背道而馳,真正“下樓”看來還要待以時日。看到刊出的文章時,我半喉切除術后恢復也很順利,所以好心情又多了幾分。然而心情沒好幾天,緊接著五月全喉切除,八月又是痛苦萬分的放療。但命運的捉弄并未嚇倒我。經過一年多的休養,2010年開始,我讀《晨報副刊》的三篇“舊刊今識”又陸續在刊物上露面了。所以《粵海風》與我不僅有文字因緣,而且它給病痛中的我以精神上的有力支持和鼓舞。
自退休生病以來,我同原來的專業漸行漸遠,關注點已轉移到現實社會,不免涉及敏感問題,知道只有一向開放的南方才有拙稿容身之處,而姿態開放、博采眾長、文史兼備、風格多樣的《粵海風》便是我的首選。
但愿我們的緣分一個八年、又一個八年地直到我看不了書、動不了筆的那一天;
祈望《粵海風》一個百期、又一個百期地一直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