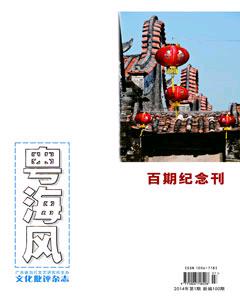關(guān)鍵詞:“自信力”
羅飛
《粵海風(fēng)》自1979年改版以來,出滿百期實(shí)在不易。
我這“實(shí)在不易”四字并非諛詞,是從我經(jīng)歷的編刊艱辛中得出來的判斷。幾十年來,我共編過四個(gè)期刊。其中同人刊物二,新中國成立前后各一,新中國成立后遵命編刊二個(gè),人和刊物均命途多舛:要么批判后被迫停刊,要么識(shí)相點(diǎn)主動(dòng)謝幕。說起出刊期數(shù)那更是汗顏:最少的只出過兩期,最多的也只出到十二期。以我之狹窄眼光視今之《粵海風(fēng)》,實(shí)在寒磣之至。當(dāng)今期刊品種繁富,就質(zhì)量而言,參差不齊,而重量輕質(zhì)似成風(fēng)氣,就我有限的閱讀范圍來說,在眾多文化批評類期刊中《粵海風(fēng)》堪稱佼佼者。記得王元化讀到我在《粵海風(fēng)》發(fā)表為阿垅辯誣文章后,有每期讀到該刊之想,我將此意向徐南鐵主編轉(zhuǎn)達(dá)后,欣喜得到一份贈(zèng)刊。元化常和我談?wù)摗痘浐oL(fēng)》刊物內(nèi)容,頗想為它寄點(diǎn)稿子,但一直為眼疾困擾,終未能如愿,我倆均引為憾事。
我看當(dāng)今期刊重量輕質(zhì)現(xiàn)象之所以形成氣候,原因多多。其表象如賣版面、稿稿交換及采用關(guān)系稿等,形成文化層面的“格雷欣(Thomas Gresham)法則”——劣幣驅(qū)逐良幣,影響于社會(huì)的是人文精神日趨失落。要在文化層面上提高人,使人有理想、有抱負(fù)、有道德,何其難哉!
《粵海風(fēng)》從本身補(bǔ)鈣做起,乃治本之道。記得徐南鐵主編在2005年發(fā)表在《光明日報(bào)》上的《編雜志者當(dāng)有自信力》一文中說:
我想,保留幾種游離于圈子的雜志,保留一些于評職稱和升遷無益,但卻是嚴(yán)肅思考、認(rèn)真操辦的雜志,或許是維護(hù)學(xué)術(s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需要吧!我絕對不敢說自己辦的雜志就屬于這種需要,但是我衷心祝愿它的存在不至于毫無意義。
他提出的“自信力”話題,這使我想起在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魯迅先生就曾寫過一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文章。那時(shí)的中國是外患頻仍,統(tǒng)治者對內(nèi)使用瞞和騙的手段愚弄人民,魯迅先生發(fā)現(xiàn)“中國人現(xiàn)在是在發(fā)展著‘自欺力”。但他清醒地告訴人們:“‘自欺并非現(xiàn)在的新東西,現(xiàn)在只不過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罷了。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下面緊接著是一段至今人們都經(jīng)常引用的名言: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魯迅近八十年前的話,當(dāng)今依然在耳邊回響。當(dāng)我們提到“自信力”,重溫魯迅對中國人的“自信力”的高度評價(jià),難道不會(huì)頓覺脊梁挺直了嗎?
以文化批評為己任,立意“維持學(xué)術(s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粵海風(fēng)》同仁豪邁地說:“生為期刊,命中注定要亮出脊背讓‘發(fā)行量的鞭子抽打,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個(gè)短暫的片斷,我們需要的是歷史的總和。”——這沒有點(diǎn)“自信力”能行嗎?《粵海風(fēng)》同仁明知“中國期刊市場,或者說中國人的閱讀習(xí)慣都還不利于形成某種品位雜志的溫床。在那些發(fā)行商的視野之外,我們有一份失落,幾份悲壯,卻又悄然夾雜著一絲特立獨(dú)行的自得之情。”——這不禁使我對具有“自信力”的中國人肅然起敬。
仍用魯迅先生的話說: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xiàn)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后繼的戰(zhàn)斗,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于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錄此近八十年前的陳言舊語,以贈(zèng)今人,或有不倫不類之譏,但我無非以此祝愿《粵海風(fēng)》諸君,以其堅(jiān)實(shí)的足跡來證實(shí)自己的刊物,將是一份具有清醒的歷史意識(shí)和獨(dú)具學(xué)術(shù)個(gè)性的期刊,增強(qiáng)我們這個(gè)民族更多人的“自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