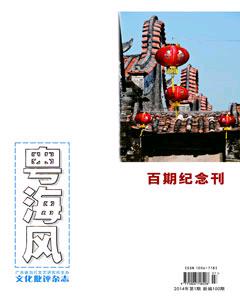學術是一種擔當
殷國明
轉眼《粵海風》創刊至今已經100期了,如果不是主編徐南鐵致函提醒,恐怕思緒仍夾雜在歲月和世事的推搡之間,難得脫離擁擠的時空,在空曠之處透一口氣,盡量在遠處遙望一下自己,還有學界的新朋舊友到底身處何處。
其實,論一個文化批評雜志,100期確實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成果。實際上,作為從一開始就是《粵海風》忠實擁戴者,從若干年起就開始擔心,其是否還能持續下去,所以每次收到刊物,都會有一種慶幸之情,并且趕緊閱讀徐南鐵先生的卷首之語,有時候難免感嘆一聲:“不容易啊!”——如此的擔心也算是一種歷史的遺留,因為至少在廣東,風風雨雨幾十年,亦有若干我喜歡的報刊,例如《現代人報》、《沿海大文化報》等,都先后不無遺憾地退出了文化界,一些朋友也如游云般散去了。在此,我也很想表達對他們的懷念。
當然,在一個變革的大時代,報刊乃至文化思想變化的潮起潮落,乃是一種家常便飯,無須常掛于心,只是源自于個人青春年華的逝去和回憶,才顯得珍貴和哀傷。不過,這種擔憂還源自于對于文化思想界和文化人本身狀況的變化。其實,《粵海風》一開始就把自己定位為“文化批評雜志”,給自己戴上了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枷鎖”——所謂“枷鎖”,就等于自動擔負了一種文化的責任和使命,為自己設置了一種難以為之、又不得不為之的歷史敢當。
因為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且早就有“文化治國”的理念和傳統,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和經國之大業,歷代歷朝都不敢掉以輕心,所以,中國歷史的任何變動,都首先觸動的是中國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都取決于對于文化及其既定傳統的反省、反思、評判和創新。文化對于既定社會的歷史、政治、體制及其意識形態的構建功能和意義,或許西方學界直至20世紀才有所醒悟,而在中國早已經成為一種常識。在這之前,西方所關注的是政治、經濟和制度等有形的、浮于社會表面的、可以付之于實踐操作層面的存在與意識,忽視了滲透于日常生活、家族制度乃至人際關系中的潛在的歷史經緯。它們是軟性的,幾近于無形的、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道”,像水一般無處不在,無處不有,決定著船載船覆,世間冷暖。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任何上層建筑、甚至制度和機制的變革,若沒有深層次的文化意識的變革和創新,都是浮云,都不過是皇帝的新衣,或者大王城頭變換的旗幟。
正因為如此,中國20世紀的大變革起始于對于文化的反思與批判,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開局,無疑具有一種象征和隱喻的意義。在一個視文化為命根子的語境中,魯迅第一次喊出了“文化吃人”的叛逆之音,在一個擁有“文化崇拜教”的傳統國度啟動一次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從未有過的整體性的、深層次的反思和批判思潮,由此使古老的中國在一次近乎歇斯底里的文化洗禮中,跌跌碰碰闖入了世界大潮之中。顯然,幾代中國人都被卷入了這場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大潮之中,在魯迅的感召下,投入了難以窮盡的文化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煎熬中,在國家的新生和自我的脫胎換骨之間苦苦追求。
這當然是一把雙刃劍。結果是突變,是災難,是摧毀,是悲劇,也是跨越,是發展,是重建,是喜劇。歷史原本就沒有完滿和純正。而經過百年的磨礪和驚變,歷史的鐘擺似乎再一次回到了特定的文化刻度上。中國在重新走向興盛之際,再一次遭遇了文化的挑戰和抉擇——而文化批評及其學術研究也正是在這時開始再次引起國人矚目。
而這一次對于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比以往不僅更加深層,而且更加廣闊;不僅面臨更復雜多變的世界風云,而且承擔著更難以預料的歷史風險。
無疑,魯迅當然是有所偏執的。因為文化并不僅僅會“吃人”,而且會“養人”,能滋潤人。偏于一端,執于一詞,必然會導致全面否定和摧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文化是萬能的,是金科玉律,是神圣不可批判的,人類必須遵循、固守和維護的。因為文化是人的創造物,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根據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設置和選擇的。數千年來,人類文化創造了無數的精神奇跡和珠寶,也造就了無數的人為地的歷史災難,包括如希特勒法西斯那樣的戰爭惡魔。設想一下,如果沒有一種強有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沒有一種迷人的、精密的文化構建,區區一介希特勒何以能夠使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投入血腥征戰和屠殺?而德國又是一個富有多么深厚文化涵養的國度啊!
而更為令人難以接受和引長思之的是,這些人類災難和戰爭的肇事者或根由,都源自于一些社會狀態最“先進”、文化最前端、科技最發達、堪稱當時世界各國爭相效仿的國度和民族。
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西方20世紀中葉興起的文化研究和批評思潮,就是從對于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開始的。這種反思實際上為文化人,尤其是被視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學者,提出了新的挑戰,設置了一種新的歷史責任和社會擔當,這就是無時無刻不在注視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構建和發展,警惕人們,尤其是權力集團,利用人性的弱點和盲點,借助于先進的無處不至、無孔不入的現代媒體網絡,構建精心設計的精致的思想意識形態網絡和知識譜系,用文化、思想和知識的方式“殺人”和“害人”。
這是人類的一次新的文化自覺和覺醒。這次自覺與覺醒是空前的,與數千年之前的傳統思想體系文化構建的對應物、方法及其價值追求有很大不同。可以說,無論是西方的希臘哲學,還是中國的儒家學說,傳統文化構建的對應物都是自然,由此產生了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和對峙,人類以文化的方式從原始和自然狀態中解脫出來,構建了充實、穩定和溫馨的精神家園,確立了人在自然中的榮貴和主宰地位,并保證了人類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路途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確立了崇尚文化、知識和奮發有為的主題價值觀。但是,隨著人類的強大與人口劇增,人類所面臨的挑戰和困境,不再來自于自然,而來自于自身內部的競爭和爭奪;而文化的構建也逐步轉向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爭斗、控制和征服。如今,人類是文化已經進入了如此的惡性循環中,每個人都在“與人奮斗”,都在人與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的相互爭斗、算計、甚至浴血奮戰中新生或者死亡。
我不想無視、也不想夸大這種文化的危機或悲劇狀態,而只是想探尋這種狀態形成的思想和歷史根由。正是在這種探尋中,迎來了文化思考和研究的轉向和轉折。這就是文化需要一次真正的回歸,回到對于人自身存在與文化狀態的檢索、反思和批判。因為不僅文化的主體是人,而且是人創造的;文化狀態不僅取決于人類的人性、知識和智慧狀態,而且與不同狀態、階層、圈層和地域的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文化最本質的價值和表現就是人,就是人的全部。
所以,文化研究與批評最根本的切入點就是人。尤其在現代中國,決定社會文化狀態、繼而進一步深刻影響中國社會變遷的并不是某種思想、思潮和理念,而是中國文化人自身的精神狀態。記得梁啟超在上世紀初就指出,在新時代,學術狀態將左右世界的走向和發展,實在具有先見之明,因為如今的世界再也不是那個自行和自然變化的社會了,其每一步、甚至每一個環節都是先有文化人和知識者發揮創意、精心策劃、小心實驗、細心評估、然后才付諸實踐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文化人與知識者以什么樣的心態和身份參與其中,用什么樣的價值觀來想象、策劃、評估和實踐,實際上直接影響著社會的文化狀態和發展進程。實際上,在一個具有悠久文化歷史傳統的國度,如果文化人和知識者陷入腐敗狀態,利用文化和知識的身份優勢謀求私利,追慕權勢,喪失了公共知識文人的基本情懷,社會的進步和繁榮還能夠持續和穩定發展。
這也是中國學術界和批評界自近代以來所面臨的真正挑戰和擔當,即人的挑戰和擔當,而其底線就是對于中國文化人和知識者自身狀態和素質的磨礪、檢驗和創新鑄造。因為是他們首先沖破了禁忌,開拓了空間,解放了思想,創造了奇跡,他們曾經風險最大,受苦最多,磨難最大;同樣也是他們,屈從于強暴,制造了謊言,美化了惡性,喪盡了天良,曾享盡富貴,高朋滿座,得意忘形。
而就在此時,在世界風云變化之時,在文化大潮轉化之際,我在自己窄小的住宅里翻開了遠道而來的《粵海風》,猶如一道文化彩虹在雨后升起,引領我走向廣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