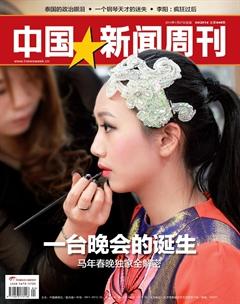阿扎冰川的誘惑
何理

搭了兩次車,才抵達德姆拉山口。這是進西藏察隅縣要翻越的山口。
施工的機器轟鳴著吐出瀝青,不久察隅縣也將通柏油路了。聽筑路工人講,夜里山口常有狼群活動,我們不由得緊張起來,加快了腳步。得在天黑前翻過山口,尋到住處,還得沿路采集植物標本。
幸運的是,很快遇到一個開拖拉機收購奶渣的生意人,愿意載我們去一個牧場,住進他相熟的牧民家。
等他扛走一大袋奶渣、開著拖拉機遠去時,我們才驚覺這位牧民房東不怎么會漢語,也不知生意人是否付過了奶渣錢,心中頓生被販賣的感覺。
輾轉多次,終于抵達了察隅縣上察隅鎮阿扎村。我們找到村委會,在村干部的幫助下,尋得一位靠譜的年輕向導,名叫次仁索朗。
次仁索朗告訴我們,穿越冰川至少需要兩天,且途中并無高山牧場,得自備糧食、炊具和被子等。商量后決定,我們去村民家里買些臘肉,其他必需品由他準備。
村子里異常寧靜,家家的門都掩著,只有一戶人家的屋頂冒著青煙。我們立在籬笆外面喊,一位年輕婦女推門出來,招呼我們上木樓去。
一進屋,撲面而來一陣暖流。屋中央火塘正旺,一位大叔侍弄著火塘,大媽正剝烤玉米吃,見我們進來,熱情地讓座。
溫暖的火塘、滾熱的酥油茶和甜香的烤玉米,很快讓我們數日來的奔波勞累一掃而光。大叔講起他年輕時的狩獵生活,很讓我們著迷。那時,在屋后就可以獵獲飛來的山雞。
不過對于我們買臘肉的請求,大叔略顯猶豫,我們申明只需要兩斤左右,供三個人兩天果腹即可,大叔才松了口,將臘肉用玉米苞葉裹好遞給我們。我們付了錢別過,心里卻有些不安,不知道是不是禁獵后,村民們缺少肉食。
次日一早,在索朗家匯合。索朗的大哥在幫他打包,把藏刀、被子、炊具、大米和蔬菜等塞進一個大竹背簍,又給我們一人倒了一碗自釀的青稞酒。酒看著渾濁,入口卻清爽。大哥又裝了一壺,讓我們帶著路上喝。
出發前,參觀了一下索朗家的木碗制作室。屋里堆著一大堆制作木碗的毛胚——大多是槭樹的樹瘤,還有大串的野生天麻。這些木碗和天麻都會背出山,去八宿縣賣。索朗的父親上山去找這些材料了,一去就要好幾天才能回來。
穿行在森林里,一路上索朗給我們介紹碰到的藥草。西藏八角蓮的根莖可以賣錢,產量也高,但遠不如天麻和木碗值錢。
出了森林,到了河灘上,前面不遠處就是阿扎冰川的冰舌末端。冰川右側原本有山路,但因數次滑坡已不能再走,只能沿著冰舌而上。
冰舌末端的海拔只有兩千多米,受夏日的溫度影響,表層已融化,混合著兩側滑落下來的泥沙,流動起來就是小型的泥石流。看著遠近流動的一股股泥石流,聽著兩岸轟隆不斷的滑坡聲,踩進泥水中,心中說不出的恐懼,看著背著大背簍走在前面的索朗,才略微心安。
聽說前不久,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的一位攝影師從然烏鎮來古村翻山,穿越冰川到了阿扎村,一個人,背著兩臺昂貴的相機,其中一臺在途中滑落。走在這冰川上,我實在不明白,這里有什么誘惑力值得他這樣。
從冰川上穿過滑坡段,腳落在實實的山路上時,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休息時,清理了下已經完全被泥漿糊住的鞋子,喝了一大碗冰冷的青稞酒。
順著山路一路攀升,路好走了很多,但也驚險不已。有一處崖壁,落腳處是松軟的泥,揪著巖壁上的草叢一步步挪過去,一腳寬的泥路因體重下陷,每一步都驚心。
翻過一座山頭后,下到了山坳處。這里長滿了低矮的柳樹,其中有成片的察隅矮柳。尋找它,正是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與察隅矮柳生長在一起的,是一種高10余厘米的柳樹,以前從未見過。
經過野外居群觀察以及回校之后的研究,確認這是一種未被描述的新種,根據其特點和習性,命名為長柄匐柳。我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標本館查看標本時,發現了混在其他柳樹標本中的長柄匐柳標本。其說明上寫著:“產地:阿扎至然烏鎮的途中;時間:1973年;采集人:青藏隊。”想到我們和植物學界前輩相隔著40年,在同一地點,對同一物種進行了采集,不由得有神交之感。
索朗給我們一人砍了一棵竹子做拐杖,靠著它,一步步撐到了當天的目的地。
意想不到的是,在冷杉樹之間,有用厚塑料布斜拉起的三五個只有頂沒有四壁的簡易棚子。我們才意識到,這條路是阿扎村民出入的要道。
其中有一個棚子,位于巖窩處。大巖壁向內傾斜,塑料布從壁頂斜拉,系在旁邊的兩棵云杉上,接著地。這樣就不是四壁通風,成了兩頭貫風,這是值得慶幸的,不用直接裹被子睡在樹下了。
我們砍了些冷杉的枝條,粗的做柴火,細的平鋪在地上做床墊。用臘肉和蔬菜熬了一鍋熱湯,就著帶著糊香的米飯,狠狠吃了一頓。還把竹杖削成簽,串上臘肉,做了烤串。
吃飽喝足后,靠著火堆和衣而睡。下方的冰川轟鳴著,月光灑在上面,白里泛著藍。高大的云杉,只剩下傘形的輪廓。
醒來時,索朗已在撥弄著火。遠方的天空泛著灰藍,云霧層層彌漫在冰川上。
早餐后,繼續前行。背簍、被子和餐具等用品就留在了巖窩里,等索朗返回時再取走。雪山漸漸發亮,直到白得刺眼。
翻過扎滿經幡的山脊,阿扎冰川一覽無余,這時才發現,它由左右兩條大冰舌組成,周圍雪山環繞,冷峻而壯美。至此才明白,那個攝影師以及前赴后繼的人們,是為什么而來。
前一日走的是左側冰川的舌端,這一天要走的是右側冰川的舌根。舌根連著埡口,覆著一層深及腳踝的雪。冰上有裂縫,覆雪后難以辨識,只得走一步探一步。好在竹杖夠長,被削成烤肉簽子后正好用來探路。
雪滲進鞋里,刺骨的冰冷。腳失去了知覺,需要時常停下來,站在漂礫上,把腳掏出來搓。眼鏡也擋不住雪,眼睛疼痛得難以睜開,只能靠仰頭、眨眼來緩解。
不知在雪地里走了多久。埡口似乎就在眼前,卻始終走不到頭。一只黑色的甲蟲在雪里爬過,我們精神為之一振,也不知哪來的力氣,竟在雪地里跑了起來,一氣翻過了埡口,到了山的另一側。
下行不久,就遠遠看到了谷地里的牧場。牧民正在打包最后一頂黑氈帳篷。這里是夏牧場,秋寒來臨,得遷徙了。
帳篷基地上還有一個火塘,酥油茶溫在火旁。這一壺酥油茶,成了我們最后一段行程的能量來源。牧民拿出余下的食物,分給我們。
匆匆道謝告別,朝來古村而行。遠處,馱著行囊的牦牛隊緩緩地移動著,幾處牧場都在轉移。一只肥大的旱獺懶懶地待在洞口,瞅了我們一眼,就扭頭繼續發呆。在它的洞旁,環紋矮柳的果序已飄出白色的絮。
抵達來古村時,天已黑盡,索朗從朋友處借來摩托車,將我們送往然烏鎮。冰冷的雨,隨著陣陣朔風,將我們三人凍得通透。
深夜抵達,從摩托車上翻滾下來,手腳都已僵直。索朗卻要原路返回,還要與父親一起,把木碗和天麻背出山去八宿縣。目送他單薄的身影遠去,心里五味陳雜。
與往日一樣,鎮上匯聚著迷戀318國道的驢友,騎車的、徒步的、自駕的,各自圍著熱騰騰的大燴鍋,暢談旅途艱辛。酒杯碰在一起,發出清脆的聲音。

小貼士
1.去阿扎冰川要經過上察隅鎮、下察隅鎮,均屬邊境鎮,需辦理邊防證。
2.穿越途中無民宿、無牧場,要做好相應的御寒、扎營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