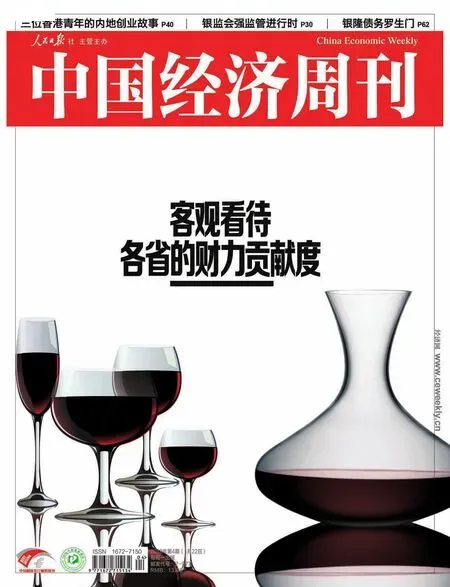李肇星:“外交不只是干杯”
劉硯青

“特別反感把縣以上干部稱為父母官”
“假如您能年輕20歲,組織上派您去做駐外大使,您希望去哪個(gè)國(guó)家?”
“如果你是一個(gè)外國(guó)記者,我會(huì)直接告訴你我不回答假設(shè)性問題。雖然我很希望你的假設(shè)是真的,但我是一個(gè)無(wú)神論者,不可能再年輕20歲。我倒是很希望你將來能夠在祖國(guó)面前說出一些我想說又不敢說的真話。”
1月19日,在中國(guó)人民外交學(xué)會(huì)名譽(yù)會(huì)長(zhǎng)李肇星首部外事回憶錄——《說不盡的外交》讀者交流會(huì)上,這位新中國(guó)第九任外交部部長(zhǎng)回答《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周刊》記者提問時(shí)表示:“如果能夠走出去的話,我覺得一個(gè)人應(yīng)該去國(guó)家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做中國(guó)代表,即使不是大使,也要為祖國(guó)做出自己特有的貢獻(xiàn)。”
想當(dāng)記者,卻搞了外交
談起自己的職業(yè)生涯,李肇星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我是糊里糊涂走上外交這條路的。”
“我小時(shí)候是個(gè)不愛說話的孩子,用山東老家話說就是‘不叫人’,嘴不甜。”在《說不盡的外交》一書中,李肇星回憶起中學(xué)時(shí)光,“有兩位老師都說過我講話不夠流暢,甚至說話好像還點(diǎn)兒大舌頭。”
自稱“一開口別人就會(huì)知道我絕對(duì)是個(gè)鄉(xiāng)下人”的李肇星,從沒想過自己會(huì)成為一名外交官。“1950年,在我上小學(xué)二年級(jí)的時(shí)候,有一輛大卡車從我們村經(jīng)過,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汽車,從此就萌發(fā)了要當(dāng)一名汽車司機(jī)的夢(mèng)想。”李肇星說,上中學(xué)以后,由于經(jīng)常看報(bào)紙,他的夢(mèng)想就變成了當(dāng)記者。“我不但當(dāng)過班里黑板報(bào)的副主編,還給《中國(guó)少年報(bào)》、《上海少年文藝》投過稿。”
“我高中畢業(yè)時(shí)六個(gè)志愿全都填的是北大。當(dāng)時(shí)第一志愿選的是中文系,因?yàn)槲矣X得考上了中文系就一定能當(dāng)記者。”最終,李肇星被第二志愿西方語(yǔ)言文學(xué)系錄取,他之所以報(bào)考這個(gè)專業(yè),也是因?yàn)椤皩W(xué)外語(yǔ)大概也是可以做記者的”。
“連做夢(mèng)都沒夢(mèng)見過會(huì)從事外交工作”的李肇星感慨地說:“我的成長(zhǎng)過程真的與祖國(guó)的命運(yùn)分不開。”
1964年1月,中法兩國(guó)建立大使級(jí)外交關(guān)系。周總理認(rèn)為,這一轟動(dòng)國(guó)際的外交事件預(yù)示著新中國(guó)在聯(lián)合國(guó)的合法席位或?qū)⒃诮陜?nèi)得到恢復(fù),于是他指示外交部抓緊培養(yǎng)一批至少會(huì)運(yùn)用三種聯(lián)合國(guó)工作語(yǔ)言的年輕干部。于是,這一年大學(xué)畢業(yè)的李肇星被選中進(jìn)入外交部翻譯班進(jìn)修。
“我就這樣糊里糊涂地走上了外交道路,今年已經(jīng)是第50個(gè)年頭了。我記得在北大讀書時(shí),鄰校清華有這樣一個(gè)口號(hào):‘大學(xué)畢業(yè)后要健康地為祖國(guó)勞動(dòng)50年。’如今,再過6個(gè)月,我就可以完成了。”李肇星說。
北大教會(huì)李肇星的事
年過古稀的李肇星毫不掩飾自己對(duì)母校北京大學(xué)的熱愛。
“學(xué)校本打算在1960年派我和另外一個(gè)同學(xué)去英國(guó)留學(xué),后來由于國(guó)家遇到了嚴(yán)重的經(jīng)濟(jì)困難,學(xué)校取消了這次公派出國(guó)計(jì)劃。盡管如此,我卻一點(diǎn)兒都沒感到難受,因?yàn)楸贝蠼o我的印象太好了,我舍不得離開。”
李肇星告訴《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周刊》,他的很多第一次都發(fā)生在北大。“第一次見到樓房、第一次用到抽水馬桶、第一次吃到大米、第一次吃到蘋果、第一次見到鋼琴、第一次聽音樂會(huì),這些經(jīng)歷全都發(fā)生在北大。”
“我剛到北大的第一個(gè)星期去學(xué)校小賣部去買練習(xí)本,發(fā)現(xiàn)有一個(gè)老人和學(xué)生站在一起排隊(duì)。我當(dāng)時(shí)向身邊的同學(xué)悄悄打聽他的身份,其他人告訴我這位老人是全國(guó)著名的美學(xué)教授朱光潛先生。盡管后來我再?zèng)]有見過這位老人,但是朱光潛先生卻用自己無(wú)聲的行動(dòng)給我上了來到北大以后的第一課。”
李肇星告訴《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周刊》,20多年前,在他第一次做外交部新聞發(fā)言人時(shí),由于感覺心里沒底,他曾找過季羨林先生請(qǐng)教如何才能做好一個(gè)新聞發(fā)言人。
“季先生當(dāng)時(shí)反問我,你不覺得你問的這個(gè)問題有什么毛病嗎?”季羨林告誡李肇星,不要把當(dāng)官、當(dāng)發(fā)言人這種頭銜看得太重。“季先生對(duì)我說,我不管你是主持人還是發(fā)言人,你只要記著,要做一個(gè)好人就行了!至于說話的時(shí)候要注意什么,一共就兩條:絕不說假話,真話不能全說。沒了!”
“老百姓是我們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說起外交官的工作內(nèi)容和工作性質(zhì),李肇星一臉嚴(yán)肅:“當(dāng)外交官絕對(duì)不是說說洋文、喝喝紅酒,外交官要牢記為祖國(guó)不怕危險(xiǎn),甚至不怕犧牲。”
2005年1月,有8位在伊拉克打工的福建農(nóng)民工被當(dāng)?shù)亍耙了固m抵抗運(yùn)動(dòng)努曼旅”綁架。綁架者要求中國(guó)政府必須在48小時(shí)之內(nèi)澄清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立場(chǎng)和這8名中國(guó)人在伊境內(nèi)工作的目的,否則將處死他們。
時(shí)任外交部部長(zhǎng)的李肇星,需要派一位能力強(qiáng)、不怕死、阿拉伯語(yǔ)好的同志趕赴前線當(dāng)總指揮。“我在開會(huì)前給已經(jīng)退休的前駐伊拉克大使孫必干打了個(gè)電話,還沒等我把話說完,孫必干同志就告訴我:只要祖國(guó)和人民需要,我可以立刻出發(fā)!”李肇星含著熱淚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周刊》回憶說,“掛了電話后,我立刻組織召開緊急黨委會(huì),剛提出要選出一個(gè)緊急營(yíng)救小組的帶隊(duì)人,時(shí)任亞非司司長(zhǎng)翟雋馬上站起來表態(tài):‘這個(gè)問題不用討論,我去!’”
“外交不只是干杯,干杯不過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點(diǎn)談話的機(jī)會(huì)。外交官要始終牢記:我們擁有的一切來自人民,我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為了人民。只要祖國(guó)和人民需要,我們不怕犧牲。”李肇星告訴記者,營(yíng)救小組穿著防彈背心、戴著鋼盔,最終冒著生命危險(xiǎn),在當(dāng)?shù)嘏笥押褪桂^的幫助下,把這8個(gè)福建同胞救了出來。
“我特別反感一些人把縣級(jí)以上的干部稱作父母官。我走了世界183個(gè)國(guó)家深刻地感覺到,這個(gè)世界上最重要人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我們所有人的衣食父母。”李肇星說。
李肇星現(xiàn)場(chǎng)趣談
“我并不覺得外交官的形象和普通人有什么差別。”
“三年前我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寫這些外交故事,是想分享我的信念與理想:我們只有一個(gè)祖國(guó),離開她我們什么也干不成;人民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發(fā)表文章有稿費(fèi),開始投稿想掙點(diǎn)學(xué)費(fèi)和伙食費(fèi)。我第一次拿到10塊錢稿費(fèi)給了母親。她是一名農(nóng)村婦女,沒上過一天學(xué),不知道稿費(fèi)是什么東西,以為我干了壞事,還讓我老實(shí)交代。”
“一次我在聯(lián)合國(guó)大廈里準(zhǔn)備去開會(huì),一位三秘跑過來報(bào)告,說日本一名年輕外交官在會(huì)上胡說八道,稱有的大國(guó)交會(huì)費(fèi)很少,權(quán)力很大,還是常任理事國(guó)。日本交會(huì)費(fèi)多,卻不是。我和這位年輕同事說,這也要先報(bào)告?你要先斗爭(zhēng),趕快跑回去,問他是誰(shuí)讓他胡說八道的。聯(lián)合國(guó)建立在二戰(zhàn)后的廢墟上,是為了反對(duì)戰(zhàn)爭(zhēng)、保衛(wèi)和平建立起來的,有的國(guó)家對(duì)歷史問題還沒正確認(rèn)識(shí)就想‘提拔’自己,不可能。后來這位同事回去質(zhì)問日本外交官,對(duì)方才承認(rèn)無(wú)理。”
李肇星“點(diǎn)拔”本刊記者:
如何“感動(dòng)人”
向李肇星提問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情。因?yàn)樗?jīng)常會(huì)向記者反問一些知識(shí)性問題,而這些問題雖然簡(jiǎn)單,卻很難準(zhǔn)確回答,因此經(jīng)常搞得大家措手不及、手心冒汗。
李肇星說,他有很多記者朋友,也很喜歡記者提出尖銳的問題,因?yàn)榧怃J而有深度的問題本身就是對(duì)發(fā)言人的一種激勵(lì)。
李肇星在《說不盡的外交》中寫道:有時(shí)候,我遇到不便回答的難題,會(huì)友好地問對(duì)方:“您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哪家報(bào)社或電視臺(tái)的?來這里多久了……”這樣就可以為自己爭(zhēng)取一點(diǎn)思考的時(shí)間,回答起來也可能更有針對(duì)性。
雖然沒有如愿以償成為一名記者,但是李肇星這輩子注定了要一直與記者打交道。
在讀書交流會(huì)上,李肇星笑著告訴記者:“由于職業(yè)關(guān)系,我對(duì)記者的提問總是格外警惕。我一看見女記者,就會(huì)想起那位世界著名的女科學(xué)家居里夫人。我很喜歡她說的那句‘科學(xué)沒有國(guó)界,而科學(xué)家是有祖國(guó)的’。今天我把這句話變一變送給你,‘新聞沒有國(guó)界,而新聞工作者是有祖國(guó)的’。”
當(dāng)記者提出希望能夠獲得專訪他的機(jī)會(huì)時(shí),李肇星一邊點(diǎn)頭表示感謝一邊推辭說:“我還是希望你們把更多的關(guān)注放在基層。做記者不要講套話,要帶頭講真話,講一些實(shí)實(shí)在在,老百姓看得懂、也愿意聽的話。”
“咱們都是做交流工作的,也算是同行。我認(rèn)為無(wú)論是做記者也好,做外交官也好,如果你說的話自己都不感動(dòng),你不可能感動(dòng)中國(guó)人,也不可能感動(dòng)外國(guó)人。”說到這里,這位從事外交工作近50年的老部長(zhǎng)雙手合十,對(duì)著記者說了一句“謝謝你”。
當(dāng)有學(xué)生向李肇星詢問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時(shí),李肇星向他推薦了魯迅先生的《藥》。“華老栓夫婦給兒子小栓買來人血饅頭治病,故事聽起來愚蠢我卻至今難忘。不管你是什么職稱或者當(dāng)什么大官,如果脫離群眾,群眾照樣會(huì)把你的鮮血用來蘸饅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