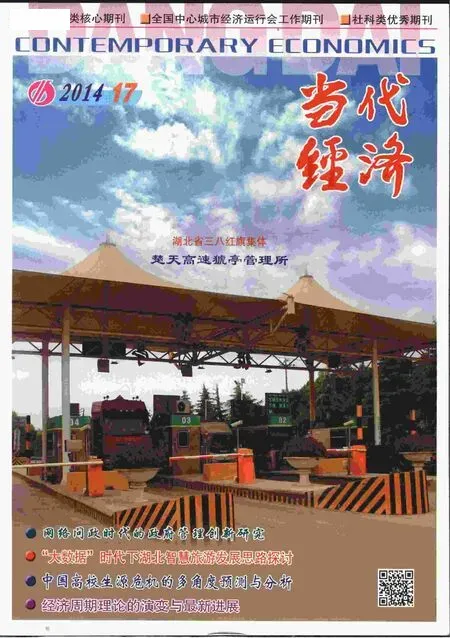M1與M2增速差和PPI的動(dòng)態(tài)相關(guān)性探究——基于Var模型的實(shí)證檢驗(yàn)
○劉藝
(中南財(cái)經(jīng)政法大學(xué)金融學(xué)院 湖北 武漢 430073)
一、引言及文獻(xiàn)綜述
根據(jù)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2014年3月份全國(guó)居民消費(fèi)價(jià)格指數(shù)(CPI)同比上漲2.4%,處于溫和區(qū)間;工業(yè)生產(chǎn)者出廠價(jià)格(PPI)則同比下降2.3%,PPI出現(xiàn)連續(xù)第25個(gè)月的負(fù)增長(zhǎng),由此造成中上游企業(yè)利潤(rùn)大幅下滑,實(shí)際債務(wù)負(fù)擔(dān)加重,加大了金融風(fēng)險(xiǎn)和經(jīng)濟(jì)下行壓力。從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和相關(guān)研究來(lái)看,PPI的走勢(shì)要領(lǐng)先于CPI,對(duì)經(jīng)濟(jì)運(yùn)行具有較好的預(yù)見(jiàn)性(楊燦、陳龍,2013;蕭松華、伍旭,2009)。現(xiàn)階段,對(duì)我國(guó)這樣一個(gè)工業(yè)產(chǎn)值位居全球第一的制造業(yè)大國(guó),從貨幣調(diào)控政策來(lái)說(shuō),不僅要從控通脹的角度盯緊CPI,更應(yīng)從穩(wěn)增長(zhǎng)的角度關(guān)注PPI。
我國(guó)貨幣調(diào)控模式以數(shù)量和價(jià)格為主。當(dāng)前,央行數(shù)量型調(diào)控模式的有效性存在爭(zhēng)議(戴曉兵,2013;王曦、鄒文理,2012);此外,由于利率還未完全市場(chǎng)化,價(jià)格模式尚待完善。研究結(jié)果指出,貨幣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的變化密切相關(guān)(范立夫、張捷,2011),若選取合適的貨幣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探究其與PPI的相關(guān)性,預(yù)測(cè)其運(yùn)行趨勢(shì)和變動(dòng)路徑,既有可行性,也有必要性。
在貨幣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中,貨幣流動(dòng)性比率(M1/M2)多反映的是一種長(zhǎng)期趨勢(shì),時(shí)效性較弱。M1與M2增速差可定義為貨幣活化指標(biāo),因其能很好地反映經(jīng)濟(jì)活躍程度及企業(yè)投資需求變動(dòng)(劉海影,2013)。從2011年下半年以來(lái),M1和M2增速差持續(xù)處于歷史低位水平,反映了實(shí)體經(jīng)濟(jì)放緩,微觀主體投資需求下降,與PPI的走勢(shì)相吻合,且領(lǐng)先PPI的變動(dòng)。因此,本文選取M1與M2增速差作為貨幣結(jié)構(gòu)變化的指標(biāo),來(lái)探究其與PPI的相關(guān)性。
對(duì)于我國(guó)貨幣供應(yīng)量與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的關(guān)系,學(xué)界觀點(diǎn)主要為以下幾種:貨幣非中性,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之間呈正相關(guān)(黃先開(kāi)、鄧述惠,2000;徐強(qiáng),2001);貨幣短期內(nèi)非中性,長(zhǎng)期內(nèi)對(duì)產(chǎn)出不產(chǎn)生影響,對(duì)物價(jià)產(chǎn)生顯著影響(劉斌,2002);貨幣完全中性,被動(dòng)的適應(yīng)經(jīng)濟(jì)波動(dòng)而不是主導(dǎo)的服務(wù)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張立華,2003)。具體看貨幣供應(yīng)量與PPI的關(guān)系:陳鈺(2011)指出M2與PPI不存在G r a n g e r因果關(guān)系,而楊繼生、馮焱(2013)的研究指出,貨幣供給沖擊對(duì)重工業(yè)以及產(chǎn)業(yè)鏈上游行業(yè)PPI波動(dòng)的貢獻(xiàn)度達(dá)74%。由此可見(jiàn),貨幣供應(yīng)量對(duì)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的效應(yīng)存在較大爭(zhēng)議。而關(guān)于貨幣結(jié)構(gòu)對(duì)經(jīng)濟(jì)的影響,學(xué)者的觀點(diǎn)較為一致,認(rèn)為貨幣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對(duì)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央行的貨幣政策應(yīng)引導(dǎo)貨幣結(jié)構(gòu)合理化,代表學(xué)者有肖衛(wèi)國(guó)、劉杰、趙圣偉(2013)。就本文要展開(kāi)研究的貨幣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M1與M2增速差來(lái)說(shuō),已有文獻(xiàn)指出其與CPI存在顯著相關(guān)關(guān)系(范立夫、張捷,2011),但更多學(xué)者關(guān)注的是其對(duì)股票指數(shù)的影響,鮮有文獻(xiàn)研究M1與M2增速差和PPI的動(dòng)態(tài)相關(guān)關(guān)系,本文試圖對(duì)這一領(lǐng)域作出貢獻(xiàn)。
二、理論分析
根據(jù)央行的統(tǒng)計(jì)口徑,狹義貨幣M1=流通中現(xiàn)金+單位活期存款;廣義貨幣M2=M1+居民儲(chǔ)蓄存款+單位定期存款+單位其他存款+證券公司客戶(hù)保證金+住房公積金中心存款+非存款類(lèi)金融機(jī)構(gòu)存款。M1與M2增速差,衡量了存款的活期化傾向,反映了微觀層面企業(yè)的經(jīng)營(yíng)活力和投資意愿。當(dāng)經(jīng)濟(jì)放緩時(shí),企業(yè)投資更加謹(jǐn)慎,定期存款比例上升,對(duì)中長(zhǎng)期貸款的需求相應(yīng)下降,從而造成M1與M2增速差處于低位,反之同理。另外,2001年以來(lái),企業(yè)儲(chǔ)蓄出現(xiàn)快速增長(zhǎng)并在國(guó)民儲(chǔ)蓄中的占比不斷上升(江靜,2013),也增強(qiáng)了M1與M2增速差對(duì)企業(yè)投資需求變動(dòng)的敏感性。PPI是工業(yè)品出廠價(jià)格指數(shù),體現(xiàn)了工業(yè)企業(yè)的定價(jià)能力,顯然受到投資需求的影響。投資需求變動(dòng)把M1與M2增速差和PPI聯(lián)系起來(lái),使得兩者存在高度相關(guān)性成為必然。
從2005年至今的M1,M2,M1與M2增速差和PPI的走勢(shì)圖(見(jiàn)圖1)來(lái)看,M1與M2增速差和PPI的波動(dòng)幅度與走勢(shì)最為吻合,呈高度正相關(guān),且PPI有滯后性。
通過(guò)圖1的分析,結(jié)合當(dāng)時(shí)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的實(shí)際運(yùn)行情況,可以看出,2005年至今,我國(guó)經(jīng)歷了兩個(gè)完整的經(jīng)濟(jì)周期。在這兩個(gè)周期中,M1與M2增速差都及時(shí)體現(xiàn)出了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的周期變化、貨幣政策的調(diào)整、企業(yè)投資需求的波動(dòng)。在每一周期的開(kāi)始階段(2005年和2008年的上半年),都出現(xiàn)了工業(yè)增長(zhǎng)趨緩,企業(yè)效益下滑,經(jīng)濟(jì)呈現(xiàn)下行趨勢(shì)。為了穩(wěn)增長(zhǎng),政府實(shí)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信貸和投資開(kāi)始反彈,M1與M2增速差顯著上升。而此時(shí)企業(yè)還處在去庫(kù)存階段,PPI變動(dòng)不明顯。由于投資持續(xù)增長(zhǎng),部分產(chǎn)品出現(xiàn)供應(yīng)緊張,提價(jià)出現(xiàn)可傳導(dǎo)性,PPI開(kāi)始上揚(yáng)。PPI上行,經(jīng)濟(jì)加速?gòu)?fù)蘇,投資繼續(xù)增長(zhǎng);PPI和投資水平的持續(xù)上升帶動(dòng)通脹壓力上升。貨幣政策開(kāi)始收緊,M1、M2增速回落;隨著新建產(chǎn)能的逐步釋放,在產(chǎn)能過(guò)剩加大、集中度低和同質(zhì)化競(jìng)爭(zhēng)激烈的行業(yè),庫(kù)存加大,由于信貸政策收緊,資產(chǎn)負(fù)債表開(kāi)始惡化,產(chǎn)品出現(xiàn)降價(jià),并從下游向上游傳導(dǎo),PPI下行。此時(shí),企業(yè)利潤(rùn)下滑,邊際資本回報(bào)率下降,企業(yè)投資需求下降,M1與M2增速差快速下行。同時(shí),固定資產(chǎn)投資往往包含大量的不可逆性投資成本,加上我國(guó)特有的行政干預(yù)和地方保護(hù),進(jìn)一步延長(zhǎng)了PPI的下行時(shí)間。

圖1 M1,M2,M1與M2增速差與PPI變化趨勢(shì)
理論上,需求、供給和預(yù)期是價(jià)格形成機(jī)制的三要素。一方面,固定資產(chǎn)投資是一個(gè)重要的需求因素,另一方面,固定資產(chǎn)投資也影響行業(yè)供給能力。張軍、方紅生(2007)的研究指出,貨幣供給通過(guò)全社會(huì)實(shí)際固定資產(chǎn)投資間接地成為價(jià)格水平變動(dòng)的主因;而M1與M2增速差對(duì)投資需求的變動(dòng)更為敏感,其與價(jià)格水平的相關(guān)性也更強(qiáng)。
M1與M2增速差和PPI的相關(guān)性,也與我國(guó)這一階段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方式和工業(yè)結(jié)構(gòu)變化的背景有關(guān)。從1999年開(kāi)始,我國(guó)的重工業(yè)化開(kāi)始加速,工業(yè)結(jié)構(gòu)中重化工業(yè)化特征較為顯著,1999—2011年間,我國(guó)重化工業(yè)占比由58.1%上升到71.3%。一般來(lái)說(shuō),重工業(yè)增速代表了投資需求的增長(zhǎng),輕工業(yè)增速則相對(duì)代表消費(fèi)需求的增長(zhǎng);重化工業(yè)化特征使得投資水平變動(dòng)對(duì)PPI的影響占主導(dǎo)地位。
再?gòu)腗1與M2增速差與工業(yè)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重工業(yè)與輕工業(yè)增速之差)的走勢(shì)來(lái)看(見(jiàn)圖3),兩者高度相關(guān),計(jì)算Spearman秩相關(guān)系數(shù)達(dá)0.77。這進(jìn)一步佐證M1與M2增速差和PPI之間的高度相關(guān)性和作用途徑。
綜合上述分析,M1與M2增速差和PPI高度相關(guān)。M1與M2增速差對(duì)PPI的影響預(yù)期符號(hào)為正;關(guān)于PPI對(duì)M1與M2增速差的影響方向,缺乏文獻(xiàn)資料支撐。依據(jù)上文對(duì)經(jīng)濟(jì)實(shí)際運(yùn)行情況的解釋?zhuān)琍PI上行在短期內(nèi)將通過(guò)刺激投資引導(dǎo)M1與M2增速差擴(kuò)大,長(zhǎng)期則由于經(jīng)濟(jì)過(guò)熱、供給過(guò)剩,導(dǎo)致M1與M2增速差的逐步回落,因而預(yù)期PPI對(duì)M1與M2增速差的影響為短期正效應(yīng)、長(zhǎng)期負(fù)效應(yīng)。本文在M1與M2增速差和PPI具有高度相關(guān)性的基礎(chǔ)上,欲通過(guò)構(gòu)建VAR模型,實(shí)證探究M1與M2增速差和PPI的動(dòng)態(tài)相互影響,明確兩者間的動(dòng)態(tài)響應(yīng)機(jī)制。

圖2 重工業(yè)與輕工業(yè)產(chǎn)值之比柱形圖

圖3 M1與M2增速差與工業(yè)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走勢(shì)圖
三、樣本及數(shù)據(jù)選擇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是實(shí)體經(jīng)濟(jì)兩個(gè)完整經(jīng)濟(jì)周期的起點(diǎn),本文選取2005年作為樣本的時(shí)間起點(diǎn),研究的視線窗為2005年1月至2014年3月,時(shí)間跨度為9年零3個(gè)月,樣本容量為111期。筆者選用月度數(shù)據(jù)作為樣本,較好地反映M1與M2增速差與PPI指標(biāo)變動(dòng)的連續(xù)性。M1與M2增速差計(jì)算的是M1同比增長(zhǎng)率與M2同比增長(zhǎng)率的差值,下文以符號(hào)DIF表示;PPI指標(biāo)也為同比增長(zhǎng)率數(shù)值,基期為去年同月。兩變量數(shù)據(jù)均來(lái)源于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網(wǎng)站。
四、實(shí)證分析
1、單位根檢驗(yàn)
計(jì)量分析要求數(shù)據(jù)是平穩(wěn)的,不平穩(wěn)則要求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否則易造成偽回歸的問(wèn)題。Johanson協(xié)整檢驗(yàn)的前提是變量滿(mǎn)足同階單整(通常是一階單整),故首先對(duì)變量進(jìn)行單位根檢驗(yàn),確定其是否平穩(wěn)或者滿(mǎn)足一階單整過(guò)程。本文采用ADF檢驗(yàn)法,分別根據(jù)A I C和S C滯后階數(shù)準(zhǔn)則進(jìn)行檢驗(yàn),檢驗(yàn)結(jié)果均顯示兩變量水平值在5%顯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穩(wěn)的,經(jīng)過(guò)一階差分后平穩(wěn),因此兩變量原始水平值服從一階單整,滿(mǎn)足了協(xié)整檢驗(yàn)的必要前提。表1給出了根據(jù)A I C準(zhǔn)則的單位根檢驗(yàn)結(jié)果。

表1 變量單位根檢驗(yàn)結(jié)果
2、協(xié)整—Johanson實(shí)證
(1)確定協(xié)整最佳滯后階數(shù)L。根據(jù)VAR 模型最佳滯后階數(shù)的確定準(zhǔn)則逐一測(cè)試從0 到3 滯后階數(shù)的檢驗(yàn)值,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F(xiàn)PE、AIC 表明最佳滯后階數(shù)為3,LR、SC、HQ 表明最佳滯后階數(shù)為2。一般來(lái)說(shuō),VAR 模型的滯后階數(shù)根據(jù)AIC和SC 準(zhǔn)則共同確定。當(dāng)AIC和SC 準(zhǔn)則結(jié)果一致時(shí),滯后階數(shù)隨之確定;AIC和SC 準(zhǔn)則出現(xiàn)沖突時(shí),則根據(jù)LR 準(zhǔn)則確定最佳滯后階數(shù)。因此,本文確定VAR 模型滯后階數(shù)L=2,相應(yīng)地,協(xié)整最佳滯后階數(shù)L=2。
(2)Johanson協(xié)整檢驗(yàn)。確定最佳滯后階數(shù)L=2之后,接下來(lái)利用Johanson提出的協(xié)整似然比檢驗(yàn)方法判斷兩變量間的協(xié)整關(guān)系。結(jié)合數(shù)據(jù)特征并經(jīng)反復(fù)測(cè)試,協(xié)整檢驗(yàn)假設(shè)選擇含截距項(xiàng)、時(shí)間項(xiàng),不含線性趨勢(shì)。協(xié)整檢驗(yàn)結(jié)果如表3所示。
表3中,r表示協(xié)整關(guān)系的個(gè)數(shù),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跡統(tǒng)計(jì)量表明拒絕變量間沒(méi)有協(xié)整關(guān)系的原假設(shè),接受變量間存在一階協(xié)整關(guān)系的假設(shè);最大特征值統(tǒng)計(jì)量同樣拒絕r=0,接受r≤1,即變量間最多存在一階協(xié)整關(guān)系。所以M1與M2增速差與PPI兩變量間存在一階協(xié)整關(guān)系。
3、Granger因果檢驗(yàn)
VAR模型要求變量間需存在雙向Granger 因果關(guān)系,因此本文在兩變量間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的前提下進(jìn)行Granger 因果檢驗(yàn),滯后階數(shù)L=2,結(jié)果如表4 所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P值表明應(yīng)拒絕原假設(shè)PPI 不是DIF 的Granger 原因,同樣拒絕原假設(shè)DIF 不是PPI 的Granger 原因。所以結(jié)論是PPI與M1與M2 增速差存在雙向Granger 因果關(guān)系。
4、模型構(gòu)建
本文要研究的是M1與M2 增速差與PPI 之間的動(dòng)態(tài)相關(guān)關(guān)系。根據(jù)理論分析,兩變量均為內(nèi)生變量且相互間影響存在滯后性,VAR(Vector Auto Regression model)是理想合適的估計(jì)方法。由于兩變量均存在負(fù)值,故不再取對(duì)數(shù)而直接進(jìn)入實(shí)證方程。因此,本文構(gòu)建的實(shí)證模型為:
DIFt=α0+α1PPIt-1+α2DIFt-1+…+εt
PPIt=α0+α1PPIt-1+α2DIFt-1+…+εt

表2 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滯后階數(shù)

表3 Johanson協(xié)整檢驗(yàn)結(jié)果
5、Var結(jié)果
(1)回歸結(jié)果。在變量間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及Granger因果關(guān)系的前提下,本文采用OLS估計(jì)方法,借助Eviews 7.0估計(jì)VAR模型,結(jié)果見(jiàn)表5。
VAR模型回歸方程如下:

(2)穩(wěn)定性檢驗(yàn)。VAR模型本身需要對(duì)之進(jìn)行穩(wěn)定性檢驗(yàn),從圖4可以看出,全部根的倒數(shù)均在單位圓之內(nèi),模型的穩(wěn)定性條件得到滿(mǎn)足。

圖4 殘差的穩(wěn)定性檢驗(yàn)
L M自相關(guān)檢驗(yàn)得到,L M1=1.78,P值=0.7765;L M2=5.38,P值=0.25,不存在自相關(guān);white異方差檢驗(yàn)(無(wú)交叉項(xiàng))顯示,χ2=49.86,P值=0.06,不存在異方差。通過(guò)診斷得出,VAR模型效果良好。
6、脈沖響應(yīng)分析
VAR模型不以經(jīng)濟(jì)理論為基礎(chǔ),所以對(duì)參數(shù)的含義一般不做解釋?zhuān)渲饕獞?yīng)用在于脈沖響應(yīng)函數(shù)。脈沖響應(yīng)函數(shù)刻畫(huà)的是在誤差項(xiàng)上加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大小的沖擊對(duì)內(nèi)生變量的當(dāng)前值和未來(lái)值所帶來(lái)的影響。以下是基于Monte Carlo模擬、滯后18期的脈沖響應(yīng)曲線。
圖5描述了PPI對(duì)于M1與M2增速差單位新息沖擊的響應(yīng)程度,可以看出,PPI對(duì)M1與M2增速差的反應(yīng)滯后3期,之后表現(xiàn)為正向響應(yīng),且數(shù)值不斷變大,滯后12期即一年之后逐漸減弱。說(shuō)明M1與M2增速差具有領(lǐng)先性,并與PPI高度正相關(guān)。

表4 Granger因果檢驗(yàn)結(jié)果
圖6描述了M1與M2增速差對(duì)于PPI單位新息沖擊的響應(yīng)程度,對(duì)于PPI的沖擊,M1與M2增速差的反應(yīng)呈現(xiàn)出先上升后下降,短期正響應(yīng)、長(zhǎng)期負(fù)響應(yīng)的態(tài)勢(shì),拐點(diǎn)出現(xiàn)在滯后6期的時(shí)間點(diǎn)。這說(shuō)明PPI的上升在短期內(nèi)會(huì)引導(dǎo)M1與M2增速差的擴(kuò)大,長(zhǎng)期則會(huì)導(dǎo)致M1與M2增速差的回落。對(duì)此現(xiàn)象的解釋是:PPI上升,企業(yè)利潤(rùn)回升,經(jīng)濟(jì)景氣度上升,投資需求回暖,M1與M2增速差相應(yīng)擴(kuò)大;M1與M2增速差的擴(kuò)大又進(jìn)一步導(dǎo)致了PPI的上揚(yáng),如此循環(huán)便出現(xiàn)了經(jīng)濟(jì)過(guò)熱、供給過(guò)剩。貨幣政策收緊,企業(yè)擴(kuò)大再生產(chǎn)的需求萎縮,M1與M2增速差在較長(zhǎng)一段時(shí)期內(nèi)逐步回落。這也十分符合我國(guó)這近十年的經(jīng)濟(jì)運(yùn)行軌跡:投資擴(kuò)張帶來(lái)了經(jīng)濟(jì)的增長(zhǎng),但大規(guī)模的重復(fù)投資也造成了如今產(chǎn)能過(guò)剩,企業(yè)利潤(rùn)縮減,債務(wù)高企,投資需求不振,重工業(yè)增速回落的局面。
7、方差分解
在考察VAR模型時(shí),還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動(dòng)態(tài)特征。兩變量的方差結(jié)果見(jiàn)表6、表7。
可以看出,無(wú)論在短期還是長(zhǎng)期,PPI自身是其變動(dòng)的最主要貢獻(xiàn)因素,不過(guò)影響力逐步下降,隨著滯后期數(shù)的增加,M1與M2增速差對(duì)PPI的解釋力逐步增強(qiáng),滯后18期其貢獻(xiàn)度達(dá)到22.57%;PPI對(duì)M1與M2增速差的解釋力度在滯后8期之后顯著增加,且在滯后18期時(shí)達(dá)到了41.18%,說(shuō)明PPI對(duì)M1與M2增速差的長(zhǎng)期影響是十分顯著的。
五、研究結(jié)論及啟示
第一,M1與M2增速差可作為PPI的領(lǐng)先指標(biāo),與PPI高度正相關(guān)。鑒于PPI在現(xiàn)今重工業(yè)增速回落背景下的特殊意義,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biāo)也應(yīng)加大對(duì)M1與M2增速差的關(guān)注。

表5 VAR模型估計(jì)參數(shù)

圖5 PPI對(duì)M1與M2增速差的響應(yīng)

圖6 M1與M2增速差對(duì)PPI的響應(yīng)

表6 PPI方差分解結(jié)果

表7 M1與M2增速差方差分解結(jié)果
第二,PPI的上升在短期內(nèi)會(huì)引導(dǎo)M1與M2增速差的擴(kuò)大,長(zhǎng)期則會(huì)導(dǎo)致M1與M2增速差的回落,大約滯后六個(gè)月出現(xiàn)拐點(diǎn)。
第三,M1與M2增速差和PPI存在動(dòng)態(tài)相互影響,它們的周期變動(dòng)也就形成了企業(yè)層面的通脹與通縮周期;M1與M2增速差可作為周期反轉(zhuǎn)的指示性指標(biāo),其底部反轉(zhuǎn)或頂部反轉(zhuǎn)形態(tài)具有較強(qiáng)的預(yù)示作用。
第四,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形勢(shì)下,PPI持續(xù)低迷,M1與M2增速差短期內(nèi)將延續(xù)弱勢(shì),只有當(dāng)去產(chǎn)能、去杠桿的過(guò)程完成后,M1與M2增速差才可能出現(xiàn)負(fù)響應(yīng),觸底反彈,引導(dǎo)新一輪的經(jīng)濟(jì)周期。從正響應(yīng)反轉(zhuǎn)為負(fù)響應(yīng)的這個(gè)拐點(diǎn)所須的時(shí)間是留給政策可操作的空間。去產(chǎn)能、去杠桿并不意味著摒棄投資,相反,在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形勢(shì)下,應(yīng)十分強(qiáng)調(diào)有效投資:在技術(shù)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升級(jí)、基礎(chǔ)設(shè)施完善、環(huán)境治理、醫(yī)療、養(yǎng)老等方面,還有許多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回報(bào)都很高的投資機(jī)會(huì)。另外,應(yīng)借鑒小島清的邊際產(chǎn)業(yè)擴(kuò)張理論和日本海外投資的經(jīng)驗(yàn),鼓勵(lì)企業(yè)走出去,這也是化解產(chǎn)能過(guò)剩矛盾、調(diào)整優(yōu)化國(guó)內(nèi)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改善企業(yè)效益的一條重要途徑。
[1]Neville R.Norman:ProducerPrice Indexes: Properties,Problems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J].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2008.
[2]Mohd Fahmi Ghazali,Ooi Ai Yee,Mohd Zulkifli Muhammad.Do Producer Prices Cause Consumer Prices?Some Empirical Evide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2009.
[3]蕭松華、伍旭:PPI:當(dāng)前我國(guó)通貨膨脹的先行指標(biāo)——基于PPI引導(dǎo) CPI變動(dòng)的研究[J].暨南學(xué)報(bào),2009,31(4).
[4]楊繼生、馮焱:貨幣供給與PPI的動(dòng)態(tài)響應(yīng)機(jī)制和結(jié)構(gòu)性差異[J].統(tǒng)計(jì)研究,2013,30(8).
[5]范立夫、張捷:貨幣增速剪刀差與CPI相關(guān)性的實(shí)證研究[J].財(cái)經(jīng)問(wèn)題研究,2011(6).
[6]任碧云:改革開(kāi)放后中國(guó)歷次M2和M1增速剪刀差逆向擴(kuò)大現(xiàn)象分析[J].財(cái)貿(mào)經(jīng)濟(jì),2010(1).
[7]陳鈺:PPI、企業(yè)商品價(jià)格指數(shù)、M2與CPI之間關(guān)系研究[J].遼寧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39(3).
[8]楊燦、陳龍:中國(guó)CPI與PPI:因果關(guān)系和傳導(dǎo)機(jī)制[J].廈門(mén)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3).
[9]戴曉兵:我國(guó)貨幣供應(yīng)量中介目標(biāo)有效性的實(shí)證分析[J].財(cái)經(jīng)問(wèn)題研究,2013(4).
[10]王曦、鄒文理:我國(guó)貨幣政策的最優(yōu)度量指標(biāo)[J].中山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52(1).
[11]黃先開(kāi)、鄧述慧:貨幣政策中性與非對(duì)稱(chēng)性的實(shí)證研究[J].管理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00,3(2).
[12]徐強(qiáng):中國(guó)貨幣供給、資本形成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關(guān)系研究——兼論中國(guó)貨幣政策中介變量選擇[J].財(cái)經(jīng)研究,2001,27(8).
[13]劉斌:我國(guó)貨幣供應(yīng)量與產(chǎn)出、物價(jià)間相互關(guān)系的實(shí)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2(7).
[14]張立華:我國(guó)貨幣供給狀況的實(shí)證分析[J].統(tǒng)計(jì)與信息論壇,2003,18(2).
[15]肖衛(wèi)國(guó)、劉杰、趙圣偉:中國(guó)貨幣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基于1952—2010年宏觀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檢驗(yàn)[J].金融研究,2013(2).
[16]江靜:中國(guó)企業(yè)儲(chǔ)蓄率——來(lái)自企業(yè)的微觀證據(jù)[J].經(jīng)濟(jì)理論與經(jīng)濟(jì)管理,2013(10).
[17]張軍、方紅生:投資與通貨膨脹—緊縮的聯(lián)系:來(lái)自中國(guó)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J].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