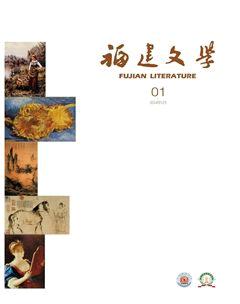找到幸福的入口
黃明生
我時常愛把幸福定格在“小”字上:小家小聚、小錢小米、小樣小足。不是本人胸無大志,心如古井,無浩然之氣,不為所動,也非無能之輩,庸碌之徒,而是年近知天命,青春將逝,更多的只想著順其自然,順風順水,以小為本,以小為樂,以小為安,以小為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樣就算是找到了幸福的入口,人生便有了幸福的開端。
幸福是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溫馨小家,一套不大但好用宜用的小屋。屋內可以擺床鋪、書桌、電腦、電視、飯桌、沙發、板凳、書架,不求奢華,不貪富麗,但求舒適,但圖溫馨。孩子大了,讓其自立門戶,志在四方。自個兩老世界,日出而起,日落而臥,只圖清靜簡單,又可小酌小飲,輕歌小曲,優哉游哉。偶爾還可約些好友來家小聚,小酒小菜,談天說地,放松心情,以利身心。
幸福是掙著一份維持家門安身立命的小錢,不用去拮據度日。無論是急風暴雨抑或是云淡風輕時季,平日里只需付以小力,便可取以薪金,衣食無憂。如曾國藩所言“餉事是平日有流水之數,數月月總匯之帳。”細水長流,平靜而過,像小草長勢,悠然自在,平常人家。偶有應酬,手頭不空,心頭不驚;從長而計,總有小積,如積沙成塔,少憂少慮,幸福相伴。間而約幾位親朋好友到自家或他家搓它幾圈麻將,小打小鬧,管它是輸是贏,過下手癮即可。
幸福是只求輕松漫步走完人生里程,不再奢望出人頭地,只求小樣,只圖小足,少來比較,省得無端憂煩,即如,不和郭晶晶比跳水,自己想舒展一下筋骨就到小溪溝泡泡;不與李詠論口才,自己想抒發胸臆就找幾位文友發發;不跟宋祖英賽歌喉,自己想唱歌玩玩就到歌廳吼吼;不同劉翔講矯健,自己想強身健體就去戶外場地練練;不與余秋雨先生試文采,縱有心靈被觸動之時就把文字寫寫。總之呢,無事時不妨想想當年李鴻章在任中堂時回對梁啟超先生那句意味深長的話:“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當自己所從事的地方稅收事業干到頭該退位了,絕不找煩尋愁,只當走過了一段彎曲的小道,講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心平氣和地回到自己朝夕相伴的溫馨小屋里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讀書、剪報、寫字、哼歌、小酌、談聊。最后可能的話就“慢慢變老,快快死去。”
其實,幸福是一種心態、一種能力,是我們內心的一種需要,一旦把自己的幸福定格在“小”字上,即可在回望往事,目視未來時,安之若素,明善誠身,如坐春風,幸福就會悄然而至,敲門入室,即使是平凡人普通人也不會被遺忘。
柿子樹
我還是孩童的時候,記得距離我家不遠的路邊有一棵柿子樹,這棵柿子樹長得又高又壯,柿子也長得特別多,秋天到來,我們都會成群結伴地前去,要么用石子往上擊打,要么用預備好的竹棍捅,把一個個剛成熟的果子成為我們這些從來不見飽的伙伴們的口中之食。
這已是久遠的事情了。
前幾年我家也種上了一棵柿子樹。每當春天來時,世故的柿子樹才遲遲從睡眠中醒來,睜開淡黃中泛著綠光的眸子,很有興致地打探春華的訊息。當確信無疑地斷定春天果真來到了的時候,便隨性勃抖衣冠,不多時日就爭先恐后地長出手掌般大小的嫩綠的葉子。于是,枝葉之間便挽起了綠色的手臂,使家園充滿了誘人的生機與活力。
初夏來臨,柿子樹毫不示弱地與園地里的桃梨等一起迎接花開的聲音,那黃白色的花兒全然不顧自己是否富麗堂皇,轟轟烈烈,卻泰然自若地在濃密的綠葉掩蓋下悄悄綻放。它散發出淡淡的芳香,站在枝繁葉茂的樹下,似乎用嘴唇可以品出那沁人心脾的味道來。等到花兒凋謝了,看著鋪在地上的黃亮亮的花瓣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的詩句仿佛就會油然而生。它總是默默地長著,不慌不忙地度過了盛夏。火熱,狂風,暴雨,蟲擾,在它看來,似乎有點兒不屑一顧,只有經過世間風風雨雨的錘煉,才會有這般堅毅而又隨遇而安的品性。
當秋風吹來時,樹冠上最敏感的葉子便收到了秋實的信息。該是收獲的季節了,該是成熟的時候了,自然也是主人家忙碌而欣喜的時候了!每一片綠葉,經過風兒的撫摸之后,便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輸送給就要成熟的果實。葉子由綠變黃,由黃變紅,就像一張張秋天的請帖,不時隨風飄動。鵝蛋大的柿子露了面,由淺綠色變成土紅色,燈籠似的吊在枝枝梢梢上,競相展示著自己的風采。而對那些調皮的鳥兒前來啄食從不大驚小怪,歡喜依然。冬日里,柿子樹失卻了蔽日的濃蔭,徒有枝杈老骨秋筋,參差錯落,如像不甘歲月剪裁高干闊葉的榮耀。
在后院的園子里,不僅柿子表現得那么艷紅累累,而且伴著它的紅豆杉、鐵樹、梨樹、石榴等也很有模樣地鮮活地長勢著。是呀,在春天,看見老爸在園子里翻地鋤草,剪枝上肥。在夏天,看見老媽在園子里澆水打藥,又菜又花。等到秋冬,望著這黃橙橙的果實,我仿佛覺得這是老爸老媽一生的真實寫照,從春的綠葉,秋的碩果,冬的淡定,看出了他們就像這柿子樹一樣,雖平平凡凡,卻對故土有著一片深情厚誼。
責任編輯 賈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