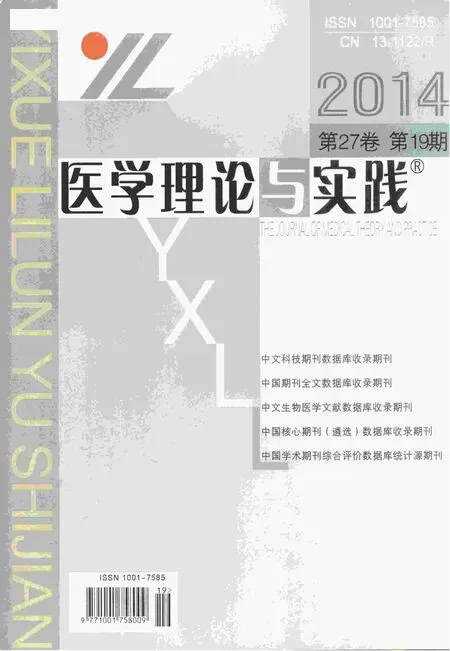微生物檢驗在感染控制中的價值分析
梁新妹 天津市濱海新區塘沽中醫醫院檢驗科 300451
感染在醫院中是比較常見的,在具備感染源、感染途徑以及感染人群等三要素的條件下更容易發生[1]。患者發生感染后可能導致嚴重的流行性疾病,對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產生一定威脅。最近幾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醫院引進了新的技術、材料以及方法等處理控制感染問題。根據黃軍垣等人的研究報道[2],加強微生物的有效檢測,合理控制感染,避免交叉感染的發生等成為了醫院安全管理的重要內容,我院選取尿路感染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采取微生物檢測方法展開感染預防控制對照性分析,現將結果總結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11年5月-2012年5月期間在我院住院治療的尿路感染患者300例作為觀察對象。其中男148例,女152例;年齡36~59歲,平均年齡(43.98±7.26)歲。將患者的中段尿培養后分離出大腸埃希氏菌300株,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150株,兩組菌株無明顯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菌株不采取任何處理措施,根據醫生的臨床經驗為患者配藥治療。實驗組菌株采取微生物檢測手段,方法如下:首先采用細菌鑒定,使用法國梅里埃公司生產的ID32E試條進行細菌鑒定。然后采用法國梅里埃公司生產的半自動微生物分析儀進行藥敏試驗檢測。確診試驗中先采用超廣譜β-內酰胺酶初次篩選,然后采用K-B法進行確診。分別給予頭孢他啶和頭孢噻肟30μg/片,克拉維酸10μg/片,加入克拉維酸后抑菌環直徑擴大超過5mm的判定為細菌感染,根據微生物檢測結果給予患者適當的藥物治療。
1.3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感染情況的控制效果。療效標準[3]如下:尿道疼痛比較輕微,患者的尿頻、尿急、尿痛以及尿不盡等臨床癥狀不頻繁發生,患者尿液中的囊尿、血尿、氣尿以及細菌尿量較少的為輕度感染;患者的尿頻、尿急、尿痛以及尿不盡等臨床癥狀比較容易發生,尿道疼痛稍重,患者尿液中的囊尿、血尿、氣尿以及細菌尿的量較多的為中度感染;患者尿液中的囊尿、血尿、氣尿以及細菌尿的量很多,尿道疼痛嚴重,患者的尿頻、尿急、尿痛以及尿不盡等臨床癥狀嚴重的為重度感染。對比微生物感染后患者的感染情況,分析微生物檢測的臨床應用價值。
1.4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組間等級資料比較采取秩和檢驗,以P<0.05為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實驗組患者輕度感染的發生率明顯高于對照組,中度感染和重度感染的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兩組患者的輕度感染、中度感染以及重度感染的發生率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Z=5.281,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發生細菌感染情況比較〔n(%)〕
3 討論
目前,國內醫院發生細菌感染的病例很常見,做好感染監測、預防醫院感染的發生比較重要。根據臨床經驗總結,醫院感染日益嚴重的原因在于介入性治療、化學藥物治療、放射性治療以及抗生素和免疫類藥物的濫用等,微生物檢驗能夠將最準確的診斷信息提供給醫生,醫生可以將感染的原因進行針對性的控制治療。楊柳[4]等人針對醫院感染微生物檢測的研究報道,微生物檢測關系著臨床感染性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以及醫院感染檢測工作,三者呈正相關關系。醫院感染監測的關鍵在于檢測好致病菌、控制好傳播途徑以及檢測易感人群等,而微生物檢測能夠很好的協調以上三者的關系,在醫院感染監管中起到重要作用[5~7]。患者、醫護人員以及醫院環境都可能成為感染源,預防醫院感染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消毒滅菌。而最可靠的殺菌消毒的方法就是生物指標法,生物指標能夠檢驗出消毒滅菌情況是否徹底,能夠將疾病傳播有效阻斷[8]。醫療器械和醫療用品的感染、醫生和護士的手、空氣污染以及環境污染均是醫院感染傳播的途徑,因此要定期的對醫護人員的手進行細菌學監測,有效阻斷細菌傳播。醫療器械是患者檢查診斷的必要手段,醫療器械中存在的微生物會損傷患者的皮膚和黏膜,尤其在潮濕的環境下致病菌的存活時間延長,因此要對醫院的病房以及辦公室進行定期的微生物監測,及時預防以及控制感染的發生[9,10]。醫院一般把住院治療的癌癥、白血病等患者稱之為易感人群,加強易感人群的耐藥性監測、呼吸道菌群監測以及腸道菌群監測是必要的預防感染的手段。本院尿路感染患者的細菌培養微生物檢測顯示,實驗組的感染程度與對照組相比明顯下降,說明微生物檢驗結果能夠為醫護人員提供準確的理論依據,合理地進行治療,控制感染的發生。微生物檢驗水平對醫院感染控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要加強檢驗者的檢驗技術,豐富診斷感染疾病的相關知識,調動檢驗工作者的主動性,提高檢驗工作者監測病原菌的診斷速度和準確性。
綜上所述,微生物檢驗能夠控制醫院感染、監測病原菌以及預測傳播途徑,微生物檢驗還能對易感人群進行監測,為醫生提供科學合理的藥物治療方案,微生物檢測對控制醫院感染的發生起到有效控制作用。
[1] 劉潔.微生物檢驗用于住院患者感染監控的臨床觀察〔J〕.中國基層醫藥,2013,20(8):1176-1177.
[2] 黃軍垣,鄭利平.加強住院患者臨床微生物檢驗對控制醫院感染的影響觀察〔J〕.四川醫學,2013,34(4):563-564.
[3] Nichol ST,Arikawa J,Kawaoka Y,et al.Emerging viral disease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0,97(23):12411-12412.
[4] 楊柳,郭清蓮,申及,等.回顧性分析比較不同臨床標本微生物檢驗的陽性率〔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11,32(14):1573.
[5] 張新秀.微生物檢驗在臨床應用中的質量控制〔J〕.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2011,10(5):396-397.
[6] 蘇建榮.重視臨床微生物檢驗分析后實驗室質量管理〔J〕.中華檢驗醫學雜志,2012,35(4):293-295.
[7] 馬立艷.加強微生物檢驗醫師與臨床醫師的有效溝通〔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11,32(10):1138-1139.
[8] 漆涌,鄭蘭香.基層醫院微生物檢驗進修醫生培養模式的初步探討〔J〕.實用預防醫學,2010,17(7):1457.
[9] Basu G,Rossouw J.Prevalence of rotavirus,adenovirus and astrovirus infection in young children with gastroenteritis in gaborone,botswana〔J〕.East Afr Med J,2007,80(12):652.
[10] 管惠彬.嬰幼兒腹瀉病原微生物檢驗結果分析〔J〕.四川醫學,2012,33(7):1275-1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