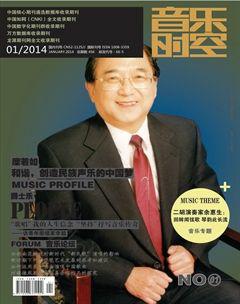試論肖邦第二鋼琴諧謔曲曲式結構
張海亮
摘要:肖邦的第二首諧謔曲(bb小調Op.31)以其戲劇性和幻想性讓樂曲充滿了獨特的風格,并被人們譽為富有浪漫氣息,且充滿熱情奔放情感的音詩,本文主要通過對第二鋼琴諧謔曲的創造特性進行分析,掌握肖邦在該曲上的情感內涵以及整體結構布局。
關鍵詞:肖邦 第二首諧謔曲 曲式結構
諧謔曲就字面上來看應理解為“戲謔”,這個詞匯早在17世紀就出現在意大利,直到巴洛克時期,“諧謔曲”才被用于描述聲樂和器樂作品,同時又因其速度輕快、節奏活潑,讓聽者能夠感受到樂曲的生氣和所要展現的幻想,因此又被稱之為三拍子。蒙特威爾第的《音樂的戲謔》(一二兩集)以及安東尼奧·布魯內利的《諧謔曲》、《詠嘆調》、《坎佐內特與牧歌》均是早期代表性較強的諧謔曲,前者為聲樂作品的代表,后者則為人聲與器樂結合的代表作品,而查爾羅的《小交響諧謔曲》則是純器樂中具有代表性的諧謔曲,但就總體水平來看,該時期的器樂諧謔曲作品非常少見,直到1650年后,以器樂為主的諧謔曲作品才逐漸增加。例如:約翰·瓦爾舍的《諧謔曲》,魯貝爾特的《小交響諧謔曲》以及約翰·申克的《音樂的戲謔》等。18世紀初,諧謔曲已發展成為了眾多樂章或套曲的重要部分,并以歡快輕松的風格而聞名,同時較常出現的諧謔曲也多以2/4拍為主,例如:JS·巴赫A小調帕蒂塔中的倒數第二樂章。到18世紀晚期,在諧謔曲三聲中部幾乎均以快三拍的形式出現,并多見于室內樂、奏鳴曲以及交響曲等套曲的第三樂章,且逐漸將小步舞曲樂章取締,使得套曲第三樂章的風格更加明快,更加活躍,不少音樂家,如布魯克納、舒伯特以及肖邦等均紛紛將其運用到套曲中,并通過大膽的創新和擴展,成功創作出不少非常優秀且各具特色的諧謔曲。
肖邦的第二首諧謔曲(bb小調Op.31)于1837年12月出版,肖邦將其作為弗斯登斯坦公爵夫人的獻禮,盡管第二首諧謔曲較之第一首并無悲劇性沖突,但其戲劇性和幻想性也使得樂曲充滿了獨特的風格,有人將其稱之為富有浪漫氣息,且充滿熱情奔放情感的音詩。當第二諧謔曲開始時,首先帶給人們一種不安的感受,再通過響亮的和弦對其進行威嚴的答復。第二諧謔曲以奏鳴曲式為主要結構,當樂曲的第一主題一出場,仿若有著巨大的魔力將我們深深吸引,急快板,聲音很弱,三連音敏捷而不安地緩緩揚起,仿佛正期待著所提“問題”的答復,在片刻沉默后,突發以威嚴的氣勢給予答復,仿若藐視一切不安。在這一問一答之間第一主題徐徐展開,在華麗的音符中將不安因子帶入其中,使第一主題能夠被流暢的帶出,而這也被譽為肖邦作品中以非凡魅力吸引聽著讓其沉醉其中的抒情主題之一,右手在引吭高歌,左手輔以美麗的音浪:在這首充滿神秘氣息的婉轉歌聲中,如同上升到了藍天中,看到萬里無云,晴空萬里的綺麗風光,一切的不安因此而消散,仿若體會到了幸福的真諦,這就是對“不安問題”的最好回答。在兩個主題反復之間,緩緩引出中間部分,中間部分初始給人們帶來寧靜祥和的氛圍,猶如和煦的陽光懶洋洋地灑在身上,一切都非常平靜,牧笛風曲調由遠處傳來:音樂仍然以安靜祥和為主調,直至另一主題的緩緩到來,以一問一答所組合而成的“二重唱”,讓不安因素在這平靜的環境下輕輕騷動。這兩個對話的曲調主要為:當“二重唱”的再次出現,仿若激烈的辯論展現在面前,中間部分所要展現的第二主題,一段如同彩虹般絢爛美麗的快速華彩性樂段隨音樂流出,徹底將不安情緒清掃出,讓聽者看到充滿希望的美好未來。樂曲對中間部分的三個主題均進行了重復,使第一、第二主題能夠得到再現,最后在即將結束的時候,以D大調來展現,這就將肖邦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樂觀精神展現地淋漓盡致。但由于形式復雜的獨立段落將發展部所代替,有部分學者在對該曲進行研究時提出:在發展部之前附有間奏曲的一種奏鳴曲形式。一開始第一主題就主要采用讓人內心騷動的音調,隨后,再通過和弦給予嚴肅的答復,將內心的勇氣和信心充分表達出來,連接部分則通過鮮明地對比逐漸將第二主題(副部)帶入,以無拘無束的旋律來傳達熱情奔放的豪邁激情,尤其在音符中將由愉快逐漸轉化為奔放的情感表達了出來,最后進行短小有力的收尾,再通過對呈示部進行重復,僅作為了稍微變化。主部主題被反反復復提及,連接部則通過強有力的高音來展開,一傾而瀉,并在重復中將副部主題更加充分地體現出來,諧謔曲從265小節開始由三部曲式的插部加展開插部組成,插部主要表現出以下三種音樂形象:
(一)是平穩、柔和的和弦,嚴謹沉思的旋律轉換為牧笛的吹奏。
(二)是一首二重唱,是上聲部通過運用略帶不安且輕快的襯腔聲部與樸素的歌調進行相互問答。
(三)是閃耀著光輝、充滿歡快的音調,逐漸從飄逸、輕盈的情緒中轉變為波瀾壯闊、豪邁雄壯的情感。
在對插部進行展現時,首先需對第三主題進行展現,右手連續起伏八分音符,讓那閃耀著光輝的華彩,一浪比一浪更高。緊接著將插部的第二主題緩緩展開,以一種激昂憤慨、咄咄逼人之勢突顯出來,緊接著將連接部展現出來,這是中間段落里第一次對呈示部的素材呈現出來,通過伴音化的旋律線條、頻繁的調性轉換等手法讓聽者仿若面前是深淵。接著通過插部第二主題的進入,音樂也從火熱的、激蕩的、充滿戲劇性的沖突中掙脫,緩緩平息。當諧謔曲進入再現部時,是從584小節開始,肖邦在對呈示部進行重復的時候,將旋律進行稍微改變,且并未對副部的調性進行變化,而是仍然以呈示部調性為主,至716小節后,諧謔曲進入到了尾聲階段,肖邦以勢不可擋的強大氣勢以及剛毅果斷的手法迅速對全曲進行收尾。
在發展部中間段落,諧謔曲所展現出的鮮明形象與呈示部相比毫不遜色,但相較于呈示部來說,其所塑造的形象緊張性更強,中間段落與前后的呈示部、再現部截然分開,故中間一段始終讓人感覺其為獨立樂章,且有不少研究者將其認定為間奏曲,間奏曲里同樣存在三個非常明顯地音樂形象對比:一是平穩、柔和的和弦,嚴謹沉思的旋律轉換為牧笛的吹奏;二是含有深刻內涵的音樂形象,一首二重唱,是上聲部通過運用略帶不安且輕快的襯腔聲部與樸素的哥調進行相互問答;三是閃耀著光輝、充滿歡快的音調,逐漸從飄逸、輕盈的情緒中轉變為波瀾壯闊、豪邁雄壯的情感。
前面已經提到,肖邦在對呈示部進行重復的時候,將旋律進行稍微改變,且并未對副部的調性進行變化,而是仍然以呈示部調性為主,進入到了尾聲時,再以勢不可擋的強大氣勢以及剛毅果斷的手法迅速對全曲進行收尾,這就使肖邦勇往直前的氣勢被展現出來。在肖邦的作品中,踏板與術語內涵是非常主要的要素,尤其是踏板,這也是肖邦被稱之為“鋼琴詩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肖邦的音樂有著非常強的旋律,故在對其作品進行演奏時,對手指觸鍵的要求非常高,當演奏者的手指技術滿足演奏所需時,同時配合踏板,可使樂曲效果更加精彩,可謂是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同時通過對不同樂段進行分析,配合不同的踏板。例如:在尾式段第5小節-第8小節,通過全踏板的配合,使得和弦彰顯地更加飽滿,使音響效果更加理想,而在第65小節時,則無需過深踩踏踏板,僅需要2/3的踏板即可,且均為切分踏板,這就能夠讓樂曲效果更加優美,旋律更加流暢,可以說在肖邦作品中,踏板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肖邦諧謔曲仍然以詼諧性為主,但在其本質意義上,增強其戲劇性張力,使表情范圍無限擴大,同時,通過深刻的體裁和動蕩的形式來展現,這就將肖邦深刻的思想內涵、成熟的藝術表現形式以及高操的藝術手法展現出來,這也是保證諧謔曲更加富有生命力的主要因素,甚至我們可將其稱之為獨特的鋼琴交響曲。
參考文獻:
[1][俄]索洛甫嗟夫.肖邦的創作[M].中央音樂學院編譯室譯.北京:音樂出版社,1956.
[2]李娓娓.肖邦詼諧曲研究[M].臺北:全音樂譜出版社,1983.
[3]賈晶.論肖邦對古典主義時期鋼琴諧謔曲體裁的拓展與革新[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1年.
[4]袁靜,付思超.淺談肖邦b小調鋼琴諧謔曲op.31作品分析及演奏特點[J].北方音樂,2012,(1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