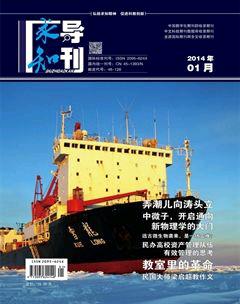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
Oubai+Elkerdi
直到最近,我還是一名用技術改造教育的積極倡導者。多年以來,先行者們的思想和工作一直都在激勵著我,比如簡·麥克格尼格(Jane McGonigal)、
凱蒂·薩倫(Katie Salen)、可汗學院創始人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所有的壞事都對你有好處》(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的作者斯蒂夫·約翰遜(Steven Johnson)、道格拉斯·托馬斯(Douglas Thomas)和《學習新文化》(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的作者約翰·斯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
作為一名技術愛好者和工科生,我相信仰賴技術之福,我們與他人及環境的互動之道不僅豐富了我們的閱歷,還改善了我們這個物種的生存狀態。我認為每一種新的工具都能夠加深我們對世界上一些最具挑戰性問題的理解,并使我們有效地應對它們。在每一次技術進步中,我都預見到潛力;伴隨著每一次技術突破,我都期許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不過,正如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在他發人深省的著作《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當中寫道,“若要對任何一種新技術,或者通常而言的進步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便應當對所失有著與對所得一樣的敏感。我們不應任憑技術的光芒蒙蔽自己內心深處的忠誠守護,以至于麻木了自身本質的那一部分。”
比如說,視頻游戲令我們浸淫于虛擬空間,在其中我們需要學習在意識中旋轉物體以及游歷各種各樣的結構和環境,這或許增強了我們的視覺空間智力。但是,卡爾發出了警告,這種能力的獲得“與支撐著我們‘記憶性知識獲取、歸納分析、批判性思考、想象力和反思的‘深加工能力的減弱如影隨形。”
實際上,計算機實現不了真實世界的微妙和復雜——不管技術變得多么先進或者精深。虛擬現實技術之父、數字媒體領袖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在他的宣示性著作《你不是個玩意兒》(You Are Not a Gadget)中點評道,技術往往“在一個去除了數據源一切個性品質的標準化系統內抓住了現實具有某種限制的量度。”這是因為我們開發的算法和工具反映的都是我們對世界的主觀理解,而我們的意識無法完整地領悟或表現一件事物。
藝術家、互聯網人類學家喬納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曾投身于幾個高度原創性的項目,目的是探求理解及贊美人性的革命性方式,幾年之后他得出了與拉尼爾類似的結論。在他的每一個項目中,哈里斯都感受到自己工具的局限以及僅僅利用數字信息挖掘深度與意義的困難。最終他對于技術的觀點遭到了翻天覆地的重塑。
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士·伊文思(James Evans)的一項研究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深刻見解。伊文思研究了3400萬份文章,將互聯網被引入學術研究之前和之后的學術論文進行了比較。他不僅證明了寫就于數字時代之后的論文在引文方面不夠豐富及多樣化,更是指出,舊式的圖書館搜索之所以有助于擴展學者的視野,恰恰是因為搜索過程在觸及真正想要的研究材料之前多多少少會瀏覽到無關的文章。正如卡爾所注意到的,“搜索引擎往往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與我們當時的搜索對象極度相關的文本片段甚至寥寥數語,而幾乎不會鼓勵我們從整體上對待研究工作。我們在網上搜索時不見森林,甚至不見樹木。我們看到的只有枝葉。”
有得,也有失。任何熟悉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人都知道,思考模式的轉變并不能靠強推輿論和規范科學帶來,而應該通過允許異議和發散性思維實現。科學革命的發生乃是由于無所畏懼的頭腦在未被探索過的領域尋求不同尋常的解釋。但是,將我們限制于某種特定思維模式(通常是開發者的世界觀)的算法,又怎么能夠讓我們質疑自己對自然的基本假設呢?
正如伊文思所證明的,每一次出現新技術時,我們試圖借以省卻的乏味而看似不相關的任務,原來都是我們學習經歷中最為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們對我們有所助益恰恰是因為它們令我們身心疲憊。依靠計算機的效能減少人類錯誤使我們的工作缺乏深刻的思考和原創性,最終令我們學到的東西不像辛苦勞作的時候多。
攝影師富爾維奧·博納維亞(Fulvio Bonavia)針對技術和藝術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一種深刻的觀點:“如今攝影行當面臨的巨大挑戰是數字技術降低了成為攝影師的門檻,但是出類拔萃卻更難了。當我還是一名手工插畫師和圖形設計師時,我會花上一整天手工創作某個作品,現在同樣的工作利用計算機兩分鐘之內就可以完成。然而我過去花掉的時間一點都沒有被浪費,因為我覺得那讓我更加成熟,讓我學會了專注、耐心、精確以及注意不犯錯誤。”
最近一些神經可塑性方面的研究表明,我們使用的每一種工具都能以不同的方式改變我們大腦的物理結構。卡爾用一種為人熟知的例子闡釋了這一點:“一頁在計算機屏幕上瀏覽的文本看起來或許和一頁打印文本差不多。但是,在網絡文檔中卷動或者點擊所需要的身體活動及感官刺激,與手握并翻動一本書或者雜志時截然不同。研究表明,閱讀這一認知活動不僅調動了視覺,還調動了觸覺。它既是視覺行為也是觸覺行為。”
幾十項由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神經生物學家、教育工作者和設計師開展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們一旦聯入網絡或者將數字技術應用于教育,便是進入了一個促使我們粗略地閱讀、草率而心不在焉地思考以及膚淺地學習的環境。我們以為自己獲益,是因為我們已經開始采用媒介自身的標準來定義智能。卡爾說得好:“當我們慣于依賴計算機來調和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便意味著我們的智能已委身于人工智能。”
見到很多企業家和教育界領袖將技術引入教室、難民營和其他場所,希望使學習大眾化,我心中的憂慮多于希望。那么多心存善意的人對教育感興趣,是一種人們樂于見到的現象。然而僅有善意是不夠的,正如伊萊亞斯·阿布賈德(Elias Aboujaoude)的急切之言:“這些做法的效果有待于去理解、研究以及討論。”
對技術狂熱者來說,了解本文提及的研究并對新時代的花言巧語提出質疑是尤為重要的,這樣我們或許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技術的進步牽涉了什么,又危及了幾多。我將以杰倫·拉尼爾的警世箴言結束此文:
“當應對活生生的人時,技術人員必須采用全然不同的方法論。我們對大腦的了解不足以在科學的基礎上領悟諸如教育或者友誼之類的現象。因此,當我們以影響到現實生活的方式部署學習或者友誼等的計算機模型時,我們是在依賴信仰。當我們要求他人借助我們的模型去生活時,我們可能是在貶損生活本身。我們怎么會知道自己可能會失去什么呢?”(來源:果殼網,2013-10-3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