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野》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何寶民
《秋野》是上海暨南大學(xué)秋野社的社刊。20世紀(jì)20年代末上海學(xué)生文藝社團中,秋野社是為人熟知的一個,由暨南大學(xué)校長秘書兼文學(xué)院院長章衣萍(1900-1947)發(fā)起建立。暨大學(xué)生陳翔冰、陳妤雯、陳雪江、鄭吐飛 (原名鄭泗水)等,暨大的教師夏丏尊、顧仲彝、葉公超、余楠秋、張鳳、汪靜之、章鐵民等,都是秋野的校內(nèi)社員。文學(xué)社成立時正值天高氣爽的秋天,于是從李賀《南山田中行》詩中取“秋野”二字命名。1927年12月,社刊《秋野》創(chuàng)刊,暨大出版科出版,開明書店發(fā)行。三十二開本,一百余頁。
衣萍在《發(fā)刊詞》中道出了秋野社的宗旨:“秋野社是為坦白的表現(xiàn)我們的感情,我們心靈上的苦悶而產(chǎn)生的,其唯一的目的是從荒寞中辟出樂園來。”進而抒發(fā)了秋野社同仁的心聲:“我們住在青天白日下的江南革命之邦,我們勇敢的前驅(qū)的戰(zhàn)士的鮮血已經(jīng)流成河渠了。然而,看呵,我們的心靈是怎樣的苦悶,我們的感情是怎樣的隔膜,我們社會是怎樣寂寞和消沉!‘從寂寞中辟出樂園’來,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朋友們,我們不必想望那遙遠的‘樂園’,并且,‘樂園’實在不是我們暫時所需要的事。同是站在戰(zhàn)場的血泊里的人,我們應(yīng)該悲哀地哭,應(yīng)該狂樂地笑,用我們的哭聲和笑聲去安慰那偉大的地下和地上的革命的靈魂,同時把自己的怠惰和寂寞的靈魂也劇烈地喊醒,我們需要的是革命,不是‘樂園’。把‘樂園’留給未來的遙遠的朋友們吧。我們應(yīng)該唱著勇敢之歌走到戰(zhàn)場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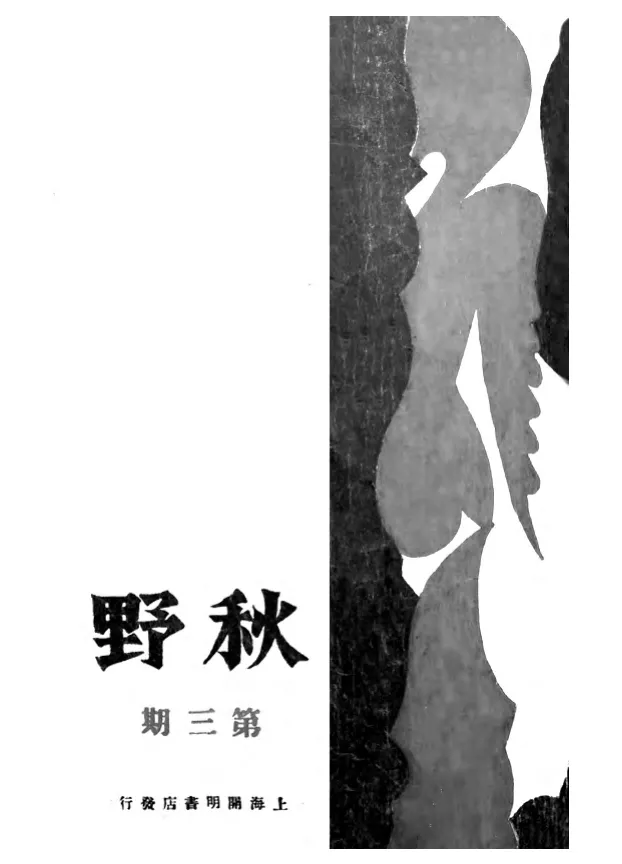
《秋野》第三期刊影
27歲的章衣萍當(dāng)時是和魯迅過從較多的朋友。魯迅曾多次應(yīng)邀到暨大演講。第一次是應(yīng)老友夏丏尊之邀。夏丏尊時任暨大國文系主任兼教大一國文。因為國文系剛建立,只有一年級學(xué)生,所以邀請是以“同級會”的名義發(fā)出的。《魯迅日記》1927年11月6日:“上午丏尊來邀至華興樓所設(shè)暨南大學(xué)同級會演講并午餐。”主要講關(guān)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讀書方法等問題,可惜講稿不存。
隔了一個多月,章衣萍敦請魯迅再次來到暨大。《魯迅日記》12月21日:“午后衣萍來邀至暨南大學(xué)演講。”這次演講題目是《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演講的記錄稿有兩種版本:一是章鐵民記錄。《魯迅日記》12月29日:“下午寄還暨南大學(xué)陳翔冰講稿。”“講稿”,即魯迅的演講記錄。秋野社將記錄送請魯迅修改審定,魯迅審閱后寄還陳翔冰。記錄稿的題目就是《文學(xué)與政治的歧途》,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秋野》上發(fā)表,署“魯迅先生講演,章鐵民記錄”。章鐵民 (1899-?),安徽績溪人。時在暨大附中任教。一是劉率真記錄。題目也是《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刊載于1928年1月29日和30日上海《新聞報》的副刊《學(xué)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魯迅講,劉率真記”。劉率真,即曹聚仁 (1900-1972),浙江蘭溪人,時任暨大教授。魯迅《集外集》收入的是后者。
章的記錄稿 (以下簡稱《秋野》文)約三千字,曹的記錄稿 (以下簡稱《集外》文)多了一千字左右。比較閱讀兩篇《文學(xué)與政治的歧途》,會更接近演講的“原貌”。
《集外》文較《秋野》文記錄得比較詳細。如,《秋野》文中“政治家對待文學(xué)家起初是捧,后來是殺;這是毫無理由的”一句,《集外》文中是:
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xué)家,又感到現(xiàn)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
魯迅稍后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說到革命家要改變現(xiàn)狀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革命成功了,革命家成了權(quán)力者。身份不同,態(tài)度也就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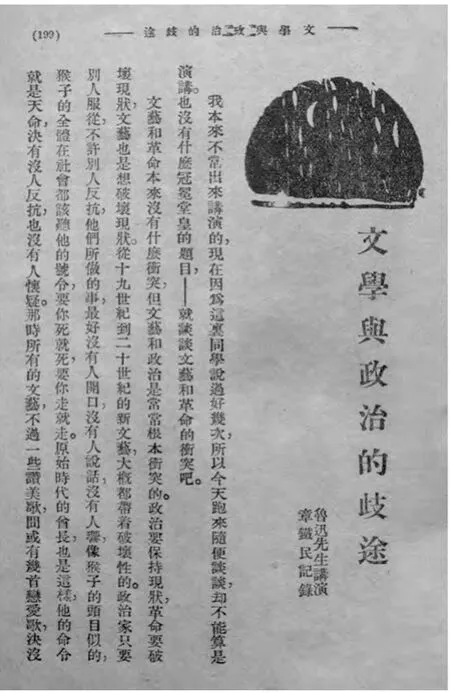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首頁
記錄詳略差別不大,表述卻有不同。如,《秋野》文中“文學(xué)家時時要理想革命,時時和現(xiàn)實沖突,所以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都不能舒服。真正的革命文學(xué)家永遠不能出頭,永無好日,這是命運”這一段在《集外》文中則是:
在革命的時候,文學(xué)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為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現(xiàn)實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們這樣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現(xiàn)實不一致,這是注定的運命。
說得更為透辟。接下來,魯迅說:“蘇俄革命以前,有兩個文學(xué)家,葉遂寧和梭波里,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后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xiàn)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葉遂寧,現(xiàn)通譯葉賽寧。蘇聯(lián)政府過去一直宣稱葉遂寧是自縊身亡。“2005年10月25日的《參考消息》刊出了俄新社記者阿拉托科·科羅廖夫?qū)懙摹度~賽寧:是自盡或是他殺?》一文,報道了剛剛拍攝完成的一部關(guān)于葉賽寧的電視劇,就推翻了他是自殺的傳統(tǒng)說法,認(rèn)為是克里姆林宮指使人暗殺了他。”(朱正:《重讀〈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秋野》文較《集外》文詳?shù)牟欢啵灿欣狻Q葜v稿的第二段,《集外》文中在“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后,接下來是:“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這一句,在《秋野》文中卻是長達四行的文字:
文學(xué)家希望破裂,政治家希望不破裂,結(jié)果是文學(xué)家受排擠。當(dāng)革命者不曾成功的時候,他們和文學(xué)家是合作的,他們要利用文學(xué)家做宣傳革命的工具。一到革命成功,革命者變?yōu)檎渭遥麄冎辉S別人服從,他們是一言一動不容他人有懷疑的余地。但文學(xué)家有自己的理想,不肯附和別人的意旨,就不能不受排擠。
演講中有的看似與主旨無甚關(guān)聯(lián)的“題外話”,《秋野》文中未見錄存,而《集外》文中保留下來。如,演講開始一段。《秋野》文是:
我本來不常出來講演的,現(xiàn)在因為這里同學(xué)說過好幾次,所以今天跑來隨便談?wù)劊瑓s不能算是演講。也沒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題目,——就談?wù)勎乃嚭透锩臎_突吧。
《集外》文卻有具體的實例:
我是不大出來講演的;今天到此地來,不過因為說過了好幾次,來講一回也算了卻一件事。我所以不出來講演,一則沒有什么意見可講,二則剛才這位先生說過,在座的很多讀過我的書,我更不能講什么。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紅樓夢》里面的人物,像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都使我有異樣的同情;后來,考究一些當(dāng)時的事實,到北京后,看看梅蘭芳姜妙香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并不怎樣高明。
從“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說到《紅樓夢》,再說到舞臺上的賈寶玉林黛玉。話題所及,也反映了魯迅對舊劇的看法。這些“閑話”,同時活躍了演講的氣氛。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是魯迅的名作。魯迅論述文藝家、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微妙關(guān)系:當(dāng)反對舊社會的黑暗勢力時,左翼文藝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之間是可以合作的,因為有“不安于現(xiàn)狀的同一”。但是當(dāng)革命勝利,革命政治家掌握政權(quán)以后,這時候他就希望維持現(xiàn)狀,文藝家如果不識相,還要繼續(xù)不滿于現(xiàn)狀,政治家就不能容忍了,二者就會分道揚鑣。政治家為什么要同文藝家過不去?魯迅說:這是因為文藝家“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 (有時,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軋他)”。“政治家認(rèn)定文學(xué)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大膽說出別人不愿說不敢說的話,正是文藝家賈禍的因由。將近70年后,魯迅的兒子周海嬰記述: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小住,邀約幾位老鄉(xiāng)閑聊,翻譯家羅稷南也參加了座談。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nèi)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shè)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shè)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絕不敢如此冒昧,羅先生卻直率地講了出來。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rèn)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guān)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魯迅與我七十年》)這一嚴(yán)峻回答使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也印證了魯迅在講演中的論斷。先生就文藝家與政治家關(guān)系議論之深刻精辟,幾十年來無出其右。朱正稱道這篇文章“具有穿越時空看透各種政治家的歷史的眼光”。(《重讀〈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曹聚仁因為他的記錄稿與章衣萍曾有過糾結(jié)。他在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中幾次提到這件事,對章頗為不滿。在《〈情書一束〉的故事》一節(jié)說:“我和章衣萍很少往來,只有一回,魯迅先生到暨大來演講,我曾作了記錄;那份稿子,寄到《北新》半月刊去,他卻把稿子壓住了,沒讓魯迅先生看到。后來,我的筆錄稿在《新聞報》發(fā)表了,魯迅先生才知道有這么一段經(jīng)過,說了他一頓。(《集外集》所收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便是我的稿子。)這是我和魯迅相識之始。”在《魯迅與我》一節(jié),曹又說:“這篇講稿,并不曾在上海版《語絲》半月刊刊出,給章衣萍擋住了,退還給我。后來刊在《新聞報·學(xué)海》上;那年,楊霽云兄編《集外集》,我把剪報交給他,魯迅先生看見了,要去編入正文的 (可看魯迅寫給楊兄的信。楊兄那時在持志學(xué)院聽我的課)”。曹聚仁說的情況,見之于魯迅1934年2月19日寫給楊霽云的信,信中說:“曹先生記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為附錄了。”一個“也”字,說明魯迅認(rèn)可了章鐵民的記錄稿,而且時間在認(rèn)可曹聚仁這份記錄之前。曹說章衣萍壓下了他的記錄稿,雖然一說《北新》,一說《語絲》,前后不一,但這個可能是存在的。既然《秋野》上已經(jīng)刊出了章鐵民的記錄稿,章衣萍作為《秋野》的主事者當(dāng)然不希望再有另外的記錄稿發(fā)表。
1929年12月4日,魯迅在暨大又有一次講演,講題是《離騷與反離騷》,記錄稿后刊登在《暨南學(xué)刊》。前一年的11月,《秋野》在出了第二卷第六期后已經(jīng)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