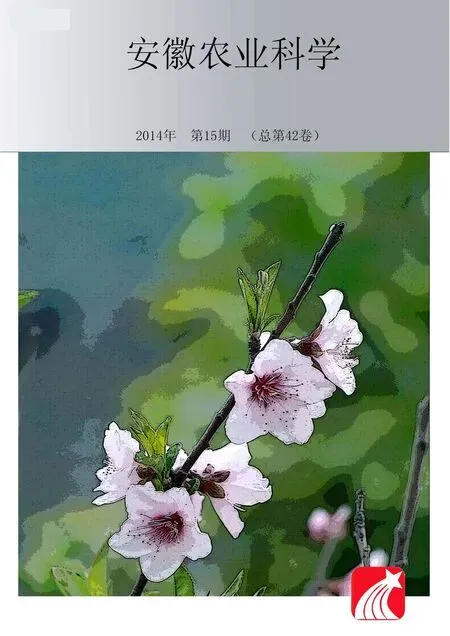城鄉統籌的國際經驗借鑒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陳 軼,朱 力,張 純
(1.南京工業大學建筑學院,江蘇南京210000;2.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100871;3.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北京100044;4.北京交通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北京100871)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越來越多農村人口涌向城市的同時,農村地區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凋敝。事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在特定發展階段,都出現過城鄉發展不同步的現象。國外發達國家如德國、韓國、日本等在統籌城鄉進程中均做出了相應的嘗試,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了解國外統籌城鄉的實踐經驗對于推進我國城鄉統籌進程具有參考價值。
城鄉統籌作為城鄉關系的一個特有階段,目前在城市規劃領域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近年來,隨著我國政府層面對城鄉統籌、農村問題的重視,城鄉統籌的社會意義越發重大。我國在2003年初開始提出城鄉統籌政策,國內對城鄉統籌的研究歷經概念描述、方法措施、批判性解讀等方面,中國的城鄉統籌正在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林毅夫[1]、樊綱[2]、韓俊[3]認為我國目前的城鄉統籌手段多是采取重視物質空間布局的方式在農村地區建設中小城市、小城鎮及城郊社區群,以此提供新增就業滿足農村地區就業需求;孫自鐸認為城鄉統籌的核心在于城鄉差別完全消失、城鄉關系達到完全融合[4];石憶邵認為城鄉統籌是城鄉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城鄉社會、經濟、文化的持續協調發展[5]。在方法措施方面,樊綱[2]、林毅夫[1]認為減少農業人口是控制城鄉差距縮小的有效辦法;韓俊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達到城鄉利益平等的關鍵[3];石憶邵[5]、趙群毅[6]、趙英麗[7]認為城鄉一體化具體體現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現在城鄉資源高效地綜合利用、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均衡配置、城鄉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融合。在批判性解讀方面,張京祥[8]、韓俊[3]、李兵弟[9]指出目前的實踐存在以城鄉統籌的名義,掠奪農村土地資源、將城市建設項目下放到農村地區進行非法建設等。總體上,目前對城鄉統籌的概念及對策措施研究較多,然而城鄉統籌成功與否的關鍵與國情和城鄉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現有研究對世界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城鄉統籌的經驗借鑒研究較少,特別是對城鄉統籌的關鍵環節如農村市場化、土地分類、農村法律制度建設等方面的經驗借鑒尚不多見。
筆者選取中東歐和中亞、日本、韓國和德國經驗進行回顧和比較,探討在城鄉統籌中在對農村政策傾斜、土地分類整理等方面的經驗及與中國目前實踐的差異,并基于這些經驗借鑒對解決中國城鄉差異問題提出相應的建議。
1 城鄉統籌國際經驗借鑒——來自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地區的實踐
1.1 農村市場化案例:中東歐和中亞的城鄉統籌 20世紀90年代初,中東歐和獨聯體經歷了劇烈的經濟衰退,重振農業經濟成為了首要任務。中東歐國家意識到增加非農就業對改善農村經濟有直接的作用,進而對非農業人口往城鎮遷移有推動作用。他們對中東歐國家非農就業的內部結構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對如何進一步完善農業改革、提高非農就業比重、加快農村人口向城鎮轉化進行了必要的探討。具體措施如下:①鼓勵農民提高“非農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②推動農村地區市場化進程;③注重建立統籌城鄉就業的管理體制。
1.1.1 鼓勵農民提高“非農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中東歐國家農村地區的農民兼業特征明顯,從事非農產業帶來了收入的提高。非農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5個方面:家庭內部非農活動、農村小城鎮的非農業活動、大城市的非農業活動(涉及通勤)、家庭成員從城市中的匯款、家庭成員從國外的匯款[11]。由于難以從空間角度界定非農業活動發生的具體區位,比如非農業活動會發生在農村、小城鎮附近以及城鄉結合部等不同的區位,這些分類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家庭非農收入的真正來源,此外,非農業收入的來源方式多種多樣,主要分為兼職類的通勤和施工、自謀職業類的農產品貿易和鄉村旅游以及農業本身的農產品加工為主(表1)[12]。中東歐國家農民兼業現象表明農業不再是收入的重要來源,非農就業收入才是提高收入的源泉,按照世界各國城鎮化的一般道路來看,農民進入城市或城鎮就業是一種適合大部分農民的道路,但也仍有相當一部分離不開土地的農民不能到城鎮就業,這樣一來,鼓勵農民以兼業的方式提高收入,減少了“舉家離農”式的農業人口外流,有利于緩解城市人口的過度集中。

表1 部分中東歐國家農業額外收入的主要來源(非農業收入百分比)%
1.1.2 推動農村地區市場化進程。中東歐國家意識到制約農業改革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因素。他們用計劃和市場兩種體制對農業增長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發現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獨聯體國家在農業改革的各方面都落后于以市場經濟為主的中東歐國家[12-16],再一次說明了制度在農業改革和城鄉統籌的重要性。推動農村市場化進程包括推動價格和市場、土地改革、農產品加工市場化、農村金融市場化以及體制市場化等方面。以1分代表計劃經濟,10分代表市場經濟,數值越小表明該國家計劃經濟比重越大,數值越大表明該國家市場經濟比重越大[12],分析顯示,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波蘭在農業改革的各方面都優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羅馬尼亞、亞美尼亞、格魯尼亞和烏克蘭(表2)。

表2 部分中東歐和獨聯體國家農業改革評分
1.1.3 注重建立統籌城鄉就業的管理體制。中東歐國家在城鄉統籌過程中注重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體系,在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保護農民合法權益方面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有效地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互促進,帶來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形成良性循環。值得注意的是,農業就業比重在中東歐國家和獨聯體國家接近十年的變化情況,在改革之前,中東歐和獨聯體各國的農業就業比重為10%~30%,其中波蘭和羅馬尼亞的農業就業比重達到26.4%和27.5%。伴隨著體制改革,各國的農業就業比重發生了顯著變化,大體的趨勢是中東歐國家的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呈下降趨勢,而獨聯體國家的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表3)[17-18]。這與中東歐國家農村勞動力轉向非農就業的趨勢緊密相連,由于中東歐國家逐步的市場化進程帶來了國民經濟的增長,推動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快速增長的GDP為農業勞動力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非農就業機會,促使了農業勞動力向城鎮及第二、三產業轉移,而獨聯體國家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國民經濟增長緩慢,難以提供非農就業崗位,導致勞動力向農業轉移,引發高水平農業隱性失業[12]。

表3 部分中東歐和獨聯體國家農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 %
1.2 町村改造案例:日本的城鄉統籌 日本是個島國,耕地面積只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3.6%,二戰初期城鄉差距較大,農業資源大量流向城市,耕地被大量占用,農業生產出現萎縮的狀況,針對這一狀況,當日本經濟戰后稍微有所好轉時,日本當局就將農村的凋敝現象加以重點關注,以此扭轉城鄉失調的局面。日本的城鄉統籌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人均GDP達到5 000美元,開始有能力城市反哺農村,具體的做法包括:①注重農村法律保障;②采取“市町村合并”提高農村地區行政效率;③促進農村多產業發展;④加強農村基礎設施;⑤實行傾斜政策。
1.2.1 注重農村法律保障。在遏制城鄉差距方面,日本政府采取了制定相應的農村法律措施,使農村的發展有法可依,具有代表性的有《農業基本法》、《經濟社會發展計劃》、《農振法》、《農協法》、《過疏地域對策特別措施法》等,這些法律的制定為日本城鄉統籌進程的有效展開確定了法律基礎。此外,在農村發展方面,日本政府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抓住重要的6個方面展開,主要包括農村工商業、基礎設施、土地規模經營、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業協會的建設等[20]。此外,增加對農村地區的投入還體現在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增加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社區公共事業建設的財政投入等方面。總的來說,日本在城鄉統籌中從制度層面為農民、農業、農村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從而使日本的城鄉差距得到了實質性的縮小。
1.2.2 采取“市町村合并”,提高農村地區行政效率。日本的“市町村”合并其主旨在于擴大社會公共設施的覆蓋面、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行政管理的規模效應等,為此,日本政府自明治維新以來共進行3次大規模的町村合并,即“明治大合并”、“昭和大合并”和當前的“平成大合并”[21]。町村作為日本最基本的行政單元,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小、影響之大都促使日本政府在實行“市町村合并”時需要充分考慮人口規模與小學需求、村莊數量與行政效率、村莊規模與社會公共設施共享等[22-23],總體上看,“市町村合并”僅僅是用行政區劃調整的手段提高了農村運行效率,并未造成農村地區人員的搬遷,這種做法得到了農村居民的首肯。
1.2.3 促進農村多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是農村地區發展的支撐,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農村工業的發展是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有力保障。在農村產業轉移方面,日本政府采取城市大企業到農村地區投資設廠的方式,使農村工業得到發展。此外,鼓勵農民兼業,增加農民非農業收入[24]。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日本采取了多渠道的融資方式,除了財政撥款外,還通過發行地方債券、貸款等方式用于公共設施的建設。有數據統計,日本的3 000多個町村都配備了污水、固廢處置設施[24],市政設施水平配套程度高。
1.3 新村運動案例:韓國的城鄉統籌 韓國是一個以丘陵、山地居多的國家,國土面積9.93萬km2,耕地只占國土面積的22%。20世紀70年代,韓國經濟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迅速拉大的城鄉差距使政府意識到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性,“新村運動”便營運而生。參考吳自聰等的研究成果[26],韓國城鄉統籌發展的階段性實踐見表4。韓國的城鄉統籌突出的特點包括:①制定階段性目標;②推進小城鎮促進政策[27]。韓國小城鎮促進政策具體包括營造城鎮、營造小城鎮、開發小城鎮3個進度見表5。

表4 韓國城鄉統籌發展階段性實踐

表5 韓國小城鎮促進政策總結
1.4 城鄉等值化案例:德國的城鄉統籌 二戰以后,德國的農村問題長時間比較突出,基礎設施嚴重缺乏,大量人口涌向城市,農村經濟凋敝。在此背景下,提出“在農村地區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質量”、“與城市生活不同類但等值”的“城鄉等值化”理念。巴伐利亞州采用“城鄉等值化”理念,開始通過土地整理、村莊革新等方式,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得以平衡發展,創造性地解決好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此后,這一發展方式成為德國農村發展的普遍模式,并從1990年起成為歐盟農村政策的方向。主要采取的措施有:①強調分類型土地整理;②保障農民利益。
1.4.1 強調分類型土地整理。分為常規性土地整理、簡化土地整理、項目整理土地、快速土地合并、資源交換土地等方式,對土地進行分類型整理,具體見表6。
1.4.2 保障農民收益。巴伐利亞州的實踐經驗和啟示。第一,進行“土地整理”,如將分散的小塊土地進行合并、將優等的土地置換用于農業生產等,以提高農業生產的集約化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產效率。第二,農民的田產和房產是農民自己的財富,農民有權變賣,也有權將其作為信貸抵押到銀行申請貸款,開辟新的致富途徑。第三,動員大公司到農村開辦企業,給離開土地的農民提供新的就業崗位。第四,鼓勵各地區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展開多種經營,實行積極的產業引導政策。第五,政府設立專項資金,通過職業培訓促進農民就業,并對農民開辦中小企業提供幫助。第六,采取“開發”和“保護”結合的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28-29]。

表6 德國巴伐利亞州土地整理類型
2 城鄉統籌國際經驗總結及評述
2.1 鼓勵農村市場化進程,增加農民財產性收益 中東歐和中亞在城鄉統籌經驗借鑒上著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推動農村地區市場化進程以及統籌建立城鄉就業的管理體制等方面,概括而言,中東歐和中亞國家地域臨近卻有著不同的體制,兩者對比研究更能體現體制、制度對城鄉統籌發展的影響。
我國和中東歐國家制度上類似,都是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而且中東歐國家開始城鄉統籌的時間比我國早10年左右,現階段基本停留在促進農民收入多樣化以及保障農民順利實現統籌城鄉的就業制度上。農村市場化是制度變革的產物,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帶來了城市和鄉村要素的流動性,盤活了農村土地資源,為農民增收創造了多樣化的途徑。市場化的進程也會帶來貧富差距加大,增加失業率,此時,如果處理不好則可能導致大量的農村人口再次從第二、三產業轉向農業,造成高水平的農業隱性失業,這種情況是我國在城鄉統籌進程中著力避免的。
2.2 完善新農村建設制度,確保農民利益有保障 日本政府在日本經濟發展到拐點時,持續增加對農村地區的投入,投入不僅包括了資金投入,更包括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改革。因此,日本政府在著手城鄉統籌方面意識到如何打破阻礙城鄉要素流動的制度,如何提高農村地區的效率是治理的關鍵。其主要做法有運用法律手段使日本農村的各項開發受到保護,通過行政體制調整提高日本農村地區的行政效率,實施對農村地區的政策傾斜為發展創造機遇,通過產業和基礎設施雙管齊下帶動日本農村的全面發展。
日本作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在20世紀70年代便意識到農村問題的嚴重性,并在發展城市的同時兼顧農村地區的發展。日本政府在城鄉統籌實施的亮點主要體現在從制度和體制上促使農村和城市要素雙向流動,采取了特別為農村地區制定的農村法律保障,使農村地區的建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此外,還特別體現出對農村地區的政策傾斜,采取農村地區的土地規劃、明確的投資體制、嚴格的環境保護、農民的參與機制等4個方面的方式措施實現對農村、農民、農地的有效保障。
在統籌城鄉的制度安排上,日本專為農村地區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傾斜有借鑒之處。我國現階段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矛盾最多的是土地流轉,而農民利益得到保障的唯一途徑就是立法。此外,重視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地域劃分以及區域政策的制定,區域開發與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構想是通過一系列政策來反映和實現的。
2.3 推進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加強城鄉聯系的關鍵節點 韓國政府則在循序漸進推進城鄉統籌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韓國政府意識到推進城鄉統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個需要長久堅持的政策方向,為此韓國設立了6個階段、3個進度,經過長達近40年的實踐,有效地縮小了城鄉差距。
韓國政府通過分階段目標逐步縮小城鄉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收到了良好的成效。總體上看,韓國政府實施的是由硬到軟、由慢到快、循序漸進的過程,從最初的重視基礎設施投入逐步轉向重視農村地區的制度建設等,在剛開始,調整的速度不宜過快,應該逐步設立小城鎮為增長極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在統籌城鄉的空間布局上,韓國的營建小城鎮促進政策方面有可取之處。我國城鎮體系歷來缺少中小城市、小城鎮,因此造成了廣大的農村地區缺乏強有力的增長極。這種做法類似英國的新市鎮建設,未來我國在統籌城鄉發展的空間布局上,要將建設新市鎮作為吸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節點。韓國設置營造小城鎮的方法類似英國建設“新市鎮”的方法,我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需要通過市鎮建設帶動農村地區的發展。
2.4 分類進行農村土地整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德國作為歐洲城鄉統籌的實施的代表國家,在城鄉統籌實踐中側重于土地整理,他們將土地整理分為常規性土地整理、簡化土地整理、項目整理土地、快速土地合并、資源交換土地等不同類型,并對農民利益在開發的基礎上予以保護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在統籌城鄉土地整理方面,德國的城鄉等值化成為了德國農村發展的普遍模式,也是歐盟農村政策的新方向。德國的城鄉等值化不僅對不同類型的土地進行了分類,還采取“開發”和“保護”相結合的方式,保障了農民利益。
總體上看,國外在鄉村建設過程中,經歷了硬性建設過程和軟性建設過程。其中,硬性建設過程是指建設基礎設施、配建公共服務設施等硬指標;軟性建設過程是指建立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制度安排、法律保障。城鄉統籌的核心要義是制度統籌,通過打通城鄉割裂的各種要素,使城鄉要素能夠雙向流動。我國近年來開始了城鄉統籌試點,主要是針對土地這一關鍵要素進行土地制度改革和探索,從社會公平角度提供公共服務均等化和農民權益保障等方面。目前全國各地采取的城鄉統籌的措施有:統籌城鄉戶籍制度(如成都)、發出“農轉城”戶口簿(如重慶)、啟動強鎮擴權(如浙江、山東)、農村集體土地試點建租賃房(如北京)、宅基地換房(如天津)、地票制度(如成都)等。總的來說,國內城鄉統籌還停留在試點階段,與城鄉統籌配套的制度尚在建設中,沒有形成像日本那樣通過法律手段保障農村、農民、農地利益的全面保障制度。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樊綱.城市化: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中心環節[J].政策,2001(10):28-29.
[3]韓俊.城鄉統籌發展中的幾個問題和誤區[J].中國發展觀察,2010(3):7-9.
[4]孫自鐸.試析城鎮化工業化中的土地資本化[J].當代建設,2003(1):4-5.
[5]石憶邵.國內外村鎮體系研究述要[J].國際城市規劃,2007,22(4):84-88.
[6]趙群毅.城鄉關系的戰略轉型與新時期城鄉一體化規劃探討[J].城市規劃學刊,2009(6):47-51.
[7]趙英麗.城鄉統籌規劃的理論基礎與內容分析[J].城市規劃學刊,2006(1):33-36.
[8]張京祥.協奏還是變奏:對當前城鄉統籌規劃實踐的探討[J].國際城市規劃,2010(1):44-46.
[9]李兵弟.城鄉統籌規劃:制度構建與政策思考[J].城市規劃,2010(12):12-17.
[10]王德文,程杰,趙文.重新認識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1(1):34-45.
[11]ISLAM N.The nonfarm sector and rural development-review of issues and evidence[M]//Food,Agri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Discussion.Washington DC,IFPRI,1997:22-23.
[12]BRIGHT H,DAVIS J,JANOWSKI M,et al.Rural non-farm livelihood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and the reform process:A literature review[M].Chatham Maritime,Kent,United Kingdom:Natural Resources Institute,2000:37-43.
[13]HOBBS J,KERR W,GAISFORD J.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ifood Syste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Oxford[M].UK and New York,USA,CAB International,1997.
[14]SWINNEN J,BUCKWELL A,MATHIJS E,et al.Agricultural Privatization,land reform and farm restructur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M].Ashgate:Aldershot,1997.
[15]TANGERMANN S,BANSE M.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Agriculture in an Expanding European Union Wallingford[M].Oxon:CABI Publishing,2000.
[16]CSAKI C,FOCK A.The Agrarian Econom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an Update on Status and Progress-1998 ECSSD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Working Paper no.13.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9.
[17]OECD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Emerg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1999 Paris,Franc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R].1999.
[18]EBRD Transition Report 1999,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R].1999.
[19]王宏遠,樊杰.北京的城市發展階段對新城建設的影響[J].城市規劃,2007,31(3):20-24.
[20]郭建軍.日本城鄉統籌發展的背景和經驗教訓[J].國際農業,2007(2):27-30.
[21]焦比方,孫彬彬.日本的市町村合并及其對現代化農村建設的影響[J].現代日本經濟,2008,161(5):40-47.
[22]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國外城鎮化發展模式[J].小城鎮建設,2005(6):74-76.
[23]李阿琳.日本農村分散集落中小城市的出現及其特征[J].城市規劃,2009,33(5):50-59.
[24]張泉.城鄉統籌下的鄉村重構[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6:43-45.
[25]李水山.韓國新村運動及啟示[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6.
[26]吳自聰,王彩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與國際經驗借鑒——以韓國新村運動為例[J].東北亞論壇,2008,17(1):72-76.
[27]黃建偉,江芳成.韓國政府“新村運動”的管理經驗及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J].理論導刊,2009(4):1-4.
[28]劉英杰.德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政策特點及啟示[J].世界農業,2004(2):36-39.
[29]徐雪林,楊紅,肖光強,等.德國巴伐利亞州土地整理與村莊革新對我國的啟示[J].土地整理與復墾,2002(5):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