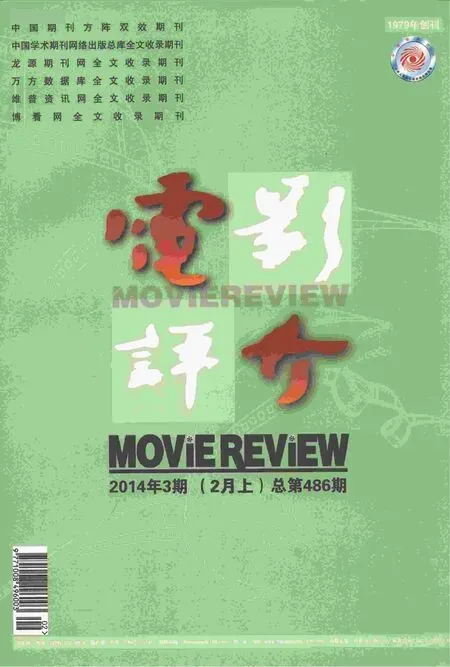論辛棄疾詞的軍事意象及階段性特征
□文/聶琴珍,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

南宋詞人辛棄疾畫像
辛棄疾(1140—1207年),原字坦夫,改字幼安,號稼軒,兩宋詞史上成就卓著的偉大詞人之一。自宋高宗以來,“恢復中原”始終是辛棄疾夜不能眠的終極關懷,愛國詩人陸游曾作詩曰:“君看幼安氣如虎,一病遽己歸荒墟。”(《劍南詩稿》卷十八《寄趙昌甫》)寫出了一位失意英雄的心聲,也是對辛棄疾一生的命運總結。
辛棄疾詞作豐碩,各個階段的經典作品也比比皆是,然而翻閱辛棄疾的詞,可以發現諸如“刀、槍、劍、戟、弓、箭、戈、甲、鐵馬、旌旗、將軍、奇兵等”[1],是辛詞的常客,有著軍事意象的作品占了辛棄疾詞作的一大部分,因為辛棄疾的身份首先是一位軍人,他有著深刻的戎馬經歷,同時濃烈的愛國情懷時刻促使他重上沙場,再建功業。軍事意象繁多成為辛詞的特征之一,本文將著力探索辛棄疾詞中軍事意象的階段性特征。
一、辛棄疾詞中軍事意象的出現及軍事詞創作
(一)辛棄疾詞中軍事意象的出現
詞本產生于閨房之中,描寫對象最初不外乎男女之間的愛恨情仇,以纏綿、溫柔的特點見長。唐五代時,詞多用于遣興娛賓;到柳永、蘇軾時,詞的意象發展到文士的日常生活;南渡時期,詞的意象轉為民族苦難、社會現實生活;到了辛棄疾時,詞的意象又發生了一次大的轉換,戰爭、軍事意象成為了辛詞獨特的藝術風景線。
“腰間劍,聊彈鋏。尊中酒,堪為別”(《滿江紅》)中的“劍”、“鋏”,都是辛棄疾作戰時常用到的兵器,因此也自然成為了辛棄疾抒發壯志的媒介;辛棄疾詞中還常常出現古代歷史人物,其中較多的是三國時期的英雄人物,諸如劉備、曹操、諸葛亮、孫權等,《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中“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描寫的就是胸懷抱負的劉備,而《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描寫的是英雄才俊孫權,辛棄疾將他們作為學習的榜樣,提醒自己要積極進取,建功立業。
辛棄疾顛沛流離的仕途經歷,使他留下了很多懷古詠史的詞作,其中描寫了大量的軍事地點,如《滿江紅·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中“赤壁磯頭千古浪,銅鞮陌上三更月”的赤壁,《浪淘沙·賦得美人草》中“不肯過江東,玉帳匆匆”的江東,都是古時有名的戰爭之地,辛棄疾不僅是文士而且還是一代武將,在他失意難當之時,這些便成了他與夢想交流的平臺。
辛棄疾詞抒情意象的軍事化不僅拓展了詞的境界,擴大了詞的抒情范圍,同時還把男人的壯志豪情引入詞中,“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表現的都是蕩氣回腸的男子風范,從而使豪放詞得以真正興盛起來,成為文學史上寶貴的財富。
(二)辛棄疾的軍事詞創作
辛棄疾仕途上的“失意”沒有實現他成為挽救民族危機的英雄人物,卻成就了他將一腔熱血化為文學上的“英雄感愴”。
1140年至1162年是辛棄疾揭竿而起的少帥時期,辛棄疾與軍事結緣,跟他祖父辛贊有著莫大的關系,其祖父辛贊是金朝的地方官,但常常“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祖父的兵法韜略對辛棄疾的影響很大,由此種下了恢復中原的偉大抱負。
1163年到1181年,辛棄疾官職卑微,但他對政治事業充滿希望和信心。代表作品《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中抒發難以遣懷的不遇之感;《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望飛來、半空鷗鷺,須臾動地鼙鼓。截江組練驅山去,鏖戰未收貔虎”充滿報國心切而現實殘酷的矛盾之情;《滿江紅》“馬革裹尸當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說”以此來鼓勵友人和自己要英勇作戰,不貪戀兒女情長。
1181年辛棄疾被彈劾,曾過了長達十年之久的罷職閑居生活,因此期間多有描寫山野風情之作,但看似閑適自得的田園生活事實上并沒有使他放棄恢復中原的夢想,其詞不時流露出功名未就悲憤和辛酸。《丑奴兒·書博山道中壁》、《八聲甘州》、《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等皆是例證。
1203年至1207年重振雄風的老將辛棄疾再次被彈劾。復國之志破滅,無緣籌措抗金大計的苦悶與痛心是辛棄疾詞此刻最明顯的情感基調,如《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喟嘆;《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人雖老壯心猶在。
二、辛棄疾詞中軍事意象的特征
辛棄疾因其特殊的人生經歷而創作了眾多的軍事戰爭詞作,其軍事詞意象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辛棄疾是一位文武雙全的軍人,擁有一腔愛國熱情,然而卻無端地遭遇貶謫和冷落,在報國無門的情況下,辛棄疾不遺余力地將個人的英雄氣質、戰斗精神滲透到詞的每個角落,其傳奇坎坷的經歷豐富了詞的題材并直接反映到詞的創作里,使辛棄疾詞的創作充滿了現實主義精神,辛棄疾詞描寫的悲憤難當的失意英雄并非文學虛構,恰恰是對自己空有報國之志卻無盡忠之路的真實寫照。
辛棄疾詞不是為了簡單地表現某種情緒而任意構造文學之虛,而是運用比興手法,或委婉或直接地表達壯志未酬的悲憤和痛苦,如《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辛棄疾時任建康江東安撫司參議官,輾轉于小官小職的他,滿腔才略卻無施展之地,進而看“吳鉤”、拍“欄桿”,卻空有抱負。下闋蘊含了三個典故:張翰因思鄉之鱸而棄官南歸、劉備唾棄求田問舍的許汜、晉朝桓溫望樹嘆流年。作者通過這些典故表達出自己進不能、退又不忍的復雜心境。
辛棄疾緬懷歷史英雄人物,是因為現實中的南宋朝廷偷安息武,懦弱無能,與歷史上的那些明主英才形成鮮明的對比,現實中需要這樣的烈士英雄,詞人用古人喚今人,希望朝廷能像歷史英雄那樣戰于城南、復國統一。
(二)雄奇闊大的美學特征
縱觀辛棄疾的軍事詞,不難發現辛詞風格豪邁、雄壯的特點,詞中審美意象多為高聳的山嶺、洶涌的江水,或者杰出的歷史英雄,它們共同的特點是氣勢雄偉、奔放,如《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
“望飛來、半空鷗鷺,須臾動地鼙鼓。截江組練驅山去,鏖戰未收貔虎。朝又暮。悄慣得、吳兒不怕蛟龍怒,風波平步。看紅旆驚飛,跳魚直上,蹙踏浪花舞。
憑誰問,萬里長鯨吞吐,人間兒戲千弩。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馬素車東去。堪恨處:人道是、屬鏤怨憤終千古,功名自誤。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煙雨。”
這是一首錢塘觀潮詞,作者通過“鼙鼓”、“鏖戰”、“貔虎”、“紅旆”,描寫出潮起時氣吞萬里、驚天動地的景象。辛棄疾以其浩邈的情思,深沉博大的審美視野向我們展示了辛詞宏遠的境界和開朗的胸襟,使辛棄疾詞富有雄奇闊大的美學特質。
(三)人物形象的階段性特征
辛棄疾軍事詞中的英雄形象是具有階段性、富于變化性的。
1.少年將帥
辛棄疾二十一歲時就參加了抗金義軍,有著年輕人獨有的膽識與豪情,如《滿江紅·賀王宣子產湖南寇》中“早紅塵、一騎落平岡,捷書急”、“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的才氣和抱負,希望自己能一展宏圖驅逐金兵,此時期的創作盡顯豁達與熱情。
2.勇猛斗士
辛棄疾文武俱全,卻得不到重用,憤懣之情可想而知,但是此時的辛棄疾并沒有因此悲觀,也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如名篇《滿江紅》,是辛棄疾送給好友的勉勵詞。借好友家族英烈勉勵奔赴前線的朋友奮勇殺敵,為抗金事業做出大貢獻,下闋雖寫自己已無用武之地所以只能借酒澆愁,但是詞人并沒有由此消沉下去反而筆鋒一轉,以“馬革裹尸當自誓”來鼓勵友人要英勇作戰,這不僅是對友人的殷切勸勉,同時也是對自己的鼓舞和鞭策。此時的辛棄疾,雖然位卑言微,但是艱難和險阻并沒有打倒這個熱血沸騰、激情昂揚的愛國青年。
3.落寞英雄
辛棄疾42歲時被迫退隱,正是壯年卻閑居山野,失落難當的他對宦海浮沉充滿無奈,對軟弱的朝廷憂慮萬千,雖然自己不在官位,但報國之心仍在,此時辛棄疾詞中的抒情形象由勇猛的斗士轉換為落寞的英雄,《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中“劍”、“吹角”、“連營”、“麾”、“沙場”、“弓”等豐富的軍事意象將詞人渴望戰于沙場、建功立業的心情展露無遺,然而如今的作者只能在夢里盼望馳騁疆場,只能醉眼看劍,心中期待的軍戎生活卻只換來了“可憐白發生”的無限悲哀,詞人想抗金復土,然而此路多艱,幾經波折的宦海生涯,使辛棄疾深感才高遭嫉,惟有全身而退,才能自我保全,詞中不免流露出退隱山林之意,然而抗金統一的夙志仍在他的內心深處回蕩。
4.暮年衰翁
辛棄疾一生都在執著地爭取機會收復失地,然而失望重重。朝廷的棄置不用和怯懦,激發了辛棄疾內心的悲憤,此時的辛棄疾詞成了辛棄疾英雄失路、一生不得志的悲壯凱歌,辛詞中曾經的意氣少年變成了如今的暮年衰翁,作《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時,辛棄疾已是六十六歲的老人,一心報國卻無門。
浩邈深沉的家國憂思以及對山河與百姓的眷戀,是辛詞重要的情感基調,詞中的抒情形象隨著詞人的際遇而變化,但是詞人對于民族前途的深沉憂慮卻不曾因處境的變化而改變。
辛棄疾詞中的抒情形象雖然從少年、青年、壯年到暮年有著不同的坎坷經歷和人生際遇,但是濃烈的愛國熱情和抗金統一的夙愿卻貫穿人物形象的始終。
辛棄疾以一代愛國詞人的高度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文學印跡,從揭竿而起的年輕少帥,到奔走呼號的勇猛斗士,再到賦閑家居的落寞志士,再到重振雄風的暮年老將,坎坷的人生境遇和多艱的仕途使其詞作中的軍事意象也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成功地將濃烈的愛國情懷和悲壯沉郁的人格氣質融解于詞的字里行間。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