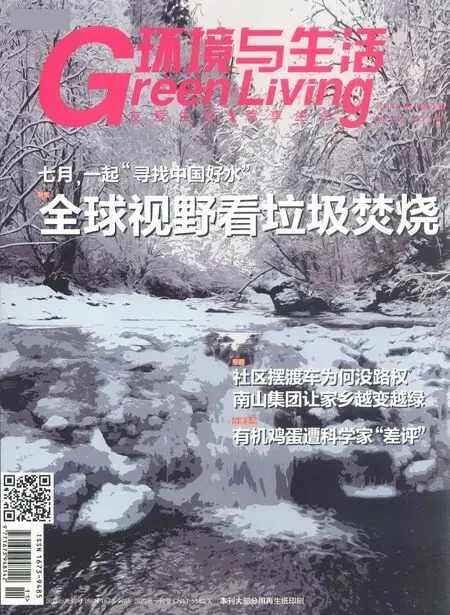我們的環評里沒提“健康”二字
◎呂忠梅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我們的環評里沒提“健康”二字
◎呂忠梅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我從事環境保護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幾年在“環境與健康”立法和推動《環境保護法》的修訂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關于“環境與健康”,我們進行了一些文獻的梳理,還做了社會學的調查,最后以重金屬污染作為研究的一個切入口,我們選擇了鉛和鎘。
從2006年開始,我們對2004年至2013年發生的63件案子做了分析。事件主要發生在我國東、中部區域的農村,其中33件引發了嚴重群體性事件,56件致健康損害,19件涉及健康問題。
要立法,我認為首先要解決以下問題:第一,環境污染對人群健康到底有什么影響?因為立法涉及各種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第二,現行法律能否滿足環境與健康監管的需要?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監管體制?第三,從法律上來講,環境污染物從哪里來?政府應該怎么監管?第四,要進行公共健康干預,涉及政府公共干預措施,還涉及群體的利益訴求,比如發生糾紛時,怎么處理?應該由誰賠償?怎么賠償?
另外,危害還有一個累積性的特點。我們分析的63個案件中,有90.5%都是累積性的污染。以什么標準來判斷?事件爆發后處理方式是否合適?這都是法律要面臨的問題。另外,損害賠償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確定因果關系。從法律上講,必須找到因果關系才能夠決定誰來承擔法律責任。但是,像重金屬污染這樣復雜的因果關系如何確定?這也是目前世界上面臨的難題。
環境與健康問題,最重要的是建立風險管理機制。但是,我們的法律制度恰恰沒有風險管理。我們的環境評價制度里,“健康”二字提都沒有提,只評估新建項目對環境的影響,并沒有評估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說明我們的環境標準體系還不盡科學,沒有真正把人體健康的標準作為環境保護標準的一項核心內容。此外,從執法手段上看,現在各個部門的信息也還沒有實現共享。
最后是環境責任追究,責任方到底要賠多少錢?我們統計了1000多件環境案件的司法判決結果,發現受害人能勝訴的非常少,勝訴也只賠償直接經濟損失。直接經濟損失是什么?比如死多少魚就賠這些魚的錢,人受害了只賠醫療費、誤工費,以及一點營養費,別的就不賠償了。受害人并沒有得到合理的賠償。
我們還面臨以下問題。第一,環境與健康監管體制難運行,管理手段不能適應風險管理需求,公眾參與嚴重不足,“有牽頭無統籌,各干各的”。我們去縣一級調查,發現衛生部門根本不管環境與健康的問題,只管“看病難看病貴”,健康問題歸誰管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到環保部門,環保部門說歸衛生部門管。第二,現有的管理手段不能適應風險管理的需要,只等到出很嚴重的污染事件了,才成立領導小組,開展調查。
另外,一旦出了嚴重污染事故,往往找不到問責主體,因為沒有環境監測機制。結果往往是“企業污染,百姓受害,政府買單,最后誰都找不著”。信息不公開也是一個問題,發生事故以后要不要告訴公眾?一些項目有健康風險,上馬前要不要告訴老百姓?我們去多個部門調查,都說不能告訴。為什么?因為一告訴就要鬧事。但是,這種封閉的管理模式能解決問題嗎?
最后,事故發生后,通常有十幾份鑒定書,五花八門,這是因為我們在污染危害健康的事件處理中缺乏技術保障。要解決以上問題,個人認為我國必須制定一部專門的環境與健康法,現在全世界只有一部環境與健康法,是韓國制定的。
本欄目責編/鄭挺穎 zhengtingying@vip.163.com

(朱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