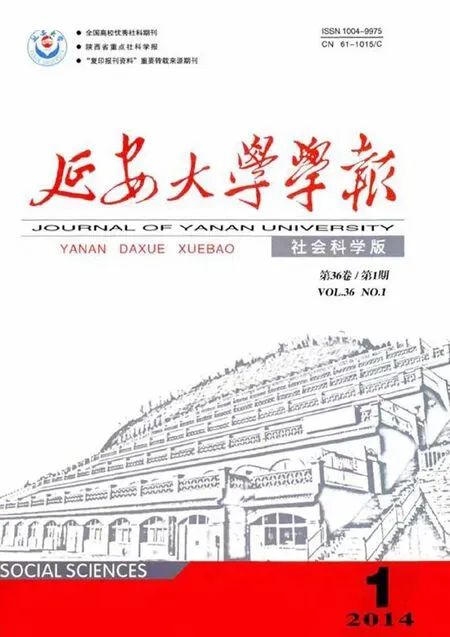朝鮮王朝對清觀解構分析
季 南
(延邊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吉林 延吉133002)
對朝鮮半島的歷史文化特別是中韓關系方面的研究成為中韓建交后學界研究的熱點,尤其是清鮮關系更是備受關注。中外學界從封貢體制、朝貢貿易、對外政策、文化交流等角度出發深入探討清鮮關系,其中朝鮮對清朝的文化心態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化心態影響著朝鮮的對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響著清鮮關系的發展變化。朝鮮王朝對清觀經歷了一個由蔑視、抵制到逐步認同接受的過程,本文跳出朝鮮王朝對清觀嬗變研究的窠臼,從正統意識結構、民族意識結構、復仇意識結構出發解構分析朝鮮王朝的對清認識,以期為朝鮮王朝處理對清關系時的種種表現找到依據。
一、正統意識結構
正統論源于儒家的大一統思想,是困擾著中國歷代王朝的核心觀念并且是政治家和學者們長期關注的問題。割據、篡奪、夷狄之國皆被視為“不正”,尊王和攘夷思想構成正統論的理論基礎。朝鮮王朝的正統意識來源于中國的正統觀念。朱云影曾說“李朝約五百年間,朱子學說始終維持無上的權威”,[1]而朱子正是高舉華夷之辨提倡尊王攘夷的旗手,熱衷于從春秋大一統觀念出發評判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的正統性問題。在朱熹看來,只有漢族建立的長期穩定的大一統政權才具有正統地位。朝鮮的儒學者繼承并發揚了朱熹的正統觀。
朝鮮大儒成海應(1760-1839)曾說中國自春秋以來,“得天下之正統者,唯漢、唐、宋、明四朝”,同時也指出“唐高祖值隋主失德,生靈涂炭,舉兵而聲其罪,吊其民可也。乃為裴寂等所誑,出師既茍且,又立代王侑為天子,自以為禪授”,[2]同樣也是篡奪,不能稱為“正”。宋太祖出師陳橋,在諸將的擁戴下而立,“露刃犯闕,扼幼主而奪其位”,也是篡奪,同樣也稱不上“正”。那么“得正統”的漢、唐、宋、明四朝中也只有漢、明得天下而無疵議。與漢朝比較起來,“皇明之世,閨門正于上,權柄不移于下,將帥不敢恣,直士奮舌強諫,朝廷清明純粹,比漢又過之”。[2]在他看來,漢代以后的魏、晉、宋、齊、梁、陳各朝都是篡奪而來,更不能稱為“正”,“不正者雖得以威力強服之。人不戴之。天亦與之而不終……自三代以來,居天下之正者,皇明也。合天下之統者,亦皇明也。夫正統者,有名有實者也”。[2]只有明朝才是成海應心目中名正言順的正統王朝。成海應生年,清入關幾乎百年,還在肯定大明王朝的正統,無疑是在否定清朝的正統性。
朝鮮王朝晚期的性理學家柳重教(1832-1893)也專門作《正統論》,依據朱熹《通鑒綱目》評判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問題,認為三代以上“以圣神之德,膺天命建民極,蒞中國而撫四夷,其子孫世襲大位累百年,而天下無異志”[3]的王朝是真正的大一統;六朝“未及混一天下之時是也,于其中名義有正有不正,生于其世者,擇而事之”,[3]東周、蜀漢和東晉“為亂賊所割據,夷狄所侵奪而不能一”[3]是統之卻不能一;滿清王朝是“亂賊之竊居大位,夷狄之冒據中國,其統之非不一矣,而斷之以名義,則偽而非真,僭而不正也”,[3]所以“國人士大夫守其義者,舉有不欲西向而坐之心,至今重三百年猶以皇明舊君為君,以俟天下義主之興”。[3]
朝鮮儒林諸多關于中國歷代王朝正統論的討論,最終目的卻都是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統地位。這些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議論,而是支配著朝鮮統治階層處理與滿清王朝雙邊關系的思想情感,并希望這種情感一代代地傳下去。在正統意識的支配下,朝鮮君臣通過筑壇建廟、祭祀明朝皇帝、優待明朝人后裔、尊崇祭祀中國的忠臣義士、珍視明朝的舊物舊制、編修各種史書等方式凸顯其尊周思明的正統意識,尤其是在對待藩屬國臣服的重要表征的正朔問題上,朝鮮對奉行清朝正朔始終不是心甘情愿。即便在清鮮關系總體上穩定的英祖時期,很多場合仍然堅持奉明正朔。在祭祀上,除了宗廟和文廟祭祀采用清朝年號之外,其他的祭祀活動都以明朝年號或“崇禎后幾年”代之。比如英祖六年(公元1730年),祭祀諸葛武侯、岳武穆王時,英祖下令“勿書雍正年號”。[4]英祖十年(公元1734年),英祖許可新建的昆陽兩胎室表石書“崇禎紀元后幾年干支月日書刻”。[4]英祖二十八年(公元1752年),英祖為孝純賢嬪制的志文最后書以“時,皇明崇禎紀元后百二十四年予即阼二十七年仲冬識”。[4]在對忠臣義士進行表彰時,為表明對忠臣義士的品行的認可,教旨和祭文上也不寫清朝年號。英祖十一年(公元1735年),英祖對已故的崇尚義節的處士追贈三品,并教旨“勿書清國年號”。[4]為了褒獎忠臣義士,英祖在明朝滅亡一百二十周年之際為明朝援鮮的移民后代以及抗清義士的后代特設忠良科,及第者的紅牌都不書清朝年號,只書某年某月。英祖四十六年(公元1770年)、四十八年(公元1772年)、四十九年(公元1773年)、五十一年(公元1775年)的忠良科也都遵循英祖四十年(公元1764年)的舊例不書清朝年號。對于秉持春秋義理正統觀念的朝鮮儒士來說,崇禎、永歷已不單純是明朝的兩個年號問題,而是具有更深層的象征意義,身處清朝,卻始終或明或隱地使用已故王朝的年號無疑是對新朝的否定,同時也正是朝鮮君臣正統意識的反映。就連主張北學清朝的北學派人物在使用年號問題上也堅持使用崇禎紀年。樸趾源在其《熱河日記序》中點出了使用崇禎紀年的用意:“曷私稱崇禎?皇明,中華也,吾初受命之上國也。崇禎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三十余年,曷至今稱之?清人入主中國,而先王之制禮變而為胡,環東土數千里,劃江而為國,獨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猶存于鴨水以東也,雖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肅清中原,以光復先王之舊,然皆能尊崇禎以存中國也。”[5]朝鮮曾以“小中華”自居,自認為是中華正統的承繼者,從而顯示其與周邊國家文化上的差距,遵行崇禎紀年也正是為了保存中華文化。對于朝鮮使用明朝年號柳重教有如下闡述:“吾東士大夫今用皇明年號,其意蓋曰:既不可以夷狄為君,又不可以一日無君,仍以舊君為吾君,以俟天下義主之興爾。”[3]清朝雖一統中國,但卻不是朝鮮君臣心中的“義主”,朝鮮君臣“仍以舊君為吾君,以俟天下義主之興爾”。
事實上,滿清帝王在正統問題上也在做著各種努力。例如,多爾袞死后,即位的順治皇帝就在有意識地為成為符合“中華道統”的圣君明主不斷努力,他所關心的是使自己的統治合天意、順人心,加強清政權漢化、華化以及儒化程度,縮小清王朝與明王朝以及中國歷史上漢人建立的諸多王朝之間的差異。順治皇帝對儒學儒術表示贊賞:“上之賴以致治,下之資以事君”,[6]并要求學官諸生當共勉。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三月所下的詔書更彰顯了其推行儒化的決心:
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弗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儒術,以開太平。直省學臣,其訓督士子,博通古今,明體達用。諸臣政事之暇,亦宜留心學問。[6]
順治皇帝還編纂推廣宣揚儒學儒術的書籍,推行儒化教育,在施政過程中“化民以德,齊民以禮,不得已而用刑”,[6]推行仁政,使那些漢族儒臣在其身上看到了儒家理想政治的希望。但朝鮮人對滿清統治者所做的努力顯然是不領情的,雖然禮儀上不得不對清朝行事大之禮,但在政治上和思想情感上依然不能接受滿清人是中華的正統。
就在順治皇帝努力證明清王朝的正統地位的同時,高舉“反清復明”旗幟的朝鮮人宋浚吉(1606-1672)對清王朝的“正統”提出了挑戰,主張和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權建立關系:
恭惟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開辟以來,亦未聞于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真是誠痛切語也……竊聞帝室之胄,尚有偏安于廣、福之間,天下大統,不全為魏賊之所竊,而我國漠然不得相聞,于今幾年……今殿下聿追先態,奮發圖功,日夜俟天下之有事——而彼此形勢,亦已為天所厭,實為難久之兆……[7]
在宋浚吉看來,滿清王朝有如三國曹魏一樣,不是承繼天下之大統者,當然也不是“帝室之胄”,且“已為天所厭”,氣數將近。
春秋大一統的正統觀念深植于朝鮮君臣心中,也正是基于這種正統意識,朝鮮君臣有尊周思明的種種舉動。他們通過建大報壇崇祀明朝皇帝,表彰明朝援朝義士及其后裔,在祭祀、私人信件、碑銘中暗行明朝年號,以此表示對清朝的反抗,并彰顯在他們心目中正統存于明朝。朝鮮自我定位為“小中華”,是明朝正統文化的承繼者,從而顯示正統存于朝鮮。朝鮮多次討論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問題,卻幾乎不談自身的正統問題,因為作為藩屬國,它的正統性往往是通過“上國”的確認體現的。清朝的前身是興起于建州的女真,只不過是明朝的藩屬國,竊據權柄乃以下犯上,有違春秋大義。也似乎只有通過強化與明朝千絲萬縷的關系才能解決朝鮮內心的正統危機。南明政權滅亡后,正統無以為繼,朝鮮將存明朝正統作為一種使命和責任,建大報壇正是這種使命感、責任感驅使下的具體行動。通過祭祀明朝皇帝的方式,證明朝鮮承接了明朝正統。正如吳慶元在《小華外史》中說的那樣:“興廢系乎天時,義理根乎忍心,故天時或與人違,而義理無時可熄。今此中國之淪為夷狄,天時之舛也。尊周而攘夷,內華而外夷,人心之正也。今自永歷壬寅,皇統雖絕,其后四年已有我東建廟之議。遂設壇而祀三皇,三皇陟降洋洋在上。于是乎已晦之日月復明于一隅青邱,既絕之皇統長存于數尺崇壇。則天意人心不歸于此,而將奚適也”。[8]
二、民族意識結構
關于朝鮮王朝對滿清統治的敵視和抵制,學界很多研究都從華夷觀的角度尋找原因。華夷觀與正統論密不可分,華夷之辨成為判別中國歷代王朝是否正統的基本原則,即“夷狄之國為不正”。[1]中國傳統的華夷觀,在地理位置上將中國置于中心,外圍的皆稱為夷,出現了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的局面;在文化上,華夏文化是優于夷狄文化的先進文化,華夏的儒家文化可以影響甚至改造夷狄文化。夷狄文化為了改變自身的落后面貌自覺地接受華夏文化的熏陶、浸染甚至改造。在朝鮮人心目中,朝鮮是夷,但卻是不同于其他夷狄的“夷”,因為在接受華夏文化浸染的諸夷當中只有朝鮮完成了從夷到華的蛻變,“華夷自有界限,夷變為華,三代以下,唯我朝鮮,而得中華所未辦之大義,獨保其衣冠文物,則天將以我國為積陰之碩果、地底之微陽”。[9]在滿清入主中原后,朝鮮不僅僅強調自己是“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10]的“小中華”,而是以中華正統的繼承者自居,“我東之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諱哉!素夷狄行乎夷狄,為圣為賢,固大有事在,吾何慊乎!我東之慕效中國,忘其為夷也久矣”。[11]近代性理學家崔益鉉有段跋文明晰地交代了朝鮮由夷到華的蛻變過程:
或曰吾東亦夷也。以夷事合于中國之正史,有例乎?曰: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意也。況吾東箕子立國,革夷陋而為小中華,后雖中微,而貿貿始自高麗,已骎骎有用夏之漸,所以風俗好見稱于朱子也。至于本朝則得復小中華,而崇禎以后,則天下欲尋中國文物者,舍吾東無可往,實所謂周禮在魯也。[12]
在崔益鉉的眼中,中華正統在滿清王朝已不存在,而朝鮮在完成由夷到華的蛻變后成為中華正統唯一的承繼者。
朝鮮除了文化上的優越感外,更多地在“華夷觀”中注入民族差異的內容。正像韓東育先生說的那樣“華夷”理念給東亞地區帶來過文明,也播撒下了“自民族中心主義”[13]的種子。秉持“自民族中心主義”的民族,以自身族屬的標準來判斷他者族屬,認為自身族屬在所有方面或若干方面都優于他者族屬,對他者族屬不能全面客觀地認識,并欠缺對他者族屬的關心,對他者族屬持有敵意。在朝鮮人的心目中能夠代表中華文化的只有漢族,無論契丹、蒙古還是女真都是夷狄之輩。對于中國歷史上這些非漢族統治下的王朝,朝鮮也是持排斥態度的。高麗太祖訓誡“契丹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制度,慎勿效焉”。[14]對于蒙古也是“猜忌莫甚,雖和之,不足以信之,則我朝之與好,非必出于本意”。[14]對于崛起于偏遠建州的女真,朝鮮同樣沒有打破固有的偏見而是將其深深打上夷狄的烙印。
朝鮮與女真淵源很深,如果要給兩者確定一種關系,那就是“不完備的封貢關系”。[15]因為女真向朝鮮貢獻方物,而朝鮮對前來納貢的女真首領和隨從賜予官職,雙方有朝貢冊封的事實行為,符合“封貢關系”的基本條件。朝鮮是明朝的藩屬國,而女真則是明朝邊疆的少數民族,二者之間雖有朝貢冊封之行為,但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主國和藩屬國的關系,并且朝鮮對女真部落首領進行冊封也是實施羈縻政策的一種手段,“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職者,非欲侍衛者,欲羈縻也。又國初萬戶宣略將軍之職,不惜遙授,亦欲羈縻也”。[16]朝鮮建立之初,太祖量授萬戶、千戶之職,使李豆蘭招安女真。1394年,太祖又授予前來朝貢的女真斡朵里部酋長萬戶、千戶、百戶等職位。后太祖又以斡朵里猛哥帖木兒為上護軍,授慶源等處管軍萬戶印。除了考慮女真作為“藩籬”的地緣政治因素外,朝鮮從軍事、經濟的角度與女真展開邊境互市貿易。比如從女真輸入馬匹以補充軍事需要,提高軍隊戰斗力;從女真貿來貂皮以滿足朝鮮貴族對奢侈品的需求,但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朝鮮手里,是否開市、開什么市,完全出于對朝鮮自身需要的考慮。
女真部落在發展初期,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發展程度較低,生產生活資料匱乏,溫飽難以解決,于是建州衛李滿柱、猛哥帖木兒、董山以及野人女真都曾多次親自或者派人到朝鮮納貢,以此獲得朝鮮方面豐厚的回賜。在女真與朝鮮行朝貢冊封之實的過程中,女真是受益的,所以也樂于接受朝鮮的羈縻政策。16世紀末,努爾哈赤抓住戰機完成了對女真各部的統一,但文明程度和社會發展程度仍遠遠落后于朝鮮。朝鮮對女真的態度仍然是存有偏見和鄙夷,但努爾哈赤的崛起引起了朝鮮的警覺。當女真勢力強大后,也想盡快扭轉與朝鮮交往中的被動局面,在發展雙方關系時爭取平等性。比如在壬辰倭亂之際,努爾哈赤統一的建州女真就曾聯絡朝鮮政府表達了要幫助朝鮮御倭的愿望,但朝鮮得此消息后卻十分驚恐,認為努爾哈赤的示好是另有圖謀,所以朝鮮宣祖國王委婉地予以拒絕。時隔不久,出于自身的安全考慮努爾哈赤又向明朝表達了“愿揀精兵,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奴,報效皇朝”[17]的愿望,朝鮮得此消息致書明朝,請求明朝禁止努爾哈赤出兵。
朝鮮不但拒絕了努爾哈赤援朝抗倭的好意,而且策劃“借倭伐胡”。1593年,連年遭遇糧荒的女真易水部越境搶掠朝鮮民眾財物,朝鮮派兵鎮壓,遭到了女真的頑強抵抗。正當朝鮮器械殆盡,御敵無策之際,朝鮮密發六鎮兵馬,以降倭為先鋒突襲女真駐地,朝鮮對此不以為恥,反而認為一雪前恥。這種行為進一步激化了朝鮮與女真的矛盾,也充分展現了朝鮮嚴重的民族偏見。
努爾哈赤援朝抗倭的請求被拒絕,反而獲得了發展壯大的機會,經濟、軍事實力都大大提高。1616年,以赫圖阿拉為首都,努爾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權。這個以“小中華”自居并沾沾自喜的朝鮮王朝,在心理上將自己置于“小天朝”的中心,滿足于“野人、倭人俱我藩籬,俱我臣民,王者等視無異。或用為力,或用為聲,不可以小弊拒卻來附之心”[18]的虛榮。對“禽獸之性,非可以德化”[18]的女真建立的政權,朝鮮在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即便經過“丁卯之役”、“丙子之役”,屈服于武力壓迫與清朝建立起宗藩關系,但對這個“犬羊”之國的統治朝鮮是不予以承認的。他們對清人施以“胡”、“虜”、“犬豕”等侮蔑性稱呼,并認為清人入主中原后使中原淪為腥膻污穢之地,尤其是清人下令改變冠服制度,無疑是對中華禮儀和正統的破壞,因為冠服可以“布文章、正等位、秩上下、裨貴賤”,[2]但清朝卻要求“辮發左祍,服馬蹄袖,戴絨帽”,[2]“壞堯舜以來上衣下裳之制,使天下泯然皆為羯,莫克自異,天下之變極矣”。[2]《小華外史》的作者吳慶元自比胡銓、魯仲連,以與夷狄為伍為恥,拒絕向滿清統治低頭,曾有如下言論:“皇綱不振,夷狄生心,羊狠狼貪,共噬中原。以我殿下之智,挾三韓之眾,屈身卑心欲拜于禽獸之徒,而君臣不言其非,臣且痛之,宋主事金而胡銓爭之,六國帝秦而魯連恥之,臣今日之志不在胡銓魯連之下”。[8]
對于這樣的夷狄之國建立起來的政權,朝鮮王朝充滿了詛咒和詆毀,總是希望它的統治早日敗落。在這種思想感情的驅使下,朝鮮使臣擔負起了搜集中國情報的任務。這其中自然交織著兩條互相矛盾的路線:一條是盡量反映清朝國內現狀的信息,另一條則是不可避免地夾雜在情報中的朝鮮使臣個人的主觀愿望和價值判斷以滿足對清朝固有的偏見,在這樣的滿足中,對清朝的仇視和鄙薄發揮得淋漓盡致,以此證明朝鮮自身的正統性和其軟弱的合理性。朝鮮使臣認為清朝皇帝尤樂游宴、奢侈無度,清朝臣子無不行賄,再加上蒙古作變,他們斷定清王朝即將敗落,還分析康熙皇帝對待漢族的苛政,判斷清王朝所存的危機,甚至將種種“天變”看成是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征兆。對于這種不符合實際的清朝即將滅亡的情報,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和懷疑,反而被朝鮮君臣津津樂道。對滿清的深深厭惡以及敢怒不敢言的無耐使朝鮮人固執地將邪惡、滅亡和清王朝的統治聯系在一起,滿足了朝鮮不正常的政治心理需要。
三、復仇意識結構
除卻受春秋大一統思想影響的正統論意識以及灌注進“自民族中心主義”的夷狄情結外,朝鮮人對滿清人還有著刻骨的仇恨。這固然與皇太極丁卯、丙子兩征朝鮮,迫使朝鮮與之訂立城下之盟,以武力征服的手段與朝鮮確立宗藩關系,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使朝鮮人受到重創脫不了關系。尤其是三田渡盟約之后,清軍長達兩個半月的滯留,任意搶掠,俘虜了不少朝鮮人,后又將這些“戰利品”在沈陽拍賣,這更增加了朝鮮對清朝的仇恨,以至于孝宗國王要“替天行道”,積極主張北伐,朝鮮人甚至對吳三桂的叛亂、鄭經的反清活動都抱有幻想。如果要對這種行為找到理論依據的話,那就是在春秋時期復仇的責任和理念累積演變下經《春秋公羊傳》的闡發而逐漸形成的系統化的“大復仇”學說。
《春秋》“大復仇”學說對后世影響極大,尤其是在北宋徽欽二帝被俘,趙宋政權南渡的情況下,漢儒極力倡導復仇乃春秋大義。南宋也始終沒有擺脫金的蹂躪踐踏,攘夷的大旗在南宋也始終被高舉。朱熹就曾數次上書講復仇攘夷,“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轉出于一己之私也。恭維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仇,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19]對于金兵俘虜徽欽二帝這種不共戴天之仇,決不可通過議和來解決,而是“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致勝”,要“內修政事,外攘夷狄”。[19]《春秋》“大復仇”學說以及朱熹復仇雪恥的主張深深影響著朝鮮人。曾遭遇康熙朝文字獄迫害的戴名世在筆記《八月庚申及其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中說:“今夫《春秋》之義,莫大于復仇,仇莫大于國之奪于人,而君父之死于人也。故吾力能報焉,而有以洗死者之恥,上也;其次,力不能報,而報之不克而死,最下則忘之,又最下則事之矣。”[20]正是基于這種復仇意識,朝鮮人是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對“夷虜”之人建立的王朝進行報復。
隨昭顯世子入質于沈陽的鳳林大君(后來的孝宗國王),“及入燕,清人以金玉、彩帛遺昭顯及王(指鳳林大君),王獨不受,頗以我人之俘虜者代之”,[21]他主動與清人劃分界限,不像昭顯世子那樣用聲色犬馬磨光了自己對清人的仇恨,而是隱藏自己的反抗情感。他不輕易接受對方的饋贈,也沒有因為受到滿清統治者的禮遇和冊封而改變對清朝的態度,反而對清朝充滿了仇恨。孝宗國王“誕降之夕,彩云呈瑞。既生九歲而遭丁卯之難。十七歲而母大妃薨,哭泣悲哀,庭中不忍聞。十八歲而遭丙子之難,入于江華。十九歲而丁丑正月,得朝仁祖于南漢之城下,仍質于沈陽。既而西至于蒙古界,南至于山海關,又南至于錦州衛、松山堡,見諸敗將。又東至于鐵嶺衛、開原衛,又東北至女奚部,鑿玄冰丈余而飲其水。二十六歲而居北八年,始東歸。未數月旋入燕山,見京邑灰燼。二十七歲乙酉自燕山歸國。前后二十七年之間,天之憂戚玉成者靡所不至”。[22]八年的質子生涯和坎坷經歷使孝宗對清朝的仇恨是刻骨的。這位皇帝在朝鮮“義理派”的挾持下,逐漸走上了反清復明的道路。孝宗為“北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位之初就大量啟用新人,斥退親清舊臣,并積極擴軍備戰,御營廳軍和禁軍數量都有所增加,并針對對清作戰特點將其改為騎兵,改造原有武器裝備,盜賣硫磺,增加戰斗實力,并加強邊塞防御體系。孝宗將興兵北伐視為“申天下之大義”,[22]曾在與心腹大臣宋時烈密談中提到:
大義既明,雖使社稷滅亡亦有光于天下萬世,何愧之有哉?天意于我不邈然,庶無滅亡之虞也。……群臣無可與謀事者,余今年且四十余矣,十年之中大事不成,則寡人志氣寢衰,雖欲平定中原不可得也。卿宜興同志之士密謀之。[22]
此番密談還未付諸實踐就伴隨著孝宗的次年離世而消歇了,但卻反映出孝宗強烈的復仇心態。
肅宗國王即位之時,清朝發生了三藩叛亂,朝鮮君臣又認為此時是復仇雪恨的大好時機,已經漸漸消聲的“胡五百年之運”的反清意識再次得到強化。尹鑴也是北伐的積極倡導者,顯宗在位時就曾慷慨激昂,上密疏建議顯宗“替天行道”:
臣聞除天下之憂者,必享天下之福;持天下之義者,必受天下之名。其道在因時乘勢,審其機而亟圖之。
嗚呼!丙丁之事,天不吊我,禽獸逼人,棲我于會稽,厄我于青城,虔劉我赤子,毀裂我衣冠——當是時,我先王忍一死為宗社,捐一恥為萬姓;而沬血飲泣,含羞拊心,思一有所出,以至于今,天道累周,人心憤盈矣!
今日北方之聞雖不可詳,丑類之竊居已久,華夏之怨怒方興。吳起于西,孔連于南,韃伺于北,鄭窺于東。剃發遺民,叩胸吞身,不忘思漢之心。側聽風飚之響,天下之大勢可知也已。
我以鄰比之邦,處要害之地,居天下之后,有全盛之形,而不于此時興一旅,馳一檄,為天下偈,以披其勢,震其心,與共天下之憂,以扶天下之義,則不徒操刀不割,撫機不發之為可惜。實恐我圣上其承之心,無以奏假于我祖宗我先王,而有辭于天下萬世矣![23]
尹鑴此封密函反映出其特有的思想感情結構:將滿清人視為“禽獸”、“丑類”,這些“禽獸”非中華正統,而是“竊據”,對丙、丁之事耿耿于懷。清朝國內的不穩定,使這些具有儒家慣性反應模式的“義理派”不能正確認識客觀形勢。顯宗國王有鑒于孝宗反清的不了了之,始終沒有反清的行動。
肅宗即位之初,尹鑴又上疏申明復仇雪恥大義。他將興兵北伐、渡海通鄭、與北絕和視為國家面臨的三件大事。即便耿精忠、尚之信都已紛紛投降,尹鑴仍然鼓動肅宗北伐:“清人與吳三桂相持已累年矣。天下中分,干戈搶攘,國內虛耗,兵民愁怨。我以全盛之國,士卒精銳,當此之時,聲大義,率大眾,乘虛直搗,則乃彼國滅亡之日也”。[24]
正當肅宗國王和朝臣認為清朝天下將亂而寄希望于吳三桂時,這個十幾天前才稱帝改元,以衡州為定天府的吳三桂還沒來得及北向,就死于永興了。于是朝鮮“義理派”和“主和派”又寄希望于鄭成功的兒子鄭經。朝鮮人希望鄭經和對馬島的反清聯合艦隊可以形成,領議政許積甚至下令為日本人和鄭經利用濟州這樣的口岸提供方便,兩方的艦隊或聯絡人員可在此休息、取得補給,“既捉漢人,則不可入送北京”,[24]并對遭遇困難的人提供幫助,甚至“惟故失一船,容彼竊吉,佯若不知可也”。[24]肅宗國王對許積的命令照準。這樣做,朝鮮朝廷是很被動的。如果將濟州的情況如實向清廷報告,那么清廷定會要求把斥清分子遞解回國,這是朝鮮君臣不愿為之的,如果對入濟州的漢人和日本人置之不理,那么清朝方面的“勘罪”麻煩會接踵而至。事實上對濟州海面的情況,清朝方面是知曉的,比如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清朝派使者二人曾到朝鮮頒布詔書,傳達兵部、禮部風議,并明言如果朝鮮有請求發兵的請求,清朝的精兵朝發夕至。朝鮮對此感到忐忑,因為此次清使頒詔很可能是清朝對朝鮮暗通鄭經的警告。
清朝成功平定三藩之亂,并成功收復了臺灣,使鄭氏堅持了六十多年的反清復明大計化為泡影。朝鮮也不得不從“胡無百年運”、“不久將亡”的幻境中清醒過來,重新認識這個正在中國每一個角落發揮作用的滿清王朝。在“天朝禮制體系”下恪守番邦之禮。但即便如此,復仇的心態和反清的情緒一直留存在朝鮮人心中。
四、結語
我們常談到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包含觀念上層建筑和政治上層建筑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制約。朝鮮王朝對清觀屬于觀念上層建筑,它影響著朝鮮王朝各個時期的對清政策。儒家的春秋正統觀、大復仇觀與朝鮮的民族意識交織在一起,內化為朝鮮人心中揮之不去的情結。在正統意識的支配下,朝鮮君臣通過筑壇建廟、祭祀明朝皇帝、優待明朝人后裔、尊崇祭祀中國的忠臣義士、珍視明朝的舊物舊制、編修各種史書等方式凸顯其正統意識,對奉行清朝正朔始終不是心甘情愿。在民族意識支配下,對“禽獸之性,非可以德化”的女真建立的政權,朝鮮在心理上不予以接受,并固執地將邪惡、滅亡和清王朝的統治聯系在一起,以滿足其不正常的政治心理需要。在《春秋》“大復仇”學說的影響下,朝鮮期待一次又一次機會:孝宗計劃北伐,肅宗時期北伐論再次被強化。雖然清朝的統一和強大使朝鮮一個又一個復仇幻夢化為泡影,他們不得不正視現實,調整心態,從而調整對清政策,但這個調整的過程是漫長的,也是痛苦的。
[1] 朱云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08,178.
[2] [韓]成海應.研經齋全集[A].韓國文集叢刊:第274冊[C].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影印標點本,2001.
[3] [韓]柳重教.省齋集[A].韓國文集叢刊:第324冊[C].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影印標點本,2001.
[4] 朝鮮王朝英祖實錄:第42冊[M].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編縮版,1970.
[5] [韓]樸趾源著,朱瑞平校點.熱河日記[Z].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6] 趙爾巽,柯劭忞,等點校.清史稿:第2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7.130,141,134.
[7] 朝鮮王朝孝宗實錄:第36冊[M].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編縮版,1970.120.
[8] [韓]吳慶元.小華外史:下冊卷七[M].首爾:漢城朝鮮研究會,1914.200.
[9]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46.
[10] 朝鮮王朝成宗實錄:第8冊[M].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編縮版,1970.670.
[11] [韓]洪大容.湛軒書[A].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602冊[C].漢城:景仁文化社,1998.256.
[12] [韓]李恒老.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Z].漢城: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本,2011.1412.
[13] 韓東育.“華夷秩序”的東亞構架與自解體內情[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45-54.
[14] 高麗史:第2冊[M].漢城: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線裝.32,60.
[15] 陳放.朝鮮與女真、滿族諸政權關系變遷研究[D].延吉:延邊大學,2012.
[16] 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第2冊[M].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編縮版,1970.414.
[17] 朝鮮王朝宣祖實錄:第21冊[M].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編縮版,1970.544.
[18] 朝鮮王朝世祖實錄:第7冊[M].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編縮版,1970.
[19] 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508,768.
[20] [清]戴名世撰,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9.
[21] 朝鮮王朝孝宗實錄:第35冊[M].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編縮版,1970.365.
[22] [韓]朝鮮正祖李祘敕輯.尊周匯編:第三冊[M].漢城: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線裝.
[23] 朝鮮王朝顯宗實錄:第37冊[M].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編縮版,1970.68.
[24] 朝鮮王朝肅宗實錄:第38冊[M].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編縮版,1970.372,319,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