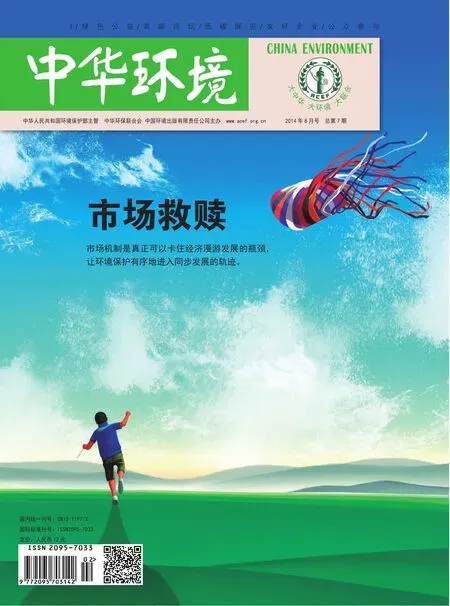慈善不該是一場“達人秀”
邵聰慧
慈善不該是一場“達人秀”
邵聰慧

7月1日,在遼寧省撫順市,陳光標將自己在美國接受采訪的報紙祭獻到雷鋒墓前。
中國的慈善究竟該往哪里走?陳光標曾經覺得應該為中國慈善事業做點什么了,于是就有了他在發達國家高調亮相的做派。
2014年7月6日,陳光標稱:聯合國頒給我“世界首善”榮譽稱號。僅不到24小時后,陳光標又表示:“我的‘世界首善’稱號可能是受騙了,我辦這個證花費三萬美金。”7月9日,陳光標和辦“假證”的基金會,兩方網絡喊話,相互指責。陳光標在微博上曬出了他和辦“假證”的“中國全球合作基金會”的微信對話,說自己被騙,要委托人去美國報警。不過詭異的對話中只有對方,卻看不到陳光標說了什么。給陳光標辦假證的“中國全球合作基金會”則發表聲明說:陳光標早知道他們不代表聯合國,“假證”是陳光標自己做的。
之前,陳光標在接受國內某媒體采訪時還說,自己獎狀、獎杯拿了4000多個,還有3萬多條哈達,接近兩萬面錦旗……每個(獎狀)后面都有一個故事。
這些不靠譜的事情與數據,如果換在一個正常人身上,估計會在網友的罵聲中走上天臺,不過,對于陳光標來說則不同。他的種種行為,正是以慈善的幌子為自己搭建秀場,利用“眼球效應”為自己的事業帶來正向的助推力。
陳光標的慈善事業起步于1998年,至今已有十幾年時間,據稱,在這期間他累計捐獻款物約30億元人民幣,幫助特困戶逾百萬。但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資深慈善家陳光標似乎還“稚嫩的很”,他的事業“并沒有走出多遠”。
比爾蓋茨宣稱將捐獻全部遺產用于慈善時,人們吃驚的不是他的巨額財富將會讓多少窮人受益,而是他的慷慨顛覆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財富觀,從而造就出一個更為專注的慈善群體。
這一評價的得出,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對他慈善行為模式的不認同。因為,個人名義下的“大禮包”、“大紅包”幾乎成了陳光標式慈善的“行為藝術”—— 2011年3月11日,陳光標向盈江地震災區民眾每人發放200元救災款;同日,日本發生9.0級大地震,陳光標飛赴日本購買了5000個口罩,在街頭派發給當地人;2011年9月25日,陳光標在貴州畢節現場向觀眾派發3000頭的豬羊;尤其讓人難忘的是,他用數億元人民幣砌成的“錢墻”……
陳光標動輒“發放現金”的招牌方式,讓很多人不受用。這次在美國,他遇到了同樣的尷尬:不僅有乞丐當場拒絕接受施舍,連當地官方也出面表示“不支持”。他的慈善做派,在一個相對成熟的慈善運作機制中,面臨著不被認可的現實。對此,我們應該如何認知呢?
也許,作為一項社會運作機制,慈善事業遠非“請客吃飯”這么簡單。慈善,固然是一種物質捐贈,但它還有“硬幣的另一面”,那就是價值傳播與感染,用我們的流行語,就是要有正能量,而且可以肯定的說,就重要性而言,后者一點都不亞于前者。
如今,中國富人開始涉足慈善事業,有些也是成功的、受歡迎的,但中國的慈善事業總體仍處于起步階段,由于理論準備不足,慈善的施惠方和受惠方都不知道慈善事業的本質是什么?因此,施惠方往往把向公眾高調撒錢當慈善,而受惠方則往往因個人生活需求、創業需求而向施惠方盲目伸手。
慈善行為從本質上講,是為了滿足社會危困群體或個人的需求,由團體機構或個人以出資、出物、出力等方式進行雪中送炭式的公益扶助。慈善事業要實現理想境界,施惠方和受惠方都要有最基本的素質:施惠方施善應盡量不留名、絕對不求回報(包括口碑宣傳),而受惠方則應永存感恩之心,所謂滴水之恩,異日涌泉相報。反觀近年某些慈善家,送錢時電視攝像機跟在旁邊,這與新年春節時地方政府領導高調慰問貧困群體送慰問金的做法何異?
從這個角度,“中國首善”陳光標的慈善確實還有點“土豪金”,他做慈善很努力,但就是少那么一點點感染力。這種局限性從其個人表述中也能感受到。陳光標也認為,慈善不只是簡單的捐助,但他更強調慈善是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然而,慈善顯然不只是停留在分配意義上的。慈善事業,也遠遠不是投入大宗財產和愛心那么簡單。
完整的慈善事業,需要一種深層的文化理解,需要一套更成熟的機制搭配,需要一個人性化的行為模式。與此對照之下,美國媒體質疑:陳光標所謂的慈善事業似乎完全是在通過施舍進行自我宣傳。
中國的慈善究竟該往哪里走?陳光標曾經覺得應該為中國慈善事業做點什么了,于是就有了他在發達國家高調亮相的做派,但走出國門的“陳氏慈善”,并沒有輔以中國企業家的內斂氣質、審美態度和共生精神。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中國慈善本來不需要以國之名進行營銷,因為這本來就是被人類共識所守候的,慈善事業只有國際攜手合作的份兒,沒必要為誰強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