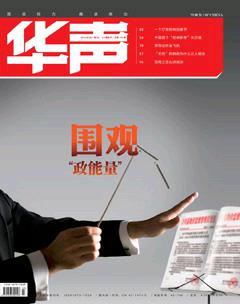尋找“政能量”邊界
整理|田雄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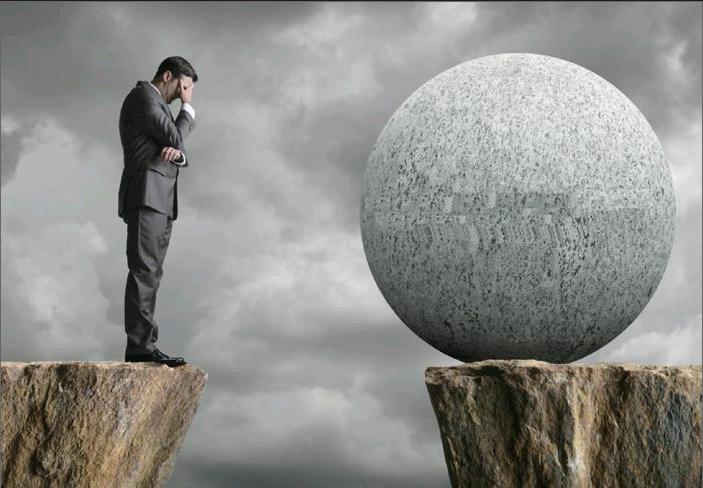
在一次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中,李克強總理講到這樣一個事例: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畢業生,回到家鄉創業,辦一個書店,在多個部門跑了30多趟,花了不少錢,歷時三個多月,總算辦起來了。但開業后,各種檢查、收費、罰款就跟著來了,沒錢就拿書,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最后,他一氣之下關門不干了。
權力總是不甘寂寞,政府活動總是傾向于不受約束。當行政權力過度干預經濟社會生活,并且造成嚴重消極后果之后,人們才意識到政府和市場之間應該有邊界。也就是說,這樣的邊界不可能在一開始就是明確的。然而,沉痛的教訓不應只換來政府的自覺,而應是行政的法治化。當政府取消或下放某些權力時,應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晰、固定,否則,自覺一旦消失,政府從市場中抽身而出的權力,在一夜之間便可跨越邊界向市場縱深推進。
用法律來標識的邊界是清晰可辨的、應當嚴格遵守的,如果法律也不能捍衛邊界,那么就只能捍衛法律的權威。問題在于,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目前還未得到法律的庇護,則侵入市場的行政行為就不會受到懲罰。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湖北的一個縣早前動用“紅頭文件”向鄉鎮攤派銷售湖北自產煙酒的任務,在輿論的強烈關注下,當地表示將迅速撤銷這個文件。即使政府毫無邊界意識,除了被譏為地方保護主義,依然可以毫發無損。如果依法行政與“紅頭文件”可以并行不悖,那么也應當加大對“紅頭文件”的合法性審查。在一些地方,“紅頭文件”已淪為政府自創權力的工具。
在計劃經濟年代,奉行全能主義的政府全面管控經濟,或許還有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雄心抱負;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活動如果不受約束地侵擾市場,則恐怕連半點父愛主義的溫情也沒有。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不應只在人們的心里、政府的覺悟里,更應在措辭嚴謹的法律條文中,在法律不容挑戰的實施中……
尋找政府與市場邊界的中國路徑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而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尋找兩者的邊界,是最基礎的一步。
經過35年的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已經發揮了很大作用,但還沒有發揮決定性作用。具體表現為,首先,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以及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方式,都有待于進一步探索,民營資本所面臨的“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情況始終沒有真正突破。其次,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仍然是雙軌制,價格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發揮不夠,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并存。另外,宏觀調控方式有待改善,近年來通過直接干預價格實施宏觀調控的現象比較明顯。四則,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財稅體制沒有建立起來。坦率地講,地方政府不是不想建設服務型政府,而是事權與財力相脫節使然。有人將各級政府的財力狀況作了形象比喻:“中央喜氣洋洋,省級滿滿當當,市里勉勉強強,縣鄉哭爹叫娘”。地方政府事權大、財力小,容易引發政府越界“自謀財路”的持續沖動。而最受關注的顯然是,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比如,城市里的房子可以賣給農民,農民宅基地上建的房子卻不能賣給城里人。
需要正視的是,要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實踐中的困難源于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慣性與頑固性。
長期以來,相比于消費拉動、外貿驅動,政府直接投資推動是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色調。甚至有觀點認為,政府實際上是“經濟建設型政府”、“地方政府已經公司化”。
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實質,是劃定政府職能邊界。深入研究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論述,我們可以暫且將政府職能概括為以下五項:建設法治政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政治職能);科學宏觀調控,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經濟調節職能);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市場監管職能);改進社會治理,確保社會安定有序和富有生機活力(社會治理職能);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公共服務職能)。
由此,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全面轉變政府職能,促進和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路徑已十分清晰。
政府治理與社會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同時,全會要求創新社會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這是繼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后,再次提出政府與社會邊界的問題,使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共同發展、相得益彰。
社會組織屬于“社會性基礎性設施”,是政府的伙伴,可以幫助政府治理社會,承擔政府支持的公共服務工作。長久的維穩力量來自社會自身。因此,政府與社會組織可以形成拾遺補缺、服務替代、協同增效三種協作關系。
在兩者的關系中,社會組織是政府的伙伴,不是政府的伙計;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潛在賣家,不是政府的執行機構。擁有行政權力的社會組織容易演變為“二政府”,而沒有自主性的社會組織則容易成為政府附屬物。
目前,我國存在社會組織培育發展不足與規范管理不夠的雙重問題,且許多社會組織行政化傾向明顯。在美國每197人中就有一個社會組織,印度每400人中有一個社會組織;而在中國,每2967人中才有一個社會組織。從42個國家的數據分析來看,社會組織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為4.7%,中國內地為0.3%。
2013年3月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了“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的部署。逐步推動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探索一業多會,引入競爭機制。重點培育、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這些社會組織,可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部門審查同意。
尋找”政能量”邊界的國際摸索
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對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進行了多方探索。
對西方國家來說,政府與市場邊界是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而動態調整的,給人以鐘擺之感。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有四個發現。
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是西方各國政府、市場邊界調整的初始條件與基本底色。換言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不管怎么調整,市場經濟體制根基沒有動搖。政府邊界的擴展是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為前提的。
第二,特定時段政府與市場邊界的重大調整,都是為了解決特定歷史階段的具體問題。如果缺乏強有力的國家干預,西方各國能否走出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令人懷疑;如果沒有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職能定位的市場化改革,整個西方世界能否走出經濟滯脹的沼澤也是問題。
第三,不是在經濟發展中取消政府作用,而是探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正如1997年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的那樣,“如果沒有有效的政府,經濟的、社會的和可持續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這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政府的作用是補充市場,而不是替代市場。”
第四,一般以列舉法來界定政府職責,用排除法界定市場作用領域。如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政府的第一項職責:做好基礎性工作”,“在基礎工作之外:政府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所謂的基礎性工作包括五項:建立法律基礎、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環境、包括宏觀經濟的穩定、投資于基本的社會服務與基礎設施、保護承受力差的社會階層、保護環境。
關鍵是該政府做的,政府能不能不缺位、做到位;不該政府插手的,政府能不能沒插手、不越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