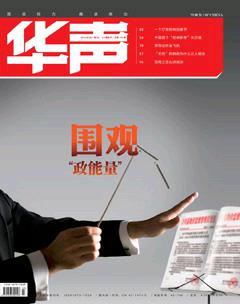我的1979
整理|劉念國



1979年2月17日拂曉,炮火映紅天空,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東西兩線同時向越南軍隊展開反擊,長達近10年的南疆戰事自此打響。
曾幾何時,反映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歌曲、影視作品紅遍大江南北,但時光的流逝沖淡了人們的記憶,今年是對越自衛反擊戰35周年祭,讓我們再次緬懷英烈,重溫共和國戰史!
在人民解放軍如今的高級將領序列中,有一個群體與對越自衛反擊戰息息相關——
許其亮上將,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9年時任空軍航空兵第二十六師獨立大隊大隊長。
張又俠上將,現任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1979年時任14軍40師118團連長。
劉粵軍上將,現任蘭州軍區司令員,1979年時任41軍123師367團2營4連連長。
王西欣少將,現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1979年時任第13集團軍149師446團班長。
坊間稱他們為“英雄越戰幫”,這些人在戰后的十幾年間迅速成長為中國第四代和第五代將領層骨干。而從軍履歷中“曾參加對越邊境作戰”這一筆,成為了日后他們晉升途中的一道助力。
事實上,1979年開始的這一場戰爭,其影響遠不止是培養了中國軍隊現代化進程骨干領導層這么簡單。這場戰爭,它不僅重塑了中國南部的復雜地緣政治格局,也深刻改變了中國軍隊的戰爭思維。它為中國軍隊從骨子里進行變革,提供了血的動力。
一支軍隊,沒有血的代價,就不可能有自我顛覆。
往事如卷,不可盡閱。
今天,我們只想通過四個人的“一九七九”,來翻開35年前中國南疆那場戰事的一個頁角。
講述人:
馮仁昌:湖南人,隸屬陸軍42軍邊防五師二團一營四連偵察兵,1979年2月17日入越作戰。
李永安:湖南人,55軍163師新聞干事,1979年隨部隊進入越南境內,《攻克諒山》拍攝者。
殷燕:女,湖北人,54軍161師文藝兵,戰前編入161師醫院3所醫務兵,1979年2月26日隨部隊入越作戰。
劉萬傳:廣東人,55軍163師489團7連士兵,1979年2月17日入越作戰。
每個人都怕,不怕死的是電影
1979年2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云南、廣西兩線對越南軍隊展開全面反擊,戰線迅速推至越南境內。
23歲的偵察兵馮仁昌,此刻作為東線(廣西方向)先頭部隊一員,開始進攻中越邊境線上一個高不足百米的山頭——庭毫山。
這一槍,打響了這場持續近10年的邊境戰爭。
馮仁昌此時入伍不滿兩年,隸屬解放軍五四二一0部隊邊防五師二團一營四連。算不上老兵,卻也不是新兵蛋子。第一批對越作戰的主力部隊中,大多是1977年左右入伍的兵源,20多歲的小伙子。
馮仁昌所在的邊防五師,1978年10月就已奉調進入廣西前線。事實上,在戰爭打響的一年多前,中越邊境就已處于零星交火的狀態。層出不窮的邊境事件,天天傳進這些軍人的耳朵里。
“因為我們部隊在開戰前就已經部署在中越邊境。有一天,一個女孩哭泣著跑到我們團部報告,稱自己遭到了三名越南特工隊的強奸,大家都很氣憤。”馮仁昌回憶。
邊境的種種慘案,讓這些熱血男兒義憤填膺。保護自家女人,還有什么比這個更能激發血性?
不過,一腔熱血不能掩蓋對死亡的恐懼。這些沒上過戰場的毛頭小伙,每一個戰前的日日夜夜,都重復活在對死亡的恐懼里。
“開戰前一晚,我一宿沒睡著,心理一直在犯嘀咕。上戰場誰不怕死,但主要還是緊張。我沒留下遺書,部隊不讓。”
馮仁昌回憶稱。
2月17日開戰當天,54軍161師的殷燕,尚在師部駐地河南焦作等待開拔。161師作為第二階段主力部隊,參與了攻打越南諒山的關鍵戰役。
開拔前,殷燕碰到了一件事,讓她記憶猶新:
“晚上醫院突然接到一名‘重病號,是482團一個連隊的士兵。由于戰前恐懼,割腕自殺未遂。每天醫生和護士們進去為他治療打針時,都對他投以鄙視的目光。護士給他注射時,手都格外的重,常能看到他疼得呲牙咧嘴,卻不敢發出一聲叫喊,后來在部隊出征的軍列停站休息時,我發現他就在我們隔壁的悶罐車廂里,一同隨部隊拉上了前線,不久他被送上了軍事法庭。”
在對另一老兵、55軍163師489團7連戰士劉萬傳的采訪中,有兩句話令人印象深刻,他用簡短的幾個字回答了“怕不怕”的問題——“我只想活命”、“趕快結束戰爭”。
馮仁昌在攻打庭毫山的戰斗中異常英勇,所在連隊被授予“庭毫山戰斗英雄連”;劉萬傳在拔除“法國樓”工事的戰斗中奮不顧身,所在連被授予“對越自衛反擊戰攻堅英雄連”,個人獲勛章。
雖怯而勇,知節知義,從來都是中國士兵最可敬的地方!
真的戰場,比想象的更糟糕
勝利的光環,淌血的戰場。
李永安是55軍163師唯一一個戰地記者。戰前一天,他曾與487團9連連長張崇福和副連長張運合喝酒壯行。
酒酣胸膽,張運合副連長拍拍李永安的肩膀說:
“李兄,這次去越南,我準備帶著我的熊貓牌收音機,你跟著我們一起打到諒山去,到時候我們在諒山的省府,打開收音機聽中央播報獲勝的消息。過兩天進了越南,你哪都別去,就跟著炊事班,他們去哪兒,你去哪兒。”
2月17日,9連進入越南攻打同登“法國樓”炮臺。
戰斗開始不到1個小時,連長張崇福就被打穿腰部,5分鐘后傷重犧牲。副連長張運合隨即頂替,繼續帶領9連進攻5號高地,一個小時后,張運合也被子彈打中頭部,英勇犧牲。
三個人,最終只有李永安活著到了諒山。
經歷了1979年那個冬天,殷燕才知道真的戰場遠比《英雄兒女》里更糟糕。endprint
2月27日晨,東線最關鍵的諒山戰役開始。殷燕所在的161師負責主攻制高點:650高地。
作為傷烈組醫務兵,殷燕的主要工作是收治傷員,協助手術。此外,她還需分擔烈士遺體收容,排泄物消毒等“臟活累活”。
650高地攻堅戰開始后,殷燕看到的場景是這樣的:
“傷員太多,遍地都是,我們都是蹲著工作,一個接著一個地做手術。時間長了腿便沒了知覺,就跪在地上工作。那六天六夜是我一生中工作最艱苦,最危險、最緊張的時刻。”
有一個河南開封的兵李民,高個,白凈,愛說愛笑,會拉手風琴,醫院的女孩兒們都喜歡和他搭腔聊天,與殷燕相熟。
“2月28日那天,從650高地上抬下來許多尸體。大家都在忙著工作,一個女兵突然驚呼:這是李民嗎?他頭的一半已被炮彈炸飛,癱成一個血肉模糊的肉團,軍裝被血浸透,擔架里都是血水,面目全非。要不是拿出他左上兜能夠證明身份的生死牌,誰也不知道他就是李民。”殷燕回憶。
戰爭的殘忍讓生命如草一般瞬間毀滅,多少人沒有來得及說一句話,就永遠地倒下了。
撤軍前,偵察兵馮仁昌見到了戰友在自己跟前拉響“光榮”彈的一幕。
3月5日,在完成既定的戰略目標后,我軍命令部隊全線從越南境內撤出:
“我們是3月16日時候,接到的撤軍命令。但是我們守了3天,然后才開始走的。我們的一個戰友因為踩中了地雷而被炸傷了雙腿,由于怕連累戰友不能及時后撤,自己拉響了‘光榮彈。30多年了,我至今記得他的名字:程兆輝,湖南人。他當時準備拉響手榴彈的時候,我們戰友都前去拉他,但是他一把扯開,自己壓住手榴彈就走了。”馮仁昌含淚說道。
踏上戰場,都是英雄
李永安之前以為,自己一個拍照片的,不會有任何危險。他不需要打仗,遇到危險可以隨時躲,應該說危險系數基本為0。
2月28日,李永安跟隨部隊攻打諒山。3月4日,攻打諒山南區需要通過奇窮河大橋。
“部隊發起攻擊后,敵人一刻不停地從南邊炮轟北邊橋頭,我先是跟著部隊后面,剛拍了一張照片,就被炮火炸得完全看不清。在我跳下戰壕的一瞬間,一發炮彈在頭頂5米的地方炸開。我親眼看著18位戰士被炸傷亡,我的一只耳朵也再聽不到任何聲音。我找出一個紙煙盒,在隆隆的炮聲里給妻子寫起了遺書。那時候,我的雙胞胎女兒剛三歲,都隨了母親的姓,我就在遺書里和妻子商量,讓小女兒跟自己姓,也算是有個紀念。”
寫完遺書,李永安拿起手槍和相機,爬出戰壕,從奇窮河大橋沖向諒山南區。
3月4日,李永安拍下了1979年反擊戰中最著名的的一張照片:《攻克諒山》。
4日下午,李永安接到電話,要他連夜趕回國將拍攝的照片交到營部。照片隨后被發往北京。
4日晚,鄧小平看到了《攻克諒山》,下令中國部隊撤軍。
馮仁昌是先頭部隊的偵察兵,他更體會什么叫九死一生。
犧牲無處不在,我們的戰士,有時候都搞不清自己的性命,是丟在女人、小孩還是老人手里。
“我所在的連隊正在沿著先頭部隊走過的道路前進,因為越南到處布雷,我們只有沿著之前部隊趟過的道路前進。這時候迎面走來了三個背籮筐的越南女孩。我們當時也沒當回事,就讓她們走了過去。可誰知走了沒多長時間,后邊就傳來了一陣槍響,我們連隊立馬就被放倒了3個人,而我們根本找不到敵人。我們猜想極有可能是剛才那三個越南女孩,背后的籮筐里放著的可能就是AK-47突擊步槍。”馮仁昌說。
即使是殷燕這樣身處“后方”的醫務兵,也隨時面臨著越南特工的偷襲。
650高地攻堅戰傷亡慘重,殷燕所在的戰地醫院消毒水告罄。6月28日深夜,這個19歲的女文藝兵,孤身一人去野外取水。她的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挺住,挺住,向前走!我邊走邊用耳朵聽著周圍的動靜,想著萬一有了情況,扔手榴彈千萬別忘了拉弦兒,給醫院發出信號,讓他們有時間轉移。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絕不能當俘虜。”
1979年2月,42軍162師政治部原電影放映員郭蓉蓉(戰時編入傷烈組),在搶運傷員回國途中,遭越軍特工襲擊,郭蓉蓉連同車上傷員一同被越軍燃燒彈活活燒死,身體燒得焦黑,彎曲成一團——郭蓉蓉是我軍第一個在中越邊境戰場犧牲的女兵,遺體未能運回。
上了戰場,都是英雄!
如果能準備得再好些、再充分些……
鄧小平同志在對越作戰的內部講話曾提到,在這場戰役中,解放軍仍然依賴隊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戰術”沖擊敵人的陣地。這種戰術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價。高級參謀人員年齡老化,不愿放棄傳統的防御戰,雖個人驍勇善戰,但對進行一場現代戰爭毫無準備。
殷燕回憶起她所在部隊的一次“誤傷”。所謂誤傷,或多或少暴露了我軍戰前準備的不足:
“我們師3營7連在向團主力靠攏時與越軍相遇,7連長見進攻受阻,便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坐標位置,并向幾十公里外炮群報告,引導炮兵轟擊越軍陣地。由于部隊配發的軍用地圖是四十年代法國人繪制的,地圖標記與實際景物誤差很大,結果頭幾發用來修正彈著點的炮彈,當即把連長和報務員炸死。數分鐘后,沒得到要求修正弾著點報告的炮群,按照原設定坐標一齊開火。炮火過后越軍陣地夷為平地,7連百十號人也幾乎沒有幾個能站起來了!”
馮仁昌所在部隊在進攻庭毫山時,還遇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況:
“有時候自己人打自己,敵我不分。打庭毫山的時候,我們與自己人打了一夜,后來才知道是自己人!我軍通信能力嚴重落后,我們連當時只有一臺步話機,排以下基本沒有通信聯系。”
另外,由于指揮員缺乏對實際戰場的了解,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傷亡。馮仁昌舉過一個例子:
“我所在部隊沒有坦克和裝甲車的支援,我們也沒有乘坐過裝甲車和坦克。但我軍很多士兵都是乘著坦克前進的。當時有上級下令,要求戰士們將腰帶綁在坦克上,這樣可以隨著坦克來機動。但是越南軍隊使用了高射機槍,在山頭上對我軍進行掃射。由于腰帶來不及解開,大多數士兵被打死在車上。”endprint
馮仁昌的另一段往事,則深刻反映了當時的后勤狀況:
“后勤保障,基本無吃無喝,我常常都是喝草根汁來解渴的,越南境內的水井和水洼子我們根本不敢喝,怕越南人下藥。”
另一名老兵劉萬傳在接受采訪時也提到,自己在越南是靠著喝尸溝里的水活下來的:
“后幾天基本沒吃東西,沒有吃的,沒有水。后來最后實在忍不住了,我喝了有越南死人的水洼,實在是渴得不行了。”
生從祖國來,走回祖國去
3月5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通過新華社向全世界宣布,對越自衛還擊,懲罰侵略者的戰斗已達到預期目的,解放軍于3月5日起全部撤回中國國境線以內。
但回國的道路并不順利。劉萬傳講述了歸國途中遇到的炮擊:
“我們以步行為主,有一段是坐汽車,部隊交替撤退,工兵最后布雷。在撤軍途中,越南的炮火打了過來,他們重炮很猛的,很多都是100毫米口徑以上的,我們遇到炮擊后,就趕快找掩體躲避起來。很多新補充的新兵不知道怎么躲,沒有經驗,沒能回來。”
劉萬傳回國后,就近找了郵局,偷偷寄了一封平安信回家。
新聞干事李永安,由于提前一天回到了國內,見到了一批又一批歸國的部隊通過邊境線:
“我們部隊撤軍時,在越南有越南的老百姓送別,進入廣西,有中國的老百姓來迎接。很多戰士、指揮員都愿意撤軍,也有部分軍級領導希望能往河內挺進,最難打的仗都已經打完,接下來的挺進應該會容易很多。我師 487團2營住在越南邊境一個叫波包村的地方,與當地老百姓共同生活,已經有了感情,中國軍隊撤出時,當地老百姓還前來與官兵握手送別。”
3月6日上午,161師戰地醫院裝車回國,殷燕坐車從友誼關回到了廣西。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和八一廠在關前架起了攝影機。殷燕以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記錄了自己入關回國的心緒:
“從友誼關經過的軍人們,無不被那樓頂上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所吸引,那深情凝望的眼神,是經受過戰場考驗、從生死線上走回來的人才會有的,那是發自心底對祖國依戀的神情。五星紅旗,看到你就是回到了家,看到你就有了安全感,就渾身充滿幸福的力量。軍人們就像久別了母親的孩子一樣,禁不住熱淚盈眶,面對著國旗,舉起右手,久久地行著軍禮不愿放下。”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軍約有6900名指戰員在越南犧牲,14800多人受傷。
謹以此文,祭奠長臥南疆35年的英烈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