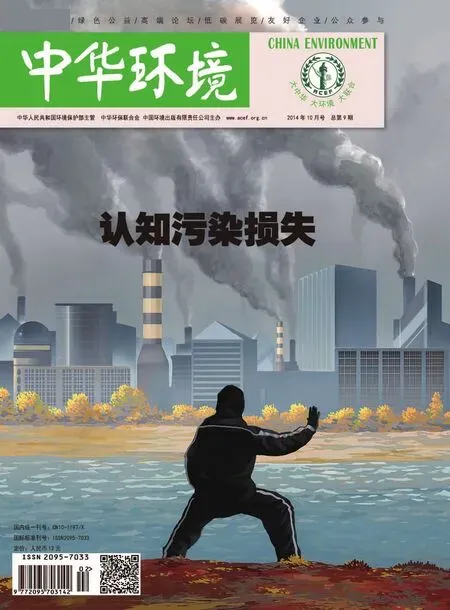不能幸免的污染后遺癥
邵聰慧
不能幸免的污染后遺癥
邵聰慧
污染的頑疾源自社會集體無意識,更為可怕的是,我們無法預料,長此以往會帶來什么災難。

2014年6月24日,湖北宜昌市夷陵區龍泉鎮,長江一級支流柏臨河河水泛著白泡散發陣陣惡臭,水葫蘆、浮萍瘋長阻塞河道。CFP/供圖
這是一個國民“談癌色變”的時代。當我們城市的天空不再藍,當我們喝的水屢屢受到威脅,當我們吃的10頓飯就可能有1頓碰上地溝油,在這不知不覺中,癌癥的小細胞,可能就會悄然滋生。在經濟發展的背后,環境污染的問題日益嚴重。相似的問題,在不同的地方持續上演,并且毫無止步的意思。從傳統產業到新興產業,污染的蔓延正在慢慢結出惡果。
鉛污染“隱身”十年終爆發
在徽縣人眼里,徽縣是中國氣候最好的地方。它地處秦巴山地中的徽成盆地,夏天不熱,冬天不冷,既不潮濕,也不干燥,群山環繞的嘉陵江源頭,山青水秀,原始森林茂密,人稱“隴上小江南”。地下的礦藏更是豐富,有鉛鋅、鐵、汞、硫等22種,還有金礦,而尤以鉛鋅礦儲量豐富。鉛鋅產業是徽縣的工業支柱,但2006年被查出的數百人“鉛中毒”事件使當地人的生活從明亮走向漫無邊際的陰影。
2006年5月,新寺村一名5歲兒童周浩不幸被電擊,失去右臂,被緊急送到陜西西安的西京醫院治療。周浩總是腹痛,嘔吐,引起了醫生的注意。8月,醫生給周浩做了幾項微量元素檢查,驚奇地發現周浩的血鉛含量達到557微克/升,而正常兒童的血鉛含量應在100微克/升以下,小周浩已經重度鉛中毒。這一消息在新寺村及整個徽縣迅速傳開,數千群眾坐長途車去西京醫院檢查,被查出鉛中毒的很快達到七八百人。
有村民回憶,徽縣有色金屬冶煉廠是在1995年五六月間搬遷到新寺村,1996年投入生產,大煙囪開始冒煙。這個大煙囪,每年要向空中傾吐出200噸鉛,鉛的密度高,很快就落到地面。農民鉆進苞谷地里收苞谷,手一抓苞谷就黑了,從苞谷地里出來,全身成了“黑人”。白襯衫晾在屋外,一夜就成了黑襯衫。他們種植的蔬菜,白送都沒人要。
光陰荏苒,轉眼十年,徽縣有色金屬冶煉廠,已經更名為“甘肅宏宇有色金屬冶化公司”,成為洛壩集團的子公司。鉛污染對人體的危害也開始浮出水面。
專家表示,鉛超標可影響神經、造血、消化等多種器官,更為嚴重的是它會影響嬰幼兒的生長和智力發育,損傷認知功能、神經行為和學習記憶等腦功能,嚴重者造成癡呆。
2010年,有記者重返該村,小周浩已年滿9歲。母親王淑紅很發愁,說他幾年來的血鉛含量時高時低,低時300多,高時500多,但至少也是正常標準的3倍。他經常惡心,嘔吐,發燒,老是肚臍眼疼。現在他已經上學,但上課不容易集中精力聽講,好動,愛走神。近來最讓母親王淑紅發愁的是,他的顱骨缺一塊,要做補顱手術,但西京醫院的醫生說,因為他重度鉛中毒,手術后傷口愈合很慢,感染的風險很大。
記者給周浩拍攝時,他戴著帽子,空蕩的右衣袖被風吹動,神情憂郁。而他的小伙伴們不用大人教,就興高采烈地張大嘴讓記者拍他們的牙齒,看來以前“被拍攝”得很多,已經有經驗。他們的牙齒殘缺不堪,并且發黑,單看牙齒你會以為六七十歲了,而他們只有六七歲。
牙黃不僅僅是外表的尷尬,更是生理上的痛苦,嚴重的會使牙齒斷裂、脫落。
“牙黃”和“骨頭脆”的折磨
在陜西省南部的紫陽縣蒿坪鎮,人們的牙齒發黃已經遠近聞名,以至于有了專門的稱呼——“蒿坪牙”。這不僅僅是外表的尷尬,更是生理上的痛苦,嚴重的會使牙齒斷裂、脫落。在科學上,這被稱為“氟斑牙”,屬于燃煤污染型氟中毒。
蒿坪產煤,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但當地的煤含氟量高。據陜西省政府地方病防治辦公室2005年的數據,包括蒿坪鎮所屬的紫陽縣,陜南秦巴山區中南部居民的生活燃料,主要是當地出產的石煤,含氟量在2000mg/kg左右,這是遼寧工程技術大學齊慶杰教授同年給出的中國煤中平均氟含量的近10倍。
中科院地理所王五一教授得出的數據顯示,陜南農戶室內空氣氟濃度最低值是標準的近3倍,而最高值超過標準的97倍(國家標準濃度限值0.007mg/m3)。燃煤釋放的氟等有害物污染了室內空氣和食品,使生活在這一環境的人群發生慢性蓄積性中毒,病癥就是氟斑牙和氟骨癥。
相對于氟斑牙,氟骨病對人們生活的實際影響更大。當地人知道“蒿坪人骨頭脆”。很多人從四五十歲就開始腿疼,嚴重的患者已經出現了腿部變形。
由于燃煤開采量和使用量的擴大,上世紀末陜南的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患開始出現上升趨勢。陜西省政府地方病防治辦公室早在1980年調查,當時陜南秦巴山區安康、漢中市病區人口近15萬,其中氟斑牙患者一萬多人,成人氟骨癥患者五千人。2001年再次調查,病區受危害人口上升到113萬人,成人氟骨癥患者近10萬人,是20年前的20倍。在調查的14萬8-12歲兒童中,患氟斑牙病的有近8萬人,患病率達到56.54%。除了導致中毒者皮膚損害、龜裂,砷中毒還有可能導致神經系統疾病、視力障礙,損害呼吸、消化、循環、泌尿等多種人體系統,甚至導致癌癥。
齊慶杰教授的研究顯示,國產煤在各種燃燒設備的燃燒過程中,大部分煤種的氟含量是超標的,若在燃燒過程中不采取相應措施,將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大氣氟污染。他呼吁在《鍋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中加入對燃煤氟化物的排放限值,目前該標準只對煙塵、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做出了限制要求。
氟中毒也并不是唯一的燃煤引起的地方病。2001年-2003年在陜南進行的燃煤型砷中毒調查顯示:煤砷檢測最高值達到488.1mg/kg,是國家標準的近5倍。被調查的400多人中,砷中毒者近半。
由于各地產出的煤品質不一,燃燒中對健康的影響也不同,但一些普遍成分如顆粒物、硫化物、可揮發的有機物以及重金屬對健康的損害不容忽視。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在中國農村每年由于使用固體燃料(尤其是含氟或含硫高的煤炭)有約40萬人過早死亡,主要是婦女和兒童。

2010年,湖南郴州市桂陽縣發生血鉛中毒事件,圖為正在接受治療的血鉛中毒兒童。
淮河邊上根除不了的“癌癥村”
經過多年的治理修復,淮河水從表面上看已有所改觀。 但河流中的畸形水產和沿淮村莊居高不下的癌癥患病率, 還是讓人擺脫不了“癌癥村”的噩夢。
今年60歲的霍岱珊人稱“淮河衛士”,為淮河污染問題奔波了20年,曾獲評為2007綠色中國年度人物,是民間保護淮河的一面旗幟。在十幾年來的淮河治理中,霍岱珊和他的公益團隊為國家提供了許多關鍵性的第一手材料。霍岱珊告訴記者,雖然現在水質有所好轉,但那些看不到的污染仍致命。“經過這么多年的治理,上游那些‘會說臟話的排污口’已經很難找到了。現在這里的水質是四類水,你看不到污染,也聞不到怪味兒,但是水體中的持久性化學物污染、重金屬超標等仍然存在。”
在霍岱珊辦公室的水族箱里,十幾條畸形魚分外醒目。有些脊柱彎曲成螺旋形,有些鱗片疊生、身體天然殘缺。“這些魚都來自淮河。因為水污染,淮河的魚類曾經幾乎絕跡。現在有了魚,我們卻發現這些魚是畸形的,而且比率很高。有些人家幾代都是漁民的,以前都沒見過這種畸形。”
霍岱珊說,污染對淮河的傷害深入骨髓。持久性化學污染物、重金屬污染“致癌、致畸、致突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被消除。“以美國密西西比河為例,上世紀70年代它是污染很嚴重的,現在已經幾十年過去了,水也清澈了,但是被污染過的魚,沒有人敢吃。淮河水也是一樣。”
受污染影響的不僅是河中生物,過去十多年中,淮河流域的河南、江蘇、安徽等地“癌癥村”頻現。在緊靠沙潁河的河南省沈丘縣杜營村,村支部書記杜衛民回憶,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村里不斷有人患上怪病。“開始就是吃不下飯,在小地方看不準是什么病。到省城大醫院一查,說是癌癥。”
當時正是淮河水質變壞的時候,由于河水污染,上世紀60年代修建的灌溉抽水站只好被廢棄。岸邊莊稼雖緊靠著淮河,卻只能靠老天下雨澆灌。村里十幾米深的飲用水井也被污染,“水有怪味,一燒全是水垢。”
死亡陰影籠罩了杜營這個有2000多人口的村莊。杜衛民說,2003年到2010年間,村里癌癥發病率最高,每年都有十幾個人死于癌癥。“我們有個孫營自然村,2006年的時候,村里一條胡同里有8戶都得了癌癥,很多人發病后都挨不過一年。”
霍岱珊說,他們現在發現的“癌癥村”有20多個,但他反復強調,這絕不是全部。“因為很多地方我們沒有走到,但我們總結出了一條規律,凡是河岸邊的村莊,凡是劣五類水長期滯留的地方,就可能有癌癥村。后來我們按照這辦法去找,一找一個準。”
反思:不能以生命的代價縱容污染
此外,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古河鎮洋橋村,因為靠近農藥廠,該村于2001至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癥。村民睡覺時以濕毛巾捂口鼻,鴨子不在水邊而在豬圈里放養。鹽城市阜寧縣楊集鎮東進村,受巨龍化工廠嚴重污染,2001至2006年5年間死于癌癥的村民近100人。四川省什邡市雙盛鎮亭江村,該村躲過了地震卻難逃污染,至2008年,癌癥致死者達五六十人。最新的來自“中國長壽之鄉”山東省萊州市,日益嚴重的化工污染使當地部分村莊成為“癌癥村”……
每個“確診”的癌癥村都是用村民的死亡作為直接病例,事實面前任何利益團體的辯解都是蒼白的。縱觀近年來各地發生的污染事件,因由幾乎都大同小異,企業不負責任、監管不負責任、政府不負責任,儼然形成了一條黑色的環境污染“鏈條”,最終只能由無助又無奈的民眾吞下惡果,甚至賠進生命。
諸多的無奈與嘆息,凸顯出的正是當下中國許多地方的真實情形——在經濟發展的背后,環境污染的問題日益嚴重。糟糕的是,這是一個早已被人們認識到的問題,卻仍然缺少明晰的解決方案,或者說,雖有方案卻缺少解決問題的真誠意愿。
問題的關鍵在哪里?這一點不難回答: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的口號之下,只顧上馬有經濟效益的企業,卻對企業在治污方面的作為明顯監管不夠;二是相關企業,盲目奉行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并不顧及負外部效應,或只把社會責任的概念掛在嘴上,并不真正付諸行動;三是基層民眾,其利益博弈能力遠遠不足,最終成為各類污染事故的主要受害者。
這些年來,我們見多了一些地方急于上馬項目卻疏于監管、環境監測往往走過場的現象。有些時候,有些地方官員甚至明知新項目開工會導致污染問題,也裝聾作啞,在相關企業出了問題之后,也是急于包庇,而非依法作出處理。極端的時候,個別地方的行政、司法機構還會抵制甚至打擊各種力量合法、合理的監督。顯然,對于地方主事者來說,這不是一種對民眾、時代,以及對歷史負責的做法。
一個地方政府的努力,為的是民眾能夠得到更有幸福感、更有尊嚴的生活。GDP不一定代表幸福感,就業人數與財政稅收的上升也不一定意味著幸福感,民眾被強制拆遷或是遭受污染之痛卻難以得到合理的補償,更不會有幸福感。幸福感源自綠色的發展,源自有尊嚴的發展,源自生活于一方土地上的民眾在遭遇困難之后卻能夠堅信未來。
同時,一些當事企業必須作出自省,必須學會在法治的框架下謀求企業的發展。如果一個企業只顧病態地追求利潤,而無視公共利益,這樣的企業注定不可能走得很遠。遺憾的是,在一些時候,我們看到了個別企業嘴上一套,行動上又是一套——嘴上念叨著社會責任與民生利益,行動上卻是連起碼的法律法規也不遵守。一旦出了問題,不是以正確的態度面對問題,不是積極地提出方案作出整改,而往往是以一種“滅火”的態度或求助于地方政府,或通過小恩小惠企圖“搞定”監督力量。須知,一個兩個負面報道或許可以擺平,但在朗朗乾坤之下,又如何能夠蒙住民眾的千萬雙眼睛?
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不能再過度透支資源與環境,不能再借著發展的名義縱容污染。為官者也好,經商者也好,如果心中沒有這樣的信念,那么將很有可能留下人生的敗筆,也將辜負對時代的起碼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