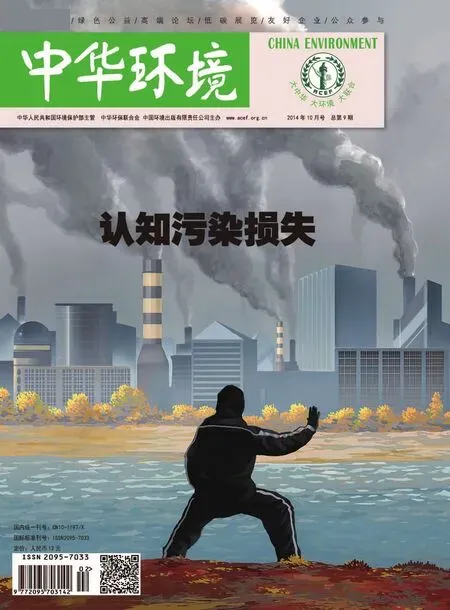污染場地修復:將環境責任進行到底
高勝達 中國環境修復網執行主編
張旭輝 中國環境修復網
污染場地修復:將環境責任進行到底
高勝達 中國環境修復網執行主編
張旭輝 中國環境修復網
污染場地真正威脅的并不是土地開發利用,而是更廣義的環境安全。如果中國能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污染責任機制,讓污染了土壤、地下水的企業不能輕易脫身,不僅要出資修復,主要負責人還可能會承擔相應民事和刑事責任,那么即使沒有環保局定期檢查,生產企業也一定會施行清潔生產,保護土壤和地下水環境。

土壤樣品
污染場地是最近兩三年才廣為人知的環保概念,它的普及主要歸功于另一個熱詞——土壤污染。媒體通過對一些土壤修復項目和從業企業的報道,逐漸描繪出初生的土壤修復產業的形貌,這在很大程度上讓全社會對土壤污染認識更清楚,關注更密切,對全國土壤污染調查數據的追問更把關注度推上了高點。
在這種社會氛圍下,國務院《近期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安排》、環保部《關于加強工業企業關停、搬遷及原址場地再開發利用過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關于開展污染場地環境監管試點工作的通知》、污染場地5項技術標準等一系列政策和技術文件陸續出臺。
面對社會保護土壤的呼聲,我國政府的反應速度很快。不過,由于我國的環保法規和政策并未對土壤環境保護做出比較具體的要求,因此關于土壤環境污染、管理和工程層面的經驗還比較少,想要全面迅速地管控和治理土壤污染還有許多困難。而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恐怕就是概念的準確把握和管理思路的厘清。
修復污染場地是為了什么
要問為什么,先問是什么。污染場地(Contanminated Site)是外來詞,是指因各類生產活動而受到污染的空間區域,通常主要包括被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兩大部分,但也可以包含部分地表水和場地內的建筑、設施等。我國污染場地修復起于房地產行業的黃金時代,修復主要是為了保證土地開發利用的環境安全,因此地下水環境一般不在考慮范圍內。同時由于修復后的場地幾乎全都立即開工建設,場地內也不會留下地表水和建筑物。所以,我國目前為止污染場地修復的絕大部分工作都是土壤修復。這也是國內常把二者等同起來的原因。
如果沒有害處,等同倒也無妨。可實際上,污染場地真正威脅的并不是土地開發利用,而是更廣義的環境安全。在美國環保局公布的案例中,許多污染場地中的有害物質都能通過地下水遷移到距場地很遠的地方,通過飲用、呼吸、皮膚接觸等方式對人和動物造成傷害,并破壞生態環境;一些污染場地內被拆除的建筑物和設施碎片若未經處理就運離場地,也可能埋下環境隱患。因此,污染場地環境管理顯然不是治理土壤污染的另一種說法,而是生產活動場所環境污染綜合防控和治理措施的統稱。準確地說,一個污染場地幾乎必定包含受污染的土壤,只修復土壤往往不能消除污染場地的危害。
由于理解偏差,我國目前出臺的許多相關政策都側重于土地開發的環境問題管理,對不開發的土地則缺少關注,使得以湖南湘鄉、云南陸良、蘭州石化等為代表的“不開發”場地被置于污染場地政策管理的范圍之外,得不到及時的控制和修復。好在今年出臺的國家標準《污染場地術語》已經糾正了對污染場地定義的錯誤理解,接下來就需要產業界不斷在理論和操作層面鞏固和加深正確的概念。
修復產業雄起難在哪
對概念和目標的回答只能解決朝哪個方向努力的問題,但這只是正確道路上的第一步,污染場地環境管理可用的武器實在太少了。
我們缺少法律的武器。我國環境保護法體系中,一部獨立的土壤環境法一直是缺失的,關于土壤的法律規定都分散在各單項法中,不成體系;地下水環境在《水污染防治法》中也只有少得可憐的原則性規定。這樣零散和籠統的法律規定,根本不足以支撐起污染場地相關一系列制度的建設。環境保護部今年發布污染場地5項國家標準時,科技司相關負責人說道,5項標準是技術標準,暫不涉及管理內容。之所以這樣說,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管理制度的制定還找不到系統、有力的法律依據,只能暫緩。污染了的場地要不要修復?誰來組織修復?誰來出資?誰來監管?誰為修復效果負最終責任?這此都是制度設計要回答的,更是環境法要回答的。
我們缺少標準的武器。5項國家標準的發布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污染場地修復技術工作無章可循的困局,但我國畢竟還沒有建立比較完整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具體來說就是農用地土壤環境標準嚴重落后于時代發展,而城鎮用地土壤環境標準還沒有出臺。污染的定義是環境介質中污染物超過一個規定的限值,限值就是標準。沒有標準就意味著無法判斷一個場地“是否被污染了”,自然就談不上是否要修復。另外,土壤和地下水修復技術的篩選和認證都有待加速開展,什么技術能用、好用,適用范圍如何、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能不能承受,等等問題都需要解答。
我們也缺少資金的武器。“氣十條”提出大氣污染治理目標,稱需投入1.7萬億元。根據治理的難度和國際經驗,土壤治理需要的資金還遠多于此。環保部生態司司長莊國泰預計需要幾十萬億。這種數量級的資金想靠財政完全解決無疑是天方夜譚,只能依靠社會和市場。目前多個省份啟動的污染場地調查和修復項目,資金來源一是財政撥款,二是社會融資,靠修復后的土地開發收益償還本金和利息。在房地產緊縮、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地方政府負債浮出水面的當下,土地收益拯救不了土壤污染,更不必提這種模式固有的“污染者逍遙,開發者埋單”的環境不公平問題。
我們還缺少技術支撐的武器。我國土壤污染修復科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早,但受限于產業拉動乏力,許多修復技術研發停留在實驗室階段,實際應用中的難題尚未解決,距離規模化、產業化還有很遠的距離。同時,由于開展針對性培養的高校和院所還不多,本土成長起來的修復人才比較匱乏,海歸人才既數量有限又不能很快適應國內環境。因此,我國修復產業的技術支撐能力薄弱,退一步講,即使國家政策力挺,馬上拋出一個修復的“大餡餅”,產業界接不接得住也不好說。
責任機制是啟動修復工作的牛鼻子
我國環保管理主要側重于預防和過程管理,比如環評、監測和監察(排污達標和排污費)制度。罰款雖然屬于事后懲戒,但力度非常有限。環保部剛剛發布的消息稱,今年上半年全國共處罰環境違法案件19289件,處罰金額74325.1萬元,平均下來每案罰金只有3.85萬元,怎么可能震懾違法行為?怎么夠修復受損的環境?
大氣和地表水循環快,自凈能力強,所以其治理主要是“減排”。土壤地下水自凈能力很弱,一次污染能保持幾十年甚至更久,所以修復才十分必要,可是其修復費用很高,通常是現行排污費和罰款的千倍甚至萬倍。我國一些企業生產經營多年,直到關停和搬遷時才發現,企業貢獻的稅收和利潤還不及修復其污染所需費用的零頭。由于始終沒有一套制度要求污染企業為環境修復付費,這樣的污染仍在一些地區不斷上演。環境修復是正外部性的,是用經濟利益換取社會效益,既然法律沒有規定污染了必須修復,修復市場上自然沒有需求,修復產業一切最美好的愿景,都不過是水中撈月。
“污染者付費”是基于人類基本倫理道德推導出的原則,也是世界各國環境法的通行原則。如果中國能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污染責任機制,讓污染了土壤、地下水的企業不能輕易脫身,不僅要出資修復,主要負責人還可能會承擔相應民事和刑事責任,那么即使沒有環保局定期檢查,生產企業也一定會施行清潔生產,保護土壤和地下水環境。
至于那些拒不實行清潔生產,嚴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企業,責任機制將通過污染損害鑒定評估、場地調查、修復方案設計等措施,算出企業需要為污染付出的巨大但合理的代價,讓有改進空間的企業痛定思痛,改造升級;讓無力改進的企業因承受不了而永遠退出市場,形成良幣驅逐劣幣的局面,同時實現環境管理的高效和國家產業升級。


國內有觀點認為,污染是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嚴格的污染場地責任制度會滯緩國民經濟發展。但美國的經驗表明,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超級基金法》指導下開展的污染場地修復非但沒有損害美國經濟發展,反而使美國一直處于世界經濟的龍頭地位,沒有任何數據表明嚴格的污染責任制度拖延了經濟發展。恰恰相反,污染責任機制提高了企業環保意識,促進了美國產業轉型升級,以微軟為代表的一大批現代高科技企業正是從那時起步的。
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生態文明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地位。生態文明的中心詞是文明,是在意識層面對發展、財富、幸福的重新定義,是認識和行為的蛻變。如果污染者固守現狀的甜頭大過痛感,那他們絕不會去蛻變。既然現有的手段還不能讓污染者感到很痛,我們能不能讓污染者為治理污染埋一次“全單”?這看起來很有些難,但或許僅僅因為從沒試過才覺得難。中國需要遏止污染蔓延,需要真正樹立企業環保意識,還需要新的、綠色的經濟增長點,污染責任機制都能幫我們做到,勇敢地嘗試一次吧,即使不成功,相信也沒有壞處。


上圖:土壤固化穩定化下圖:藥劑噴撒
(文內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