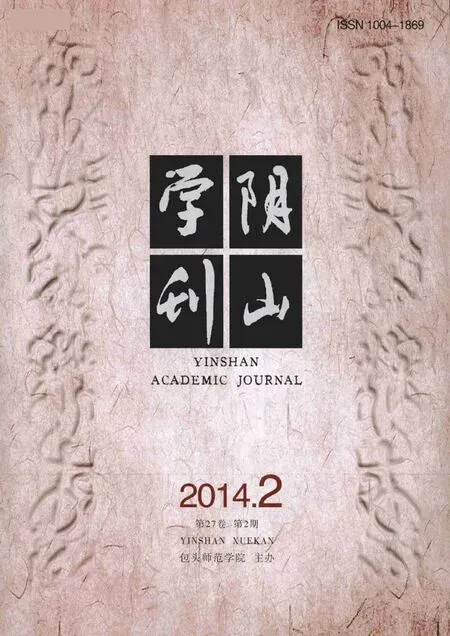功在當代,澤被后學
——《宋詩話全編》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價值
張 福 勛
(包頭師范學院 文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30)
先師吳文治先生,傾其畢生精力,領銜編纂的大著《宋詩話全編》[1](以下簡稱《全編》),十冊巨軼,700余萬字,囊括宋人詩話凡564種,其中第一冊涉及詩話108種,第二冊52種,第三冊83種(本文所述,暫及前三冊)。這些詩話的范圍,涵蓋了詩論、詩話專著和主要的詩論家及主要的論詩名著,更蒐集到了至今還遠未為研究者所知曉的散見于浩瀚載籍中的論詩片言只語。或考辨典故,或錄存逸作,或辨析真偽,或品評詩作,或記載詩事,或補正舛訛,而所有這些資料,對治古代文學者,無疑具有莫大的參考意義。茲就前三冊所見,以斑窺豹,略述其價值。
(一)補闕正誤的重要資料價值
一般治宋詩者,清人厲鶚之《宋詩紀事》[2](以下簡稱《紀事》)必系案頭必備之參考。《紀事》無疑是一部“淵源偉大的著作”[3],裒輯宋代詩人3812人,詩作8061首,征引材料1205種,但又“采摭雖廣,訛脫亦多”[4]。或者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云:“采摭既繁,牴牾不免”,或“不免于粗琉”,或“失于考證”[5]。于是又有陸心源的《宋詩紀事補遺》[6],補得詩人3000余家,詩作8000余首。但“買菜求益,更不精審”[4]而又“錯誤百出”[3]。于是又有了今人孔凡禮先生之《宋詩紀事續補》[7]輯錄二氏未收宋代詩人1826人并《續補拾遺》續收宋詩作者約600人。
盡管如此,仍然不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或誤收、漏收;或作家作品重出;或小傳、小注舛誤,或引書不準等等。而《宋詩話全編》在這些方面具有或補闕、或正誤的重要資料價值和創新理論的意義。
《紀事》卷十六所記袁陟(字世弼,號遁翁,有《遁翁集》)薦郭功甫與自作墓誌云云[2](P416),分引自《潘子真詩話》與《苕溪漁隱叢話》二書。實為同出《潘子真詩話》一書,不過分為前后二條(第二〇條和第二一條)[1](P670~672)。從而廊清了《紀事》引書之誤。
并且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又補評其詩曰:“少有文學,古詩尤佳。”蔡絛《西清詩話》又補其詩友關系說“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修)、劉原父(敞)、王文公(安石),皆其知友。”并評其詩曰:“丱時,(即)能詩,天才秀穎,有唐人風。”[1](P2484)而這些材料,對于準確、全面認識袁世弼的詩風,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參考。
宋詩人之資料,于厲氏《紀事》、陸氏《補遺》、孔氏《續補》以至《全宋詩》,皆有缺漏之憾。而《全編》中這方面的補漏,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如詩人王次卿的資料,于《周紫芝詩話》據其《太倉稊米集》卷五一《溪文集序》中有以下記載:
“吾友王次卿好學喜文,尤長于詩。其為詩如江平風霽,微波不回,而洶涌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引者按:這是對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和藝術風格的評介)其為人似其為詩,平居言笑樂易,與人和柔,未嘗一失顏色;而其涇渭白黑,自有胸次,不肯略毫發于人(引者按:這是對其為人品德之評價)。”以上資料,不僅提供了我們研究詩人、詩作的重要參考,又對其詩集的流傳情況,作了詳細的說明:“紹興七年秋九月學佛者宗毅出其(按指次卿)遺編以示仆,得詩若干,文若干,總總三百七十有九首。”可知在南宋初年尚見其作品,并且從“毅少學詩于次卿”的記載,得知其在當時的影響。可惜在后來的流轉過程中亡逸或寢失?故《紀事》、《補遺》、《續補》、《全宋詩》,包括《四庫全書總目》皆應收而未收[1](P2845)。
有的作者在《紀事》中只有作品而有關作者的資料又太簡括,如卷四十只據《東觀余論》入選翁挺詩一首,而作者小傳也只有48字。《補遺》也只收作品而無作者傳略,《全編》第三冊第2862頁《李綱詩話》自其《梁溪集》卷一三八《五峰居士(按翁號)文集序》中輯出作者生平及創作的重要資料:
“故尚書、考功員外郎翁君,諱挺,字士特、建之,崇安人。天才秀發,器業夙成,年未成童,已知聲律,能賦詩,有驚人語。及長,該極群書,貫穿古今,落筆即數千言。既而游行四方,渡浙江,寓淮楚,窺衡湘,觀光上都,宦游趙、魏之邦,盡友其豪俊,以故為文雄渾雅健,淵源浩博,能備眾體。而尤長于詩。其五言、七言,屬對律切,風清調深;其古風,歌行,渾厚簡淡,凌厲奮發,絕去筆墨、畦徑間,追古作者,信乎天下之奇才也。”對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及其藝術特點,作出了全面的評價。并且還對其詩風之成因,作出了簡捷的闡明:“(其)觸時相怒,竄逐流離,得病以死,而年僅逾于知命。身之窮,近世鮮有與君比者。平生所作數千百篇,悲歡感慨,一寓于詩以發之,奇辭秀句,膾炙人口。詩之昌,近世亦鮮與君比者。”
簡直就是一篇詩人、詩作研究的專題精彩論文!其價值,毋庸置喙。
有的詩作只是詩人的傳記資料,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亡逸不免,加以傳寫謬誤,寢失舊文,烏三轉而為馬,《全編》提供了準確的資料加以匡正、糾偏,從而具有了難得的學術價值。
《潘子真詩話》舉曾南豐(鞏)言杜牧《阿房宮賦》“鼎鐺玉石,珠瑰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考“瑰”實為“塊”之誤:“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按,從辭語結構來說,“珠”而視若“塊”,“金”而視若“礫”,也完全符合語言運用的習慣與規律[1](P669)。考辨之細謹,令人稱嘆。
又《張邦基詩話》(《墨莊漫錄》)說《劉貢父詩話》指杜甫詩:“功曹無復漢蕭何。”認為功曹不應為蕭何,而是少陵之誤。張引《后漢·高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云云。注引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以此反駁以為“少陵用此非誤”,而是劉貢父“偶思之未至耳。”這樣就避免了《劉貢父詩話》以訛傳訛也。[1](P2206)
有的詩話其思辨之精細,考證之功力,為我們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如對唐王勃之《滕王閣序》之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考辨,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例證。
①廣益書局刊行之言文對照的《古今觀止》:“落霞自天而下,孤鶩自下而上,故曰‘齊飛’;秋水碧而連天,長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8](卷三P20)
②)徐中玉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只釋:鶩,鴨類。[9](第四冊P13)
③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一冊引明代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一釋:落霞是鳥,形如鸚哥。[10](P260)
④北京出版社《中國歷代散文選》下冊釋:鶩,野鴨。[11](P7)
⑤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的《古代散文選》中冊解釋同④。
⑥上海教育學院編《中國古代文學讀本》三冊解釋落霞為自然景色,引宋人葉大慶《考古質疑》,言滕王閣遠眺之景: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與落霞齊爾。遠水連天,上下一色。[12](P307)
而《全編》三冊《吳曾詩話》》自其《能改齋漫錄》卷十四《記文》,引土人云:“落霞非云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麥蛾是也。當七、八月間,皆紛紛墮于江中,土人謂之霞,故(王)勃取以配鶩耳。”又引唐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本不能飛騰。”并引鄭康成注云:“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1](P3169)從而提出了全新的解釋,說明“落霞”與“孤鶩”,是“飛蛾”與“家鴨”,其色混為一體,在江面上漂浮。而“長天”與“秋水”,遠望連在了一起。
又《俞成詩話》據其《螢雪叢說》卷下,專有《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一篇言《吳獬事始》(按未見之僻書)云:“落霞”者,乃飛蛾也,非云霞之霞,土人呼為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1](P2783)
這樣的考據,從一種全新的視角,開啟了研究者的思索,不僵死,不守成,將死蛇弄活。
《全唐詩》詩人小傳與元人辛文房之《唐才子傳》之人物傳略,也給后人的研究留下了某些缺憾,也是靠《全編》得以補救。
如《馬永易詩話》自其《實賓錄》卷二《甫里先生》一則云:唐陸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舉進士一不中。居松江甫里(按號出此),往從張博游。[1](P678)(引者按,《唐才子傳》[13](P364)作“搏”注疑作“摶”——簡作“摶”)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篷席,赍束書、茶、灶、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遂為散人歌。(按《全唐詩》卷六百二十一有《江湖散人歌并傳》[14](P7146))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后以高士招不至。
《全唐詩》雖有陸龜蒙小傳[14](P7108),但過于簡單而枯澀,可從《馬永易詩話》中得到完整補充,如同一篇微型小說,陸龜蒙這個“江湖散人”的風神,生動地活跳了起來,非常有利于我們對其詩作風格的準確把握。
某些詩事的記載,如《墨莊漫錄》(《張邦基詩話》)關于“雪浪石”的記載[1](P2238)為后來學者注蘇詩,提供了十分重要和可靠的資料來源。清馮應榴《蘇軾詩集合注》《雪浪石》一詩引查慎行[15](P1888)所注只是根據《墨莊漫談》所記作了摘要,而《張邦基詩話》卻提供了最原始、最完備的記載,對于研究者探索蘇詩的意蘊,裨益良多。
《宋詩紀事》卷十一曾子固之祖曾易占詩《題洪州僧寺》一首[2](P272),注引出自《能改齋漫錄》(按,卷十八《神仙鬼怪》)。而《全編》之《吳曾詩話》(據其《能改齋漫錄》摘錄編纂)卻辨以為“然此詩乃蔡君謨詩,易占偶書之耳。”[1](P3178)將著作權歸還了蔡君謨,糾正了《紀事》之誤收。
《杜詩詳注》注《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咫尺應須論萬里”引《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16](P756)而《全編》之《朱翌詩話》(據其《猗覺寮雜記》卷上)指出《南史》“蕭賁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1](P3427)兩相比較,前者隔靴搔癢,而后者一引中鵠矣。
對某些詩詞名篇個別辭句的辨證訛謬,更有利于研究者對于詩意的準確把握。
如白居易《琵琶行》“家在蝦蟇陵下住”,《嚴有翼詩話》(《藝苑雌黃》)引《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蟇陵。”并征東坡詩“只難敢望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并《謝徐朝奉啟》“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作為佐證。連帶辯證這種“世俗訛謬極多”,舉古樂府有《相府蓮》,其后訛為《想夫憐》;藥石“補骨脂”其后訛為“破故紙”等等,可見周密《齊東野語》所謂“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謬等書,以雌黃(按,雌黃本為一種礦物質,可以涂抹誤書處,以稱改竄、駁正)前輩”[1](P2344)是也。
又如考唐人詩句中用“儂”字,《吳曾詩話》據其《能改齋漫錄》卷一《事始》引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并舉孟郊詩句“儂是拍浪兒”為證。吳氏以為“吳音稱儂,其來甚久,詩人用之,豈始東野耶?”引《古樂府》南朝宋鮑照《吳歌》云:“但觀流水還,識是儂(汝)流下。”又舉晉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儂(我)見郎。”又考晉吳聲歌曲,多以“儂”對“歡”,詳其詞意,則“歡”乃婦人,“儂”乃男子耳。如《懊儂歌》云:“潭如陌上鼓,許是儂歡婦。”后讀《通典》又見“江南謂情人為歡”。[1](P2997)直步步深入矣。
糾謬者如洪駒父《詩話》根據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認為“顧愷之小字虎頭”。
《吳曾詩話》(自其《能改齋漫錄》卷五《辨誤》)考查南朝宋劉義慶《世說》,乃謂:“顧愷之為虎頭將軍”。得出結論說“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1](P3032)。
按,張彥遠為唐朝人,劉義慶為南朝宋人,從時代(時間)上講,劉更接近于東晉的顧愷之;再從著作的性質上講,《世說》專門記人,而《名畫》則主要說畫,相比之下,則更愿相信《世說》。
包括后世流行的諸如《辭海》“顧愷之”條也沿襲了《名畫記》的錯誤。
某些文辭的考辨,提供了不同于歷代詮釋的另一種聲音,可以拓展人們研究的視野。
如李商隱的《錦瑟》之“莊生”、“望帝”。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之《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安徽師大中文系《李商隱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劉逸生《李商隱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余恕誠 《李商隱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等選本,都無一例外地將其坐實為真人;而《邵博詩話》(自其《河南邵氏聞見后錄》卷一八),卻認為“莊生、望帝皆瑟中古曲名”。并以杜甫“無風云出塞,不夜月臨關”其中“無風”和“不夜”,并非實指自然界之“風”和“夜”,而是兩座“城名”加以旁證。[1](P3211)讓人眼前一亮,頓覺新穎!且與“錦瑟”題目相吻合。為研究者開拓了另一種詮釋視野。
再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王觀國《學林新編》,據漢《郡國志》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于仙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又引《建康實錄》曰:“桓玄遺書于匡山惠遠法師”。據此以為匡山者,即廬山也。以之釋杜甫“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為招隱廬山之游也。
以上都是胡仔的舊說。
而吳曾引唐范傳正《李白新墓碑》(按,范碑系據李白之子所手疏——參見清王琦《李太白全集》下冊附錄卷三十一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華書局,1977年第1461頁)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說“彰明”為四川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于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以此斷定,所謂“匡山”,乃四川彰明縣之大匡山,而非江西之匡廬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為妄辨”[1](P3032)。
(二)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事實支撐
1.生平事跡之重要補遺
如在宋代的文學批評史(特別是詩話研究史)中,人們只知道李頎是個詩話作者。于《宋史·藝文志》載有李頎《古今詩話錄》七十卷,惜已佚。而在宋人的詩話著述中,如阮閱《詩話總龜》、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蔡正孫《詩林廣記》中皆有不同的存錄。而郭紹虞先生的《宋詩話輯佚》[17]上冊輯得444則,最為詳贍。但皆未及李頎生平事跡。郭先生《宋詩話考》中也只說“李頎生平事跡無可考”[18](P166)。(按,唐人亦有李頎者,見殷璠《河岳英靈集》卷上)
但于《全編》之《何薳詩話》(自其《春渚紀聞》卷五《李朱畫得坡仙賞識》)中,窺得其一斑:“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為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于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其書一詩其后,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于湖山僧舍,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云泉(按指所畫自然景物)勸我早抽身。’”[1](P2674)
知李頎不僅僅是文學批評家,而且還是當時文壇上知名的畫家和詩人。
又《春渚紀聞》卷六《東坡事實·蘇秦相遇自述挽誌》云:先生(蘇)自惠州移儋耳(儋州),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啟后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亦嘗自為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蘇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可知蘇軾在被流放儋州以后,已經作了被加害致死的精神準備。
孔凡禮生生之煌煌巨著《蘇軾年譜》卷四十: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六十六歲軾卒。[19]書中先后引用《春渚紀聞》五次,而未及臨終“自為志墓文”一段重要文字,留下缺憾。見出《全編》之補逸,對于全面研究作家生平之重要意義。
歐陽修《六一詩話》第九條記許洞難倒諸僧作詩事。但對作家“許洞”其人,并無記載。而《龔明之詩話》自其《中吳紀聞》卷一則專有《許洞》記云:
“許洞,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登咸豐三年進士第,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當世皆知其名,歐陽文忠公嘗稱其為俊逸之士。所居唯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吳人至今稱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洞與潘閬、錢易為友,狂放不羈。”又記其品行,云:“當潘坐罪亡命隱入中條山時,洞不懼時政,仍‘密贈之詩’,祈念中條山神能保佑潘云云。”[1](P3266~3267)
許洞這樣一個當時“皆知其名”的重要詩人的事跡,經過這些生動而具體的材料支撐,一下子就鮮活了起來。使他矗立在了宋代的群彥士林之中。
按,《紀事》卷七曾引《中吳紀聞》但不詳[2](P169),對作家研究不如《龔明之詩話》之裨益大焉。
中華書局1961年出版北大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所編《陶淵明詩文匯評》,關于《歸去來辭》共匯輯資料31條[20](P327~338),但遺漏了一條重要參考,即汪藻《浮溪文集》卷一九《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1](P2770)所載:“淵明作《歸去來》,托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為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為喜。視物聚散,如浮云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為淵明”。這一段話,對于正確認識《歸去來》的思想價值和準確把握淵明之思想內質,均有重要參考價值。
有的人物傳記,描寫人物如同一篇微型小說,給我們研究作家的生活、性格、修養等,提供了難得的細節材料。
《吳曾詩話》引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二二記邵堯夫(康節)居洛四十年,安平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記其性致: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為安樂先生。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堯夫每出,隨意所之,遇上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或賢不肖貴賤,皆歡然相親。自言:“有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有如此雅興,真乃賢至之人也!
又記其學問: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又記其節操:朝廷常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其名于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1](P3189)
一個豐滿、賢達、高尚之人,就活跳在讀者面前了。
2.補充宋代僧詩和詩僧的難得材料
宋代的詩僧和僧詩,因為是宋詩花園里的一枝奇葩,始終是宋詩研究者們關注的一個亮點。
厲鶚《宋詩紀事》卷九十一、九十二專辟“釋子”二卷,編者從151種諸如筆記、詩話、府志、碑帖、野史、佛典、禪書、寺志、譜牒、圖經、詩文集等珍秘典籍中,輯得宋詩僧240人,僧詩405首,詩聯147。另于九十四卷錄入女詩僧5人,詩5首。(可參拙著《宋詩論集·宋代的詩僧與僧詩》,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以四卷收入詩僧195人。今人孔凡禮于《紀事》、《補遺》之外,又于《宋詩紀事續補》三十卷,又輯得宋代詩僧333人。錢鐘書先生《談藝錄》六九引《古今禪藻集》一書,其所輯系自支遁以下僧詩。[21]
可知是“宋人詩文恥無僧”,而“詩里無僧字不清”,幾及乎宋人詩學一種極頑固的觀念。(可參見方回《瀛奎律髓》紀曉嵐批點僧詩,中國書店,1990年)
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十說:“景祐中,光梵大師惟凈以梵學著聞天下;皇祐中,大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凈居傳法院,璉居凈因院,一時學者依以揚聲”。可見禪宗對當時宋代整個社會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有多么巨大!
《全編》(前三冊)前后征引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許顗詩話》、張邦基《墨莊漫錄》、王铚《雪溪集》、黃徹《恐溪詩話》、《呂頤浩詩話》(自其《忠穆集》)、洪覺范《石門文字禪》、《冷齋夜話》、《天廚禁臠》、《呂□詩話》、《呂氏詩話》、蔡絛《西清詩話》、《龔明之詩話》(自其《中吳紀聞》)等典籍,爬羅剔抉,窮搜極討,發潛闡幽,提供了許多有關宋代詩僧與僧詩的稀缺資料,為宋詩研究者大開了方便之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恕不一一揀摘。
更為寶貴的是,有的還對僧詩的特點進行了很好的概括和比較。比如李彌遜《筠溪集》卷二一《跋微上人〈徑山賦〉后》評微上人詩“能以古為詩,遣辭嚴平,立意深切,置之才士述作中,孰知其為僧語”[1](P2992)。施得操《北窗炙輠錄》卷上評惠先覺詩“渾然天成,無一毫斧鑿痕,雍容閑逸,最有唐人風氣”。
朱弁《風月堂詩話》引東坡語比較辨才詩“落筆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詩卻如“巧人織繡耳”[1](P2942)。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六六《書璉上人詩卷后》評璉上人詩“嫵媚清熟”[1](P2819)等等。均給后人研究宋代的詩學批評以大裨益。
3.彌補某些人物關系的重要史事,使我們得以更加全面、完整地認識一些文學家的全貌,而不至于誤解和曲解。
如《潘子真詩話》第一八條記東坡于鐘山專門拜訪荊公并和詩[1](P670),第二三條又從另一個側面記述荊公高度評價東坡文似西漢,“直須與馬長(司馬相如)馳騁上下”[1](P672)等等細節,讓我們正確地認識二人雖然政見相左,而并不影響其文學上的往來和公正地評價對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見出其胸襟之廣大。
《龔明之詩話》自其《東吳紀聞》卷五記其季父龔況“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唯季父與蘇元老在庭爾,當時號為‘龔蘇’。葉石林俊聲籍甚,嘗為文字交。其它所與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平甫、張敏叔亦皆一時名士。”研究者可從這些文學的交游情況,分析作者的行處和文學風格、文學成就 、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等。
(三)為文學史上的某些專門問題,提供佐證材料
如七言詩的起源問題。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世傳七言起于漢武柏梁臺體。”征引《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群臣有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22](P2944)為據。幾成定說。
《全編》之《王得臣詩話》自其《麈史》卷二云:“世言七言詩肇于柏梁而盛于建安。考之,豈獨柏梁哉!”認為不起于漢武,下舉《詩經》之風、雅、頌,楚狂之接輿歌,它如項籍之歌,漢高(祖)之歌,然后下結論說:“皆七言之濫觴也。”認為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襲。”[1](P879)
此說打開了我們研究的廣闊思路,而不囿于陳說,啟示研究者總是要進行新的探索。
又如關于“曲”與“謠”的區別問題。
《吳曾詩話》據其《能改齋漫錄》卷一之《事始》曰:自昔歌辭,或謂之曲。并引《琴書》認為東漢蔡邕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制一弄。下分別剖析“東曲”、“南曲”、“中曲”、“北曲”、“西曲”之具體情況。最后說“三年曲成”。認為“曲”由山之曲來。
又考西漢武帝詩云:“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引《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1](P2997)是從結構之章節上區分。
按,唐孔穎達《左傳正義》:“《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遙”。(按,東漢許慎《說文》:“夫謠與遙同部,凡發于近地者,即可傳于遠方也。”)其實,自《毛詩序》:“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23](P30),探討“歌”之產生;經魏曹丕《典論·論文》探討“歌”之體不同:“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之音樂,由于“引氣不齊”而造成“巧拙有素”(本),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3](P61)又到東晉陸機《文賦》論述“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23](P67)等等,前人已從各個不同的層面,將“歌”、“謠”之本質問題論述盡矣。
再加上《吳曾詩話》考“曲”與“謠”之區別,可見清人杜文瀾《古謠諺·凡例》以及近人劉毓崧《古謠諺序》之研究[23](P390),可謂晚矣。
又,一般研究文體者,往往征引《文心》及明人徐師曾之《文體明辨序說》。其實,在它們二者之間,《全編》之《李之儀詩話》(自其《姑溪居士全集》卷一六之《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已對歌、行、嘆、曲、謠、篇、章等體區別,作了很細微的區分:
“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于句之長短,聲之高下,則為‘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遵而引之,以致其所欲達,則為‘行’。事有所感,行于嗟嘆之不足,則為‘嘆’。千岐萬轍,非詰屈折旋則不可盡,則為‘曲’。未見其實,而遂欲驟見,始仿佛傳聞之得,而會于必至,則為‘謠’。‘篇’者,舉其全也。‘章’者,次第陳之,互見而相明也”。從生成之原,到形體之別,而至風格之異,可謂述說殆盡矣。
再如《胡笳十八拍》著作權之歸屬問題也是文學史上聚訟紛紜之事。
王觀國《學林新編》引秦再思《紀異錄》,以為是(王)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昭君感焉為制曲,凡十八拍。”而王氏認為作者應系董祀妻蔡琰(文姬)為胡騎所獲后又歸漢所作。又引王安石《集句胡笳十八拍》首言“中郎(即蔡邕)有女能傳業”,而斷定“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于世。”而吳曾認為(自其《能改齋漫錄》卷五《辨誤》)“觀國謂為文姬所撰亦非矣。”他引謝希逸《琴論》以為昭君作曲凡有七曲,不過是(音樂上)拍數不同而已。并得出結論:“觀國謂昭君不能制曲,又非也。”[1](P3025)體現了學術爭鳴上開放的民主的氣氛。而這種氣氛,有利于推進學術的進步和真正地、徹底地解決相關問題。
(四)詩話所記對某些作家、作品的評論,藝術風格的品評,文論觀點的概括,則更具有直接的理論意義
1.補《紀事》、《補遺》、《續補》作家小傳無評之缺
《李彌遜詩話》自其《筠溪集》卷二一《跋趙見獨詩后》評趙見獨“作語平淡高古,不類近世詩家者流,飄然有晉宋風味。”[1](P2992)
《周紫芝詩話》自其《太倉稊米集》卷六六《書〈月巖集〉(按李廌字方叔號太華逸民,有《月巖集》)后》評李廌:“今誦其詩,讀其文,然后知此老之言(按指李端叔序其文謂東坡嘗稱其文“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也。”)為有旨焉,而自非豪邁英杰之氣過人十倍,則其發為文詞何以若是其痛快邪!”
又如宋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柳開,對他在宋代文學(特別是古文)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是《吳曾詩話》(據其《能改齋漫錄》卷一〇《議論》)作了重要的補充:
“本朝承五季之隨,文尚儷偶,自柳開首變其風。謂文章宜以韓(愈)為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于子厚(柳宗元)耳。(柳)開未第時,采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逾二十,慕王通讀經,以經籍存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舊名與字,謂開古圣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為途,故字仲途。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苑》。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余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坎》,《易》之爻、象,其深焉;余不為深也。’蓋(柳)開之謹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于穆伯長(穆修),非也。”
這一段論述,其重心不在于介紹柳開的一般生平事跡,而是闡明其在宋代古文改革運動中的首開貢獻,及其在宋代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可補《中國文學批評史》[24]中關于柳開的遺缺部分。
2.藝術風格的品評,更為后來研究者的藝術分析奠了基,鋪了路
《李彌遜詩話》自其《筠溪集》卷二二《舍人林公時旉(又作敷)集后序》,對于林時敷詩的藝術風格,作了精彩的描述:“介翁(號)深于詩,不自立戶牖,其欣于所遇,悲于所感,賦事體物,酬餞贄贈,一取他人語而隱括之。章成,千態萬狀,貫穿妥帖,不見罅隙,皆足以發難顯之情。至其奔放曲折,莫可排障,浩浩汩汩,行于地中,是豈章句士所能為哉!”又論其風格形成的原因,“介翁敏博而文,讀書過眼輒誦,自著或訓解,卷百有奇,煨燼之余,唯此稿存。”“其受才廓達雄驁,大而難用,立朝不避怨嫉,宦不遂,抱其蘊以死。”[1](P2944)
對韓子蒼(駒)詩風的把握,也是很好的例子。《宋詩紀事》前后征引宋人詩話九種之多,而未及中的,而《周紫芝詩話》自其《太倉稊米集》卷六七《書陵陽集后》只以兩句話:“淡泊而有思致,奇麗而不雕刻”便入骨也。[1](P2852)
范溫《潛溪詩眼》對于建安風格的品騭,更成為經典之評:“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1](P1245)
更為難得的是對各人的藝術風格,往往用擬物品評的對比法,進行比較研究,尋覓出它們之間的異中之同,特別是同中之異來。
如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一《紀詩》之《四客各有所長》比較“蘇門四學士”之藝術風格,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庭堅)、張文潛(耒)、晁無咎、秦少游(觀),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若四人之著。”其中黃、秦、晁,乃長公之客,張乃少公之客也。“然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辭,秦、晁長于議論。”又引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若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
經過這樣的生動比擬,不比不知道,一比見分曉,蘇軾、蘇轍、黃庭堅、陳師道、秦觀、晁無咎的各自風格特點,便赫然醒目矣。
“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過(適?)口者少矣。”(按:枯澀)
形容殆盡,當然未必皆恰切。
在風格批評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不只各說各的,只進行平行式的風格羅列,而是交叉式的互比長短,呈現出立體式的特點。如《臨漢隱居詩話》評“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同),李益古、律詩相稱(同),然皆非應物之比(異)也。”二是各人風格之長與短,也一并指出,如《鄭獬詩話》說在韓退之門下,以文章雄于一世者,“獨李翱、皇甫湜、張籍耳”,“然翱之文尚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于詩,至于它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
3.彌補權威注釋之批評不足
對一些歷代權威著作注釋中的評論不足之處,進行“亡羊補牢”的救濟。
如清仇兆鰲《杜詩評注》中《哀江頭》漏掉了張戒《歲寒堂詩話》重要評價“唐人吟詠至多,然類皆無禮”進行了彌補,并以此對作品進行了具體的分析[1](P3241~3242),最后對《哀江頭》作出了總體的中肯評論:“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并比較了同題材白居易的《長恨歌》與元微之的《連昌宮詞》,認為“皆不若子美詩之微而婉。”“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嘆曰’。(可知)人才高下乃如此!”
4.指出權威批評之不當
如《葉夢得詩話》卷下指出《詩品》“某人詩出于某人”之不當,是鐘嶸之“陋”。舉陶淵明出于應璩說為例(可參見周振甫《詩品譯注》論《詩品》的品陶等次[25](P7),引錢鐘書《談藝錄》第91頁,容不贅述)。
5.指明某些批評詞語之出處
如《嚴有翼詩話》中“辨證訛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語)舉羅隱《江東集》中《淚詩》后二句“自從魯國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婦人”[14](P7561),一般注書皆不詳其出處。而嚴拈出《孔叢子》子高言“凡泣者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儒夫,以泣著愛。”[1](P2325)如此則《淚詩》便釋然全解矣。
6.詩藝(技巧、方法)研究之創新
詩藝的研究,是詩歌藝術研究的一部分。
北宋畫家李伯時(龍眠)畫《山莊圖》,作為理論家、鑒賞家的蘇軾認為此圖畫得如此神妙,其原因就是“有道有藝”。“道”是作家、藝術家對自然界及人類社會規律的認識;而“藝”則是表達這種認識的一種手段,一種技巧、方法。因此,“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于心,而不形于手”。[26](P823),雖然認識了,把握了,卻不能很好地將這種認識完美地表達出來。可知詩藝研究的重要。
拙著《詩的藝術世界》[27]已經根據詩話所提供之材料,歸納、總結出古典詩詞藝術技巧65種。而《全編》中各種詩話對此不斷有所創新,有所發現,也有新的闡述。余又從其中撰寫出《睹影見竿乃妙》、《以俚俗語入詩》、《詩語“互相備”》、《舉果知因與舉因知果》、《“歇后”所造成的韻味》、《詩藝之故倒用》、《一語及二事》、《以一字見工拙》、《詩的細節描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詩怎樣有“滋味”?》以及《無理的“變形”》、《無聲而為有聲與有聲而為無聲》、《以未見而已見》、《用字重復而多變》、《以不言言之》等15篇詩藝的短文,已發表于報端,茲不重述。
當然,《全編》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或以文話羼入,如《范仲淹詩話》之論宋;或以詞話混入,如《張先詩話》之論詞;或與詩話無關涉者濫入,如《劉攽詩話》自劉《彭城集》輯錄所謂“詩話”六十則,其實全為“詩作”而非“詩話”;或以同一人名而重又命名詩話,如《優古堂詩話》重命名為《吳幵詩話》,容易造成混亂,等等。
[1]吳文治.宋詩話全編[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2]厲鶚.宋詩紀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錢鐘書.宋詩選注·序[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4]錢鐘書.宋詩紀事補正·題辭[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
[5]紀昀.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4.
[6]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M].北京:中華書局圖書館影印本.
[7]孔凡禮.宋詩紀事續補[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8]陸文昭.重訂言文對照古文觀止[M].上海:廣益書局,1947.
[9]徐中玉.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劉盼遂,郭預衡.中國歷代散文選[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12]上海教育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讀本[M].山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
[13](元)辛文房.唐才子傳[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14](清)康然四十六年御制.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
[15](清)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6](清)仇兆鰲.杜詩評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7]郭紹虞.宋詩話輯佚[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8]郭紹虞.宋詩話考[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9]孔凡禮.蘇軾年譜[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0]北大中文系.陶淵明詩文匯評[C].北京:中華書局,1961.
[21]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22](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23]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4]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5]周振甫.詩品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6]蘇軾.蘇軾文集[M].長沙:岳麓書社,2000.
[27]張福勛.詩的藝術世界[M].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