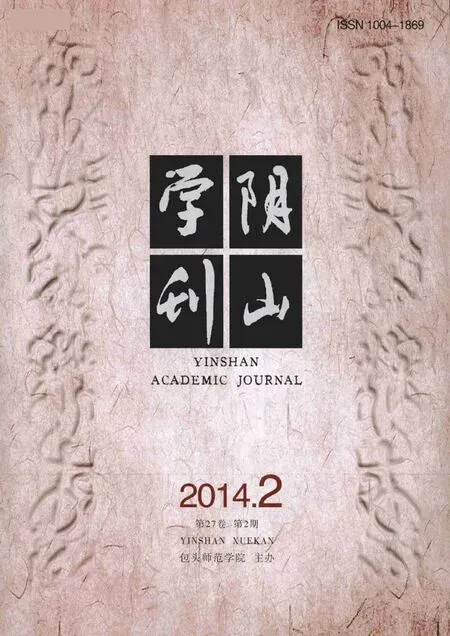試析土默特文化對北方民族多元文化傳承的歷史作用
王 澤 民
(右玉縣文聯,山西 朔州 037200)
土默特,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特殊的歷史文化系統。土默特文化,是以土默特部文化為基礎并融入了漢、藏、滿、回等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種地域文化。研究土默特文化,對于探討中國北方民族文化的歷史淵源和內涵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土默特文化具有豐富的包容性,它不僅具有一般文化的社會屬性,而且還具有鮮明的民族個性,它是歷經北方各民族的艱辛開拓、傳承積蓄和不斷創造而形成的特色鮮明、富有活力的地域性文化。開展土默特文化研究,推動土默特文化發展,是我們應該擔當的歷史重任。
近幾年,土默特文化已經受到國內外學界的關注,也取得了一系列開創性的豐碩研究成果,把土默特文化作為整體研究對象,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土默特文化的內涵、類型、特征和基本精神,挖掘了土默特文化的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揭示了土默特文化在北方民族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闡述了土默特文化是北方民族文化建設厚重的文化積淀和精神資源,這對于土默特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
在古代歷史上,曾經有許多游牧民族在土默特地區成長壯大,他們與生活在這里的其他民族共同創造了輝煌的歷史。盡管這些游牧民族由于種種原因相互嬗遞比較頻繁,有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已經與其他民族互融,但他們各具特色的歷史足跡卻深深地鑲嵌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
春秋戰國時期前后,活動在北方地區的游牧民族一般被稱為“胡”,史書中有代表性的是林胡和樓煩。他們活動比較頻繁的地區是今天的土默特地區以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等地。趙國在武靈王統治時期,勢力范圍達到今呼和浩特一帶。趙武靈王在原陽設置“騎邑”,學習林胡、樓煩的騎射技術,增強了軍隊的實戰能力。史學界以“胡服騎射”來贊譽趙武靈王向林胡、樓煩學習的進步舉措。騎射提高了軍隊的戰斗能力,使趙國在云中一帶的統治日益鞏固,林胡、樓煩被迫西遷。
進入秦漢時期,匈奴人成為活動在今天土默特地區的一個強大的民族,河套、陰山一帶是其發祥地。戰國時代的燕、趙、秦政權的邊界都與匈奴人活動的地區相鄰。秦滅六國以后,曾派大將蒙恬與匈奴大戰于北邊,“悉收河南地”,修筑了幾十座城池并派兵戍守;又修九原至云陽的直道,加強對匈奴的防備。
匈奴人頻繁地、大規模地出入和進駐今天的土默特地區也是不容忽視的歷史內容。一般來講,成百上千甚至幾千騎進入云中(今托克托縣)、定襄(今和林格爾縣)、雁門(今右玉縣)的情況甚多,較大規模的可達3萬騎左右。所以,在匈奴與中原的關系中,這一地區顯得十分重要。直到公元前33年的“昭君出塞”以及呼韓邪單于與漢朝的和親,則表明了相當一部分匈奴人強烈的和平愿望,50年以后,雙方基本處于無戰事狀態,友好交往成為主流。民族關系的融洽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其最明顯的作用之一就是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在此基礎上,各民族在經濟、文化諸領域相互交流的機會增多,歷史呈現多元化發展也就成為必然。
東漢后期,北方各地戰亂不已。南匈奴的許多人口被遷入今山西省境內,對今天土默特地區古代歷史的影響減弱。隨著曹魏政權對云中、定襄、雁門等郡的喬遷以及南匈奴的內徙,鮮卑人取代匈奴人成為在這一地區歷史上又一個影響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5世紀,敕勒人居此,人稱敕勒川。蒙古土默特部勃興,此間又以土默川著稱于世。16世紀土默特部的領地,以土默川為中心,西至烏拉山前后,東達宣化以北一帶。鼎盛時期,其領地甚至擴展到青海一帶。17世紀中葉以后直至1949年,土默特兩翼轄境為通常所謂的歸綏、薩拉齊、托克托、和林格爾、清水河、武川、包頭七縣及歸綏地區。
土默特地區向稱富庶。先前畜牧業發達,馬駝牛羊繁殖每以數十萬計,后來,牧場墾為農田,農產品又為大宗。自然資源豐富,地下蘊藏極富開發前景,地上動植物及水利、氣候資源亦頗為可觀。全境山水掩映,景觀甚佳。
14世紀以前,漢、回等族曾在土默特地區生息。到16世紀中葉,內地漢族農民相繼徙來,人數達5萬至10萬,土默川出現了規模可觀的農業和手工業。入清以來,隨著清廷對土默特牧場的開墾,漢族人大批遷來,同時也有部分回族人定居于此,本地區遂形成蒙、漢、回、滿等各民族雜居局面。與土默特地區相鄰的殺虎口自古以來就是北方民族同中原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尤其是土默特地區的歷代各民族正是通過這一地帶南下中原,這個地區又是他們的重要基地和后方,這不但推動了北方文化的發展,也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劇烈變化,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使南北民族間在政治、軍事、經濟乃至社會習俗、觀念形態、宗教信仰等各個領域的全面交往與交流,從而使這個地區得以成為中國多民族活動的大舞臺,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爐。也就是說,在民族大融合,社會大轉軌的時期,北方草原民族不僅帶來了極富生氣、極其活躍的文化品格,為中華民族注入了活力與生命,而且更帶來了歐亞大陸草原民族文化和各種信息,在中國古文明締造史上更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拓跋鮮卑改革舊俗,倡導漢文化,積極仿制和推行中原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土默特首領俺答汗在隆慶年間被明王朝冊封為順義王,其妾三娘子被明廷封為忠順夫人,先后為黃臺吉、扯力克收繼,歷事三王,左右土默特政局達40年。《明史》卷327《韃靼傳》稱,三娘子佐歷代順義王主貢時,“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三娘子為蒙漢友好和民族團結作出了突出貢獻。
明隆慶年間,殺虎口便是通貢互市之要地。“大同方面,后來增設守口堡馬市,以待原與黃臺吉同在新平堡互市的兀慎、擺腰諸部。又在助馬堡、保安堡、寧虜堡、殺胡堡、云石堡、迎恩堡、滅胡堡等處設小市場。” (王士琦《三云籌俎考》卷3《險隘考》、楊時寧《三鎮圖說》,玄覽堂叢書本)[1](P332)清代時,殺虎口又成為朝貢、商貿、移民、稅關之要道。隨著清政府對內蒙古地區移民政策的轉變,那些長期飽受災荒、重稅之苦的山西人,尤其是晉西北地區的流民,開始紛紛涌向邊關險塞,徙居口外長城以北土默特地區,從事農耕和行商活動,這種特殊的人口遷移現象,從清朝前期開始,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近三個世紀。殺虎口作為“直北之要沖”自然成為移民運動的重要口岸,山西移民,尤其是晉西北的移民主力軍便穿越此口,浩浩蕩蕩地奔赴土地肥沃的土默特地區,也有人把這一社會現象稱為“走西口”。在“走西口”移民運動中,晉蒙兩地在文化上出現的大碰撞、大交流,發生了明顯的吸收融合與共鑄新質現象。以《走西口》為代表的民歌圈的生成和“二人臺”戲曲的出現,就是這種融合共鑄的重要成果。
從殺虎口“吉盛堂”發展成為稱雄塞外的巨商“大盛魁”,二百余年頻繁往來草原與內地之間,殺虎口作為連接草原和內地的紐帶,自然成為晉商旅蒙的主要渠道。有清一代長達300年之久,土默特地區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之間,經過長期互通有無貿易往來,帶動了游牧地區經濟、文化、交通等諸方面的發展和變化。
二
文化作為民族凝聚力、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作為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生活在土默特地區的各民族從不自我封閉、固步不前,而是在游牧和農耕生產實踐的基礎上,從經濟文化交流等方面,鑄就了該地區民族開放的心態、豪放的性格和進取的精神。他們以開放豁達的心態互相彌補各自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各民族之間不斷進行全面的、多領域的、大規模的聯系與交往。而且這種聯系和交往在特點、方式、機遇等方面具有非常明顯的指向性和內聚性。這種多民族多文化的格局從客觀上決定了中國北方民族文化是多元一體的格局。
由于游牧地區缺少對自身經濟產品轉化的機制,維系自身生命的某些產品必須從中原農耕地區獲得,這就演化為對外產品的交換、軍事的對抗甚至文化的碰撞是游牧地區人民繁衍發展的必然。明王朝在隆慶五年(1571年)與俺答汗達成和議,恢復通貢關系,并在大同得勝堡和大同右衛殺胡(虎)堡開設邊貿互市場所。邊貿互市場所使蒙漢人民的生活、生產有了相應的改善和提高,尤其是通過相互交往增進了民族間的友誼。明正德以來在一段時間內,明朝統治者同蒙古封建主的關系日趨緊張,統治階級彼此敵視,封禁、攻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族關系,致使民族矛盾一度激化。在這種情況下,蒙漢勞動人民仍然相互友好往來,說明蒙漢人民之間的友誼,以及彼此間的歷時久遠的經濟聯系,絕不是封建統治者的意志所能轉移的。墩哨軍丁為避免摩擦“全不坐哨”,民族間的摩擦少了,和平與友好往來必然就成為當時民族關系的主要方面。同樣,蒙古族進入長城,也漸漸由攻掠轉向“與我買賣”,尋求以貿易的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實際需要。在邊貿市場的影響下,邊鎮一些高級軍官“希求茍安”,遂以布緞等物“買和”,[2](《禁通虜酌邊哨以懲夙玩疏》)甚至結交蒙古族的首領。如隆慶四年(1570年)大同參將楊縉就以紅布、梭布六百匹及改機緞、水獺皮等物送俺答求和,同時以梭布二百匹贖回十余名被擄人口。[3](《俺答列傳中》)就是向以敢戰著稱的周尚文也不能逆轉這種希望和平的趨勢,他在嘉靖中期任大同總兵時,也不免“私使其部與虜市”[3](《俺答列傳上》),在明廷屢次拒絕俺答求貢,俺答每次興兵南下的情況下,他藉此同俺答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俺答封貢后宣大等七鎮皆開馬市。這次馬市除官市外,還增設民市、小市,聽任商民軍兵與牧民交易,私市貿易終于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認。從隆慶五年起,民間貿易一直沒有間斷,持續了幾十年之久,這是明代蒙漢民族關系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
通過私市貿易,蒙漢人民間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故當沿邊人民的反抗遭到失敗后,他們便紛紛逃往塞外,“北走俺答諸部”[4](《俺答封貢》)。此外,由于生活無著,或不堪壓榨而零星逃出邊塞的農民,為數更多。對于這些逃來塞外求生路的漢族,蒙古族盡可能地予以救助,依照當時蒙古社會實行的一種贍養法,即“有窮夷來投,別夷來降,此部中人必給以牛羊牧之,至于孳生已廣,其人已富,則還其所給”[5](《牧養》)。據有關資料記載,來自內地的一些漢族人沿大小黑河,“開良田數千頃”,并建造了許多村莊。因漢人自稱百姓,蒙古人也以此稱呼他們,譯寫諧音作“板升”。漢族聚居的村莊,也隨之被稱為板升。在蒙、漢人民共同努力下,土默川的農業迅速發展,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促使蒙古封建主進一步改變他們的政策。原來在蒙古封建主同明朝的戰爭中,從內地俘獲了許多漢人。這些人多數淪為牧奴,“男子放牧、挑水、打柴,婦女揉皮、擠奶”[2]王崇古《核功實更賞格以開歸民向化疏》。
當土默川的開發具有一定規模,蒙漢關系有了改善,俺答便適時地采取一些措施,把一部分被掠被俘而淪為牧奴的漢人,從家庭奴隸的地位中解脫出來,讓他們參加到農業生產中去。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俺答開始從漢人牧奴中擇選儒生,給以自由民身份,使他們參加墾殖。以后,俺答又進一步從被俘為奴的漢人中,將“有智勇藝能之人”解脫出來,“令之管事”[5](《聽訟》)。至于有些“藝能”的人,還被封作達兒漢,如豐州川著名的三十二板升的首領中,就有“東打兒漢”、“打兒漢”等。從畜牧業家庭奴隸地位中解脫出來的漢人為數不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提高了人們的勞動熱情,對蒙漢共同建設家園起了積極作用。
隨著農業大規模的發展,這個地區手工業也有了可喜的進步。在逃亡草地漢人中,有一些工匠是極其寶貴的手工藝人,蒙古族對他們頗為器重。隨同丘富來到草地的丘仝,是位“習梓人藝”的木匠。他一來便施展了才干,為俺答“造起樓房三區”,又造船,還制作了不少農耕器具,因而被俺答倚為親信。隨同呂老祖(即呂鶴)來的弓匠賀彥英,一次就為俺答“治弓數十張”,[3](《俺答列傳中》)受到青睞。
在板升首領中,也有許多名噪一時的工匠,如“王繡匠”、“楊木匠”、“土骨赤”(即鐵匠)等等。這些工匠,在土默川“造室力農”、“筑城建墩”中大顯身手,發揮了重大作用。由于他們將漢族先進的手工業技術帶進草地,所以蒙古族的手工業水平也有了相應的提高。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求貢時送給明朝的貢品中,手工藝品就有“金銀鍋各一口”,至隆慶四年俺答封貢時,貢品中則有鍍銀鞍轡、鍍金撒袋(即箭囊)。
在農業手工業得到發展的基礎上,營造規模較大的城池的條件日臻成熟。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板升漢人在趙全等帶領下,于今包頭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村附近,建造了范圍約十里的“大板升城”。第二年,他們“采大木十圍以上”,又在城內建了七重宮殿和三重倉房,修建五重城樓。該城的修建,標志著土默川的開發和經濟發展水平又有了顯著的提高。
農業的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促進畜牧經濟的發展。嘉靖初當俺答駐牧開平一帶時,他們尚處于“最貧”的境地,擁有的牲畜數量很少。而到嘉靖末,俺答部已擁有“馬四十萬,駝牛羊百萬”[3](《俺答列傳上》)。這個巨大的變化,除畜牧經濟本身的發展外,應主要歸結于對土默川的全面開發和建設,尤其是農業經濟的發展對畜牧業所起的促進作用。俺答封貢時,王崇古曾說過,“今板升農業,亦虜中食物所資”[6](王崇古《散逆黨說》),這里數萬漢人所生產的谷物,除自己食用外,基本上也能滿足數萬蒙古牧民的需要。這個地區所存在的嚴重食物不足的社會問題,至此基本得到了解決。這對畜牧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另外,板升漢人在發展農業的同時,還普遍經營畜牧業,飼養了大量牲畜,如趙全的板升就擁有數萬馬牛,對發展土默川畜牧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在蒙漢人民共同開發與建設土默川的過程中,蒙漢人民在文化、語言乃至生活習俗上日益接近,民族文化相互影響已經越來越大。在土默特地區漢人中,使用蒙古族語言的人非常普遍,有些還會書寫蒙古文字,如李自馨、周元和王孟秋等人就不僅會說蒙語也會寫蒙文。在漢族文化影響下,一些牧民也由游牧轉向定居,逐漸學會從事農業生產,在土默川板升中就有“夷二千余人”。[3](《俺答列傳下》)
在板升的漢人中,起蒙古名字的也不足為奇,如漢族人趙龍在塞外生了幾個小孩,起了蒙古名字火泥計、窩兔等。到了萬歷年間,板升地方的漢族人也被明朝官員統稱作“夷人”,與蒙古族不加區別了。萬歷十一年(1583年),兵科給事中陳亮條陳說,“板升夷人,眾至十萬,宜令通事及親識者密諭得意,許其率所部來降,照宣撫宣慰事例授以世官。”[7](卷一四一)由于長期居住在板升的很多漢族人語言和生活習慣均與蒙古人相同,所以也就成了“夷人”。因為板升的漢族人已經漸漸融合于蒙古族,他們也一掃“思鄉歸正”,*鄭洛《慎招納》曰:“議款之初,華人被虜,家有父母妻子,思鄉歸正者其人固多”。反變成了明廷宣撫宣慰的對象。蒙古民族懇切期望同中原地區友好相處,通過俺答一再向明朝請求通貢,這種懇切的心情已經強烈地表現出來。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俺答向明朝提出入貢以來,在十七年中俺答又十余次提出類似的要求。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遣石天爵等通貢,申明“北部素通中國,進貢不絕,后因小失乖異。今愿入貢獻馬駝,貢道通則兩不猜忌,中國可出二邊墾田,北部自于磧外畜牧,請飲血為盟”[8](卷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俺答又向明朝進一步提出“請為外臣,朝請甌脫,給耕具食力”[9](馮時可《俺答前志》)的要求。為順利實現上述要求,俺答曾告誡諸部:“若等過塞上,敢犯塞上秋毫者,聽若等奪其穹廬及馬牛羊”[3](《俺答列傳上》),嚴禁屬部攻擾明邊。嘉靖期間,俺答為緩和雙方的緊張關系,是作過積極努力的。他的通貢主張和行動,不僅代表著蒙古族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對中原漢族人民來說,也利害攸關,故廣大邊民深表贊同。
蒙漢人民共同對土默川的開發與建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里的貧困面貌,但生活中所需的布緞、鐵器及農耕器具,仍是塞外無法解決的。長期以來塞外的困難,正如俺答在貢表中所說的,“各邊不許開市,衣用全無,氈裘不奈夏熱,緞布難得。每次因奸人趙全等誘引,入邊作歹,雖嘗搶掠些須,人馬常被殺傷。近年各邊時常調兵出搗,殺虜家口,趕奪馬匹,邊外野草盡燒,冬春人畜難過”[10]。
隆慶年間,方逢時、王崇古先后調任大同巡撫和宣大總督,他們一到任所,就盡量撤去大邊的墩軍,嚴飭諸將不得擅自出兵,要求各邊要遍插紅旗招納降者,這一變化為蒙漢民族友好開創了廣闊的前景。無論俺答,還是明朝,都在伺機行事。隆慶四年(1570年)九月,俺答的愛孫把漢那吉攜妻子及奶公阿力哥等,投奔大同敗胡堡這一事件立即成為雙方改善關系的契機。
把漢那吉是因內訌出走的。他所以投奔明朝,也是受了招降的影響。把漢那吉一行受到邊關的熱情接待,方逢時對他們厚加宴賞,并妥善安置在大同城館驛內。方逢時想趁此時機,與俺答和好,開放馬市。方逢時在九月底給王崇古的信說:“兩據平邊中路探報,俺答走了此孫,刻期聚兵來搶左右衛地方,索要孫兒,其言甚真。而劉廷玉所報要甚么即與甚么之說不虛。則弟昨所言與之為市之計,似有可行,惟在公主張,選擇得人行之。”[11](《與王軍門論降夷書》)明朝以誠相待,使俺答深受感動。明廷于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受到明廷封授的俺答所部大小酋長共63名,都頒給敕書。五月二十一日,在大同得勝堡外蒙漢聚集一堂舉行了隆重的封授典禮。至此明朝與俺答間的封貢關系順利實現。
由于政治上的統一,俺答、三娘子和歷代順義王,同歷任宣大總督王崇古、方逢時、吳兌、鄭洛等,都保持了十分友好的情誼。三娘子深明大義,先后輔佐三代順義王與明朝友好相處。她三十余年致力維護民族友好關系,因此深受蒙漢人民的愛戴。
三
土默特文化是蒙漢民族長期在嚴酷的自然環境里生存而創造出來的一種特殊地域文化。正如著名詩人巴·布林貝赫寫道:“來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純樸的粗獷的。清新的空氣,明麗的陽光,晶瑩的露水,給了他們單純的心靈;蒼茫的原野,狂暴的風雪,嚴峻的天空,給了他們粗獷的性格”[12](P85)。土默特文化內容豐富多彩,無論是物質方面的文化、精神方面的文化還是行為方面的文化,既有多樣性又有活躍性;無論是在生產中的交通用具還是日常生活里的飲食習俗,既有浪漫色調又有實用價值;無論是文學力作還是藝術精品,既有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又有對英雄人物的贊美和謳歌。諸如流行于晉蒙陜冀的二人臺,是集歌舞、曲藝、戲曲為一體的民間藝術。它是伴隨晉陜冀人民走西口到塞外謀生的移民史而形成的,是歷經悠悠歲月的時空磨礪,歷經熱愛它的蕓蕓百姓千錘百煉發展而成的綜合性民間藝術。
在這些藝術表演形式中,既有漢族的民歌、曲藝、舞蹈、絲竹樂、戲曲等成分,也有蒙古族音樂成分,如唱腔《海蓮花》、《阿拉奔花》、《四季花》、《盼五更》、《小牧牛》、《栽柳樹》等,牌子曲《森吉德瑪》、《四公主》、《巴音杭蓋》等就是其中的例子。歌唱和道白就用蒙漢兩種語言混合起來表演。如《親家翁相會》的表演中,臺詞里就有:
瑪奈(蒙語,“我的”意思)到了塔奈(蒙語,“您”的意思)家,黃油烙餅奶子茶。正趕上塔奈念經“巴雅爾拉”(蒙語,“喜慶”的意思)!中午飯更排場,瑪奈安在首座上,眾人敬酒我緊喝,放下筷子吃“五叉”(蒙古族最好的宴席食品,又稱“羊背子”)。你看瑪奈多喜色?/塔奈到了瑪奈家,正遇瑪奈不在家。瑪奈的腦亥(蒙語,“狗”的意思)咬塔奈,塔奈掏出大煙袋,狠狠地打了它的“討勞蓋”(蒙語,“頭”的意思)。
在塞外土默川上,蒙漢通婚,結成兒女親家,因為言語互相不通,親家們很少來往。《親家翁相遇》反映的故事情節,主要描述漢族親家翁向蒙族親家翁道出沒有很好款待他的話。再如蒙古族民間藝人老雙羊在演唱走西口時,其蒙漢語混合道白:
從家出口外,盲目來到妥妥岱(托克托縣),面向青山往北邁,走五申,過陜蓋,胡游亂闖到大岱。道路生,緊問訊,晚上住在大板升。蒙老鄉,真厚誠,莫把咱們當外人,滾奶茶,吃肉粥,暖炕睡得熱呼呼。進了土默川,不愁吃與穿。烏拉(蒙語“山”的意思)高,崗勒(蒙語是“河川”的意思)灣,海海漫漫的米糧川。牛羊肥,莊稼寬,逃難人見了心喜歡。
一走走到山湖灣,碰見兩個韃老板(是指蒙民老婦人),她們說話我不懂,只好比劃問安寧。有水請你給一碗,我要解渴把路趕,塔奈(蒙語“您”的意思)勿圪(蒙語“話”的意思)米德貴(蒙語“不知道”的意思)“忽爾登雅步”(蒙語是“快走”的意思)指向西,手指口渴嗓子干,她卻給了一碗酸酪旦(蒙民制成的乳制品——干酪)。
流傳在土默川一帶的山曲民歌也吸收了“腦包”(蒙古語,即隆起的高地)、“灰塌二胡”(蒙古語,冷落凄涼的意思)、“哈苜爾”(蒙古語,即白圪針)等蒙古族慣用語,如“山藥皮皮蓋腦包,誰給俺們管媒天火燒”;“遠遠瞭見他家的門,灰塌二胡死下個人”;“哈蟆口爐爐燒哈苜爾,活到哪影兒算哪影兒”;“哥哥走在那些高山疙瘩瘩唰哩唰朗割莜麥,妹妹走在那些半山坡坡蛤蟆蟆戒指指珊紅珠珠銀手鐲鐲唰鈴鈴唰啦啦刨山藥”。后句里的“蛤蟆戒指”、“珊紅珠珠”、“銀手鐲鐲”及象聲詞實際上是對塞外婦女首飾特征的生動描繪。“十月里狐子冰灘上臥,扔下了妹妹無人理”;“你走在口外只管了你,提起你走口外我心難過”;“人家回來你不回,你在那口外刮野鬼”;“西包頭紅火人又多,顧了你紅火忘了我”;“大青山山上臥白云,難活不過人想人”;“上畔畔葫蘆下畔畔瓜,娶下了媳婦守不成家”;“你在東來我走西,天河水隔兩頭起”;“萬般出在無其奈,扔下小妹妹走口外”。[13](P344~394)民歌、二人臺這種富于藝術感染力的作品長期以來一直流傳在土默川這個蒙漢雜居地區,起了蒙漢文化交流的作用。為擴大與中原地區聯系,進一步促進蒙漢文化交流,草原民族還非常注重醫學、建筑、音樂、舞蹈、剪紙、繪畫、工藝美術、禮儀祭祀、時令節日、民俗風情、天文歷法等,而且成果卓著。
土默特地區是歷史上中原農耕經濟文化與塞外游牧經濟文化交流、交融的一個窗口,通過這個窗口,使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有了進一步聯系、碰撞、融匯、貫通,相互補充,共同發展,形成以貿易交往為紐帶的密切關系。在客觀上起到了消除民族隔閡、加強民族之間理解和團結的作用,進而增強了北方兄弟民族與中原地區的凝聚力。
旅蒙商在將中原的茶葉、糧食、布匹等輸入蒙古各地的同時,還把草原上的土特產品運到中原各地,從而為中原各地農耕、運輸業提供大量畜力,為軍事用途提供了畜力,為手工業生產提供了原料。另外,旅蒙商在走屯串營流動貿易時,還把中原的中草藥和針炙等醫藥知識,帶往缺醫少藥的蒙古草原,他們在與蒙古牧民做買賣的同時,遇到蒙古人生病和牲畜疾疫時,還用針炙、中藥為牧民治療一些常見病,為病畜提供醫療,這樣不僅有利于人畜的健康保護,同時也加深了蒙漢民族間的感情溝通。商販還將中原地區的書籍帶到草原牧區,傳播了中原文化。同時,旅蒙商為便于與蒙古人做生意,必須不斷學習蒙語和蒙古文字,通曉蒙古人的生活習慣和風土人情,學習了與畜牧業有關的經驗和技術,然后又帶回內地交流,從而促進蒙、漢諸民族之間文化、經濟交流發展。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委派兵部侍郎貽谷為督辦蒙旗墾務大臣,開始了大規模官辦墾務。貽谷坐鎮歸綏,設立辦理河東河西十二臺站土地墾務的殺虎口臺站地墾務總局、分局和墾務公司等機關,逐步清丈放墾了察哈爾八旗和歸化土默特旗的土地。殺虎口臺站地墾務總局的設立,不但使土默特地區社會的政治、經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引起了放墾區的蒙古族人民在生產、生活和風俗習慣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隨著放墾區農業生產的發展,許多蒙古族人民逐漸放棄以牧為主的經營方式,轉向以農業為主或半農半牧的生產經營方式。蒙漢族人民在共同的生產勞動中,通過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提高了農牧業生產的技能。在蒙漢雜居地區多種經濟的發展,在客觀上也改變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習慣。在居住方面,出現了土木結構的蒙古包和漢式平房;在飲食方面,多以谷物蔬菜為主,輔以肉食與乳制品,并逐漸習慣飲紅茶,喝糧食酒;在服飾方面,逐漸吸收當地漢族農民的習慣,開始穿布鞋、布衫,甚至連以前最講究的發式也不大講究了。
放墾區蒙古族人民生活上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蒙古族人民風俗習慣的變化。首先是節日與祭祀的變化,放墾前的蒙古族人民有祭天、祭風、祭雨、祭雷、祭神、祭星、祭火、祭敖包等祭禮。放墾后接受了漢族人民的習慣,祭龍王、祭土地廟、祭孔廟、過端午節、中秋節、小孩過生日、老人過六十大壽、過年時貼門神、供財神等;其次就是婚姻制度的變化,放墾前的蒙古族人民一般在同族之間遠娶遠嫁,不能與其他民族通婚。放墾后的蒙古族人民打破了民族界限,蒙漢通婚的家庭開始出現了。此外,在喪葬禮儀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化,由原來的“風葬、樹葬、天葬,改變為土葬”[14]。
殺虎口臺站地墾務總局的設立,盡管解決了大批漢族饑民的生計問題,也方便了蒙古牧民的糧食供應,但是,臺站地的放墾也付出了很高的生態成本,帶來嚴重的生態后果。由于大面積的放墾開荒,導致整個土默特地區生態系統的失調:水土流失面積逐年增加,降雨量普遍減少,各種自然災害周期縮短,災情越來越嚴重,沙塵暴爆發的次數、強度以及襲擊的范圍有逐年上升和擴大之勢。
文化的開放和交流是文化發展的動力。一個地區民族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從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中汲取營養,古往今來,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吸收從來沒有停止過。保持完全“原汁原味”、封閉保守的文化傳統的民族是發展不起來的,更無從去談現代化。民族要發展,社會要發展,就必須與外界建立廣泛的聯系與交往,看到差距,明確歷史方位,尋找與時代的契合點,這樣的文化其內涵會更豐富,內容將更優秀,更加適應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更富有生命力,更易于被其他民族所接納,文化整合能力更強,從而形成文化發展的良性循環。同時對其他民族文化中適應現代社會生產生活的新觀念、新的思維方式,要努力學習、借鑒并吸收,從而建立健康合理的文化機制,不斷提高科學文化素質和理性思維能力。
結 語
土默特文化是土默川地域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是北方民族文化寶庫的瑰寶。其民族特色和鄉土氣息,是祖國文化的一顆璀燦的明珠。明清時期土默特地區社會文化風貌的變化,是蒙漢長期交往,兩種文化融合之必然。該地區既有中原文化傳統,又有濃厚蒙古族特色,新型地域文化的形成,突出體現了中華文化多元匯聚,一體化發展的總趨勢。進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土默特文化對于人們充分了解和認識北方民族文化特色,傳承與弘揚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蒙漢民族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創造文化的活動和過程其實是體現北方民族的價值追求和價值觀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化積累是文化發展的量變,文化創新是文化發展的質變。文化繼承也叫文化積累,通過對民族內部文化和外來優秀文化的積累,推動人類文化活動從有限向無限發展”[15](P11)。土默特文化是蒙漢民族的多元并存價值觀在自然環境中的外化形式,在土默特文化生態體系中,土默特文化生態觀創新發展的關鍵就是在核心價值觀指導下實現一種文化價值觀的創新。當前我們面臨著多元并存的時代,要使土默特文化生態永遠充滿生機活力,需要我們不斷加強土默特文化生態價值觀的創新理念。
[1]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
[2]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卷三一六)[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崔九思.萬歷武功錄[M].四庫禁毀書叢刊表.
[4](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M].北京:中華書局,1977.
[5]蕭大亨.夷俗記[M].山東:齊魯書社,1997.
[6]王鳴鶴.登壇必究(卷三十七)[M].清(1644-1911)木活字印本.
[7]明神宗實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王士奇.三云籌俎考[M].臺北:臺北廣文書局,1963.
[9]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卷四三四) [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0](明)俺答.北狄順義王俺答等臣貢表文[M].景明刊本.
[11]方逢時.大隱樓集(卷十一)[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
[12]大地的引力[A].巴·布林貝赫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13]閆天靈.漢族移民與近代內蒙古社會變遷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4]劉海源.內蒙古墾務研究[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15]鄭海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我國文化創新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