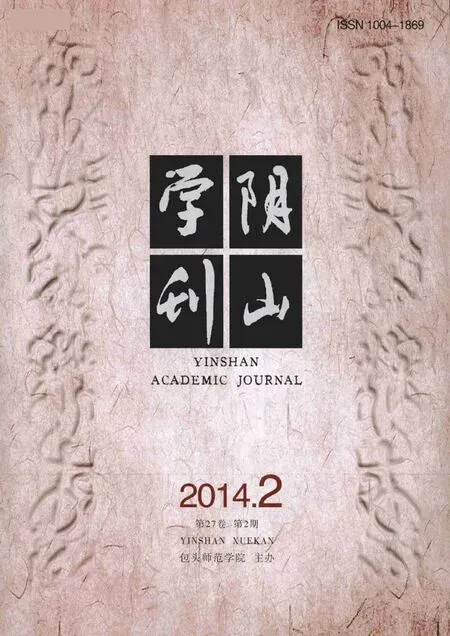論薩都剌詩歌中“雁情”的文化意蘊
王 海 香,溫 斌
(包頭師范學院 文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30)
在元代的詩壇,少數民族作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回族詩人薩都刺作為其中的杰出代表,因其詩作獨具魅力而聲名顯著,楊鐮稱之為“元代詩壇冠冕”[1](P1)。薩都剌,字天賜,號直齋,祖上原居于西域偏遠小國,自其祖父思蘭不花和父親阿魯赤開始,于蒙古鐵騎征服西域各國之際從軍往東而來,獲得戰功得以留鎮云、代之地,最終定居于雁門(今山西省代縣)。薩都剌的詩內容題材豐富,風格清新綺麗,其中很多詩詞都是在其羈旅途中所作,或為謀生而經商異鄉,或為官而遠游,或為遭謫而適他鄉,或為山川江海之美得到漫游,由于長期居于異鄉、漂泊在外,難免要產生出復雜的思鄉情感。于是鴻雁便成了敏感而多情的詩人寄托人生羈旅傷感情懷的對象。在《雁門集》中四十八首詩都涉及到雁,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因為雁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象征,一種特殊的意象符號融進了詩人的生命中。
一、雁在薩都剌詩中的情感意象
中國古代歷史上詩歌的意象眾多,雁是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一種重要意象。作為隨季節而動的候鳥,它的遷徙特性和古人思鄉情感兩者極為契合。漂泊在外的人們,常常由雁聯想到自己獨處異鄉、漂泊無依的境遇,從而雁就成了詩人思鄉懷親的寄托。雁可以成為懷鄉情思的載體,表現出安土重遷的農業民族的天性;也可作為人們倫理道德的代表,表現親友弟兄恭讓溫良、謹守雁序的群體規則;也可當作愛人眷戀癡腸的信使與寄托,表現出人世間男女別離的不舍深情;也可作為憂國憂民的情感符號,寄托了對廣大人民的關切和同情;也可以作為塞外邊疆的代表意象,展示了氣勢磅礴的北塞風光;同時也可以作為卓立于世的有識之士的形象寄托,表現了不與世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雁成為了古代文人吐露內心悲苦情韻的一個重要意象,作為元朝少數民族詩人薩都剌對雁也有著一種獨特情懷,寄情于雁來表達自己內心深處復雜的思想感情。
(一)羈旅哀愁之情。在薩都剌的詩中,羈旅之作尤多,這和他的長期漂泊異鄉有關,詩人遠離北國長奔波在南方,多年的離家使作者產生了很多思鄉懷親之感,而在這些作品之中屢次出現雁這種意象,從而雁就成為了詩人寄托情感的重要對象。自古雁就與“漂泊”結下了不解之緣,作為雁這種候鳥,它每年“木落時來,花開時歸”,在塞北沙漠與楚澤瀟湘之間往返,由此雁象征的是離愁別緒,是歸而不得的鄉思之感,更是聚而不能的思念之情。薩都剌在《寓棲云》中這樣寫道:“瀟瀟風雨客心孤,且盡尊前酒一壺。夜半酒醒愁又到,一聲白雁下平湖。”這首詩是詩人獨往鎮江赴職之時,半夜醒酒,愁緒涌上心頭,而雁之叫聲尤讓詩人在這個夜晚倍感孤獨,更加思念遠方的親人。在動蕩的政治背景下,詩人的前途是未知的,“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詩人是羨慕雁的,因為它們有歸期。又如在《過廣陵驛》中:“秋風江上芙蓉老,階下數株黃菊鮮。落葉正飛揚子渡,行人又上廣陵船。寒砧萬戶月如水,老雁一聲霜滿天。自笑棲遲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燈前”。詩人做此詩時已有七十五歲高齡,其年秋詩人遠赴江南諸道行臺侍御史,途經廣陵,詩人仍是過客奔波在官途之上。看著“黃菊”聽著“雁鳴”,詩人的心事愁思有增無減,十年中漂泊在異鄉,目睹世間之疾苦,官場之黑暗,皇室爭權之殘酷,這些都讓詩人對官場的生活深深地厭倦。看著秋天的老雁,他更加覺得自己如老雁一般仿佛永遠沒有固定的棲身之所,永遠如浮云般在天涯間漂泊流浪。“淮海客”、“云中雁”正是詩人飄零跌蕩人生的真實寫照。
(二)同根相思之情。雁,自古即被視為有德操之鳥。晉羊祜《雁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后不越序。齊力不期而并至,同趣不要而自聚”[2](P109~110)。這是對雁之德行的進一步肯定,而“雁德”也是作者想要推崇的人之倫理觀念。大雁飛行,長幼有序,秩序井然,今天我們用“雁行”來規范人們的倫理品行,來表現社會中的倫理行為的尊卑有序。薩都剌對雁的這種德行進行吸收而又有所發展。在其《九月七日舟次寶應縣雨中與天與弟別》中:“解纜不忍發,船頭雨濕衣。汝兄猶是客,吾弟獨先歸。行役關河遠,虛名骨肉稀。如何淮上雁,不做一行飛”。由于大雁在北去南來的飛行過程中,排成“一”字或“人”字,有秩序地群體前行。但如今詩中卻寫到“不做一行飛”,這是將自己與弟弟比喻為那淮上雁群,原本兩人相依為伴,如今弟弟回歸故里,自己卻要遠赴關河任職,因而不得不分開。詩人為了生活,為了施展自己的抱負,以致骨肉分離,有家不能還,這讓詩人心中無比羨慕那淮上的雁群,因為他們可以一起結伴飛行不離不棄,而現在的自己就仿佛那離群的孤雁,凄慘可憐。用雁群來表達兄弟之情的在前人詩中已多有提及,初唐韋承慶《南中詠雁詩》題作南行別弟:“萬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表達了詩人在分別之際的依依不舍和渴望與兄弟再相聚的心情。薩的這首詩中詠雁喻情手法與這種初唐《南中詠雁詩》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大雁不僅作為一種倫理象征被作者接納,還作為一種傳遞思念的載體出現在作者的詩中。交通不發達的古代,人只能居于一地,鴻雁卻可以往返于萬里之間,至此大雁成為了寄托思鄉懷人之情的載體。古代詩人通常將鴻雁借代為信使,并通過托其對書信的傳遞來寄托濃濃的思鄉情感。李商隱在《離思》中寫道:“氣盡《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峽云尋不得,溝水欲如何。朔雁傳書絕,湘篁染淚多。無由見顏色,還自托微波”。此處雁這一意象寄托了詩人的相思之情,大雁傳遞書信沒了蹤跡,湘妃竹都感嘆掉下淚水,詩人將自己的無盡相思之情托于鴻雁,期盼收到遠方親人的只字片語。作為少數民族詩人的薩都剌也用“鴻雁”傳遞自己對親人的思念。在其《寄舍弟天與》中有:“鴻雁飛南北,關河隔弟兄。水通鄖子國,舟泊漢陽城。落木風蕭下,高秋鼓角聲。故人如問訊,為我道鄉情”。鴻雁往南又飛返北,在吳、楚經商的詩人已和弟弟分離一段時間,眼望著天空往返南北之大雁,期盼它們能將他的思念傳送給自己的親人。
(三)憂國憂民之情。自古以來就有通過雁來比喻災難離散的百姓。在《詩序》中:“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3](P1799)。后來逐漸將災難離散的百姓稱為鴻雁,又或哀鴻。宋代楊時《哀鴻》中有“哀鴻常苦饑,悲鳴垂其翼”。這首詩中鴻雁哀鳴,飽受饑苦,借此暗喻百姓流離失所,無所依靠,如哀鴻一般徘徊在生死邊緣,時常有“路有凍死骨”之慘狀的出現,此處的鴻雁實質就是困境中底層百姓的化身。生活在元朝中后期的薩都剌,他經歷了元朝生活在在由盛轉衰的整個時期,他目睹了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在災荒戰亂中人民在生死邊緣掙扎,從而薩都剌寫下了《鬻女謠》這首詩,“傳聞關陜尤可憂,旱荒不獨東南州。枯魚吐沫澤雁叫,嗷嗷待食何時休。”這首詩通過“雁”這一意象真實地再現了元中后期戰亂災荒不斷,稅收加重,人民生活困苦的現實,詩人把雁與人的情感相結合,借雁之危難抒發相應的感受,表達了一種對下層人民處境的憐憫和同情。而與薩都剌同一時期的很多文人大夫,在當時復雜的政治背景下,很多詩作都大都遠嫌避禍,三緘其口,清人顧嗣立所編《元詩選》中虞集寫道:“道路備攘掠,所過凈于掃。縛人夜送軍,吏卒何草草”[4](P42~48)。這是在其近400首詩中,僅有涉及到的南征軍隊擾民行徑,而稍稍描述了當時黑暗的政治環境。所以薩都剌的詩中卻直接揭露當時統治者的殘暴,政治的黑暗,其深摯的憂國憂民之情不得不被后人稱贊。
(四)民族豪放之情。古代的大雁往往與大漠、長河這樣的意象相聯系,烘托一種雄壯曠野的北塞邊疆的宏偉景象。在王維《使至塞上》中有“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細膩描寫。這首詩是詩人遠赴西河途中之作。雖然通過眾多意象勾勒出了一幅大氣磅礴的塞外畫面,但是仍有失意情緒流露。這種失意在“單車”中可以表現出來,在這里歸雁入胡乃回歸舊巢,而詩人正與之相反,遠離家鄉,多了凄涼之意。而在薩都剌的詩中,不管是送別詩還是詠物詩往往又多了一份豪放之情。如《泊舟黃河口登岸試弓》:“泊舟黃河口,登岸試長弓。控弦滿明月,脫箭出秋風。旋拂衣上露,仰射天邊鴻。詞人多膽氣,誰許萬夫雄”。這首詩將勇士舉弓搭射的颯爽英姿生動如畫地表現出來,體現了俊逸超脫、豪邁雄壯的草原特質。薩都剌將雁意象融入到了草原民族所特有的粗獷、雄健的性格之中。在《北上別鄭文學》中:“朔風吹散鴻雁群,郎君上馬氣如云”。這里的雁群實質是比喻自己與好友的即將別離,但是仍表現“氣如云”般的豪壯。又如“西風不定雁初度,落木無邊江自流”(《九日登石頭城》),詩人用粗線條勾勒了一副深秋之景,此時詩人身居南方,將北地的鴻雁高飛與南方的潺潺流水進行融合。雖然繪制的是南國風景,卻隱含有北人的豪放粗獷,這與江南的小橋流水人家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五)高潔孤傲之情。孤雁即為孤鴻,是士人對于道德清高、思想獨醒的孤獨者形象的一種精神寄托。唐代李商隱《夕陽樓》中:“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這里的孤鴻即指不同流俗,志行高潔的有識之士。這樣的“孤雁”在薩都剌的《泊吳江夜見孤雁》中也出現過:“明月麗長空,水凈秋宵永。悄無蹤烏鵲南飛,但見孤鴻影。”當時詩人的仕途并不順暢,干文傳在《雁門集》序中說薩都剌“以彈劾權貴,左遷淮西江北道廉訪司”,詩人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異鄉漂泊中度過,常年和親人朋天各一方。在這首詩中孤雁身上融注了作者的深情,甚至可以說這只孤雁就是作者的影子,“孤鴻”的驚恐不安,孑然無助、渺然無適以及無枝可依。這里的“孤鴻”正是詩人自己漂泊無依而又怵惕不安的真實寫照,詩人與雁,早已渾然一體了,如孤雁一般孑然一身,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同時又希望自己的抱負得以施展。
二、薩都剌對雁的獨特情懷成因
詩人在詩文中多次提到雁,把自己的復雜情感也融入了雁意象中。雁頻繁出現在詩人的生活中,究其原因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加以探究。
(一)詩人的漂泊經歷
1.早期的經商歷程。薩都剌早期有過一段從商的艱難經歷,作為家中長子,他必須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重任。《溪行中秋玩月并序》中自序“余乃薩氏子,家無田,囊無儲”。在其詩歌自畫像《醉歌行》中又有“嗟余識字事轉多,家口相煎百憂集”。從這首詩中可看到詩人當時家庭生活的窘迫以及對現實的無奈。從歷史的背景來看,元朝滅南宋統一中國后,廢除科舉制度長達幾十年,像薩都剌這樣的讀書人沒有進入仕途的機會。由于生活所迫,詩人最后不得不選擇到南方吳、楚等地經商謀生,常年疲于奔命,對現實充滿了無奈。在一個人獨自在異鄉漂泊期間,每每有思鄉情懷的時候,雁的出現就增添了詩人的思鄉之愁,同時也把雁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希望它能傳遞自己對家鄉親人的思念的之情。
2.入仕后的宦游生活。薩都剌從沒有放棄通過入仕來實現自己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詔令恢復科舉,這無疑是給了當時的讀書人施展才華的機會,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薩都剌于泰定四年三甲進士及第。當時薩都剌早已年逾半百,卻從未懷疑這是自己一展抱負的大好機會,這在其詩作中對于自己內心的強烈情感有所表達。《丁卯及第謝恩崇天門》有“卿云五彩中天見,圣澤千年此日遭”;在《賜恩榮宴》又有 “小臣涓滴皆君賜,唯有丹心答圣明”。但是入仕后的薩都剌并沒有機會展現自己的宏圖大志,由于元朝中后期政治環境的黑暗,皇室的自相殘殺,薩都剌就像汪洋中的一葉小舟,在政局如暴風驟雨般的大元王朝統治下開始了他二十多年的游宦生涯。這個時期的薩都剌一直在距家千里之外的南方游歷,期間遭過多次貶謫,仿佛是那離群的孤雁倍感落寞,無比渴望能回到自己的親友身邊。唐代詩人白居易《放旅雁》中有“我本北人今譴謫,人鳥雖殊同是客”[5](P323)。詩的內容也恰恰體現了薩都剌當時的處境,一直身處異鄉的詩人,常常由雁想到自身,又由自身反觀于雁,與雁為伴作客他鄉。而這樣的漂泊的身份讓詩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內心充滿的孤獨和凄苦。
(二)儒家文化的影響
在元代這個特殊的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游牧民族強悍勇猛的民族性格所形成的開放性和進取性,強烈地震撼和沖擊著中原古老的傳統文化,在內外條件的推動下,一個文化并存、文化融合的時代逐漸形成。這一時期很多文人作品中都彰顯著民族交融的文化精神。元朝建立后,統治者大力提倡學習漢文化,薩都剌自小隨祖輩遷居中原,“舍弓馬而事詩書”,不再追求戎馬生涯,而是專心投入到了漢文化的學習中;早期的經商和后期的游宦生涯詩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南方,南方多是漢人居住的地方,從而詩人的思想在這期間受漢文化影響很大。他雖出身于回教世家,卻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薩都刺在《溪行中秋玩月并序》中自稱“有子在官名在儒”,以“儒”自居。生活在元代的薩都刺,如果說儒學對他有什么影響的話,那就是他接受了“忠孝仁義”的儒學觀念。對君要忠,在詩中時有流露。剛中進士,他要表達“小臣涓滴皆君賜,惟有丹心答圣明”的強烈情感,所以在《江上聞笛》中“銀河耿耿波茫茫,雁奴打更沙溆旁”在這里詩人以雁奴自喻,表明了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即雁群作為國家群體的隱喻,雁奴作為忠臣凈臣的化身。有關雁的文化認同在文人心理中是代代傳承的,雁以其極強的群體組織秩序成為宗法社會倫理范式的對應象征物。對君要忠,對母要孝,對兄弟要愛,這也是天地之正理,儒家文化之精髓。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安土重遷這一思想已深深影響了詩人,生活穩定,盡孝膝下成為詩人的理想生活,在《溪行中秋玩月》序中詩人認為“昔人所謂宦游之樂不如奉親之樂”這一句足以表明詩人希望侍母親于左右,一家人相聚一起;對于兄弟,也是篤于手足之情的。詩人在他的詩作中多次把情感寄托于雁,這與儒家的倫理觀念是分不開的的,古人基于宗法制的血緣倫理關系,一向講究家族的內部秩序的和諧,這是自古以來封建統治下小農經濟體制的需要。正如雁陣飛行的次第有序,直觀又生動地展示出群體互助的情景,這又被古人合理化地解釋為倫理楷模,雖然社會現實是殘酷的,但詩人內心是無比渴望群體的回歸,這也進一步體現出鴻雁活動的群體秩序所代表的民族強烈的群體意識在詩人生命中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在詩中多次用雁來表達自己的復雜情感,古詩詞中“鴻雁”意象也是詩人主觀情意與客觀物象結合的產物。這種結合體現了薩都剌的心態、情感、人生態度、生活體驗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心理。在傳統倫理文化的大背景中,不管是少數民族還漢民族,他們都會有這共同的民族情結——作為游子的懷親思鄉之情、作為知音好友的關切之情、作為同根兄弟的手足之情、作為孤我在寂寞獨處時候的落寞之情,這些復雜的情感都在傳統的雁意象中,通過人們的重溫和再造,進一步滿足人情感上的寄托。
[1]馬信.從薩都刺詩歌創作看其心態演變[J].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2]張潔,毛振華.論古典詩詞中的雁陣意象[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
[3]辭源[Z].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4]曾曉玲.從薩都剌詩歌看元朝政治的衰變[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2).
[5]顧學頡.白居易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責任編輯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