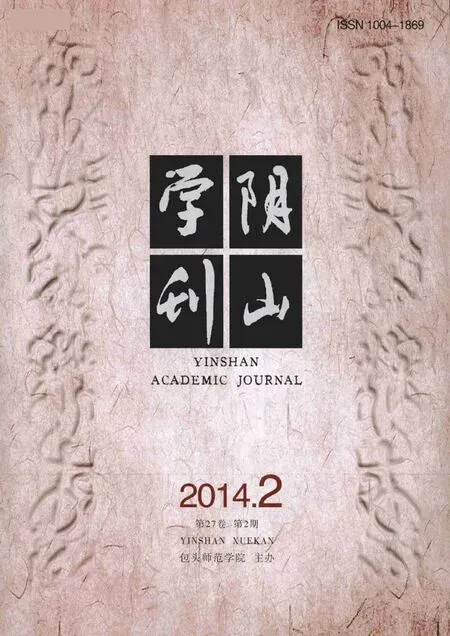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悲劇衰亡”話語(yǔ)的興起試探
張 乾 坤
(湖南理工學(xué)院 中文學(xué)院,湖南 岳陽(yáng) 414006)
“悲劇衰亡”話語(yǔ)是風(fēng)靡20世紀(jì)西方戲劇知識(shí)界的著名論調(diào)。《大美百科全書》在界說(shuō)“悲劇”一詞時(shí)明確指出:“二十世紀(jì)有關(guān)悲劇的許多批評(píng)性論著探討的是其衰落和終結(jié)。”[1](P30)無(wú)獨(dú)有偶,2002年英國(guó)評(píng)論家霍華德·布倫頓在英國(guó)著名的《衛(wèi)報(bào)》上撰文評(píng)論特里·伊格爾頓的《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時(shí)開篇就認(rèn)為:“悲劇衰亡問(wèn)題是當(dāng)代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中一個(gè)反復(fù)被探討的問(wèn)題。”[2]應(yīng)該說(shuō),“悲劇衰亡”話語(yǔ)的產(chǎn)生絕不是偶然,必然有其特定原因。這除了與20世紀(jì)現(xiàn)代悲劇創(chuàng)作整體狀況有關(guān)之外,至少還有以下四個(gè)方面的原因。
首先,其直接原因是受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出悲劇滅亡問(wèn)題的啟發(fā)。學(xué)者在談到“悲劇衰亡”這個(gè)話題時(shí),一般都是將其追溯到尼采,而不是通常所認(rèn)為黑格爾在自己的哲學(xué)框架內(nèi)提出哲學(xué)最終取代藝術(shù)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以及別林斯基在《戲劇詩(shī)》中提到的觀點(diǎn),即所謂“我們俄國(guó)的悲劇是從普希金開始,而隨著他而死亡”。例如,沃爾特·庫(kù)夫曼認(rèn)為:“悲劇死亡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尼采。……二戰(zhàn)以來(lái),尼采關(guān)于悲劇死亡的論述越來(lái)越有影響,他的觀點(diǎn)幾乎成為了一個(gè)常識(shí)。”[3](P163~164)盡管從悲劇理論史上來(lái)看,尼采并非是提及“悲劇衰亡”問(wèn)題的第一人,但他的觀點(diǎn)對(duì)后世“悲劇衰亡”論者產(chǎn)生的直接啟示作用不容小覷。
其次,來(lái)自悲劇傳統(tǒng)的強(qiáng)大壓力。一方面,雅典時(shí)代和伊麗莎白時(shí)代悲劇創(chuàng)作取得了高不可及的輝煌成就,給后世劇作家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這也就是美國(guó)批評(píng)家布魯姆提出的“影響的焦慮”問(wèn)題,即后輩劇作家(強(qiáng)者)作為“兒子”形象,始終生活在“父親”形象籠罩之下,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無(wú)形的壓抑,患有抑郁癥或焦慮癥。著名的“悲劇衰亡”者喬治·斯坦納曾經(jīng)說(shuō):“雅典和伊麗莎白的過(guò)去給將來(lái)的戲劇想象力投下了很長(zhǎng)的陰影。屈萊頓是無(wú)數(shù)作家中第一個(gè)發(fā)現(xiàn)在他們自己和戲劇發(fā)明的行動(dòng)之間存在著心理上的障礙。昔日偉大的成就看起來(lái)是無(wú)法超越了。”[4](P43~44)不過(guò),比較有意思的是,布魯姆認(rèn)為,他所提出的“逆反式”批評(píng)原則不適用于莎士比亞,盡管有自己的理由。但是,這無(wú)疑也從側(cè)面表現(xiàn)出布魯姆自身“影響的焦慮”,即英語(yǔ)詩(shī)中莎士比亞是一個(gè)比父親形象還強(qiáng)大的超人,后世詩(shī)人無(wú)法通過(guò)“詩(shī)的有意誤讀”來(lái)挑戰(zhàn)他的王者地位,只能在巨人的陰影之下抑郁而生。作為一名最擅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布魯姆身上流露出的“影響的焦慮”尚且無(wú)法遮掩,更不用說(shuō)那些膜拜傳統(tǒng)、跟隨傳統(tǒng)亦步亦趨的人了。另一方面,亞里士多德悲劇理論超越時(shí)空的絕對(duì)影響,已經(jīng)演變成了一種威廉斯所說(shuō)的“意識(shí)形態(tài)”。正如人們一提到悲劇立刻使人想起古希臘悲劇和莎士比亞悲劇一樣,當(dāng)有人提到悲劇理論時(shí),很快就使人聯(lián)想到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談到《詩(shī)學(xué)》時(shí)說(shuō):“亞里斯多德是第一個(gè)以獨(dú)立體系闡明美學(xué)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5](P124)然而無(wú)論《詩(shī)學(xué)》的影響持續(xù)的時(shí)間有多長(zhǎng),波及的范圍有多廣,它畢竟只是古希臘悲劇實(shí)踐的理論抽象與概括,理所當(dāng)然地具有一定的理論適應(yīng)范圍。正如在本雅明看來(lái),它只能具有“古代的權(quán)威性”,對(duì)于德國(guó)悲悼劇而言,其影響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本雅明批評(píng)道:“評(píng)論家們總是想要把古希臘悲劇的因素——悲劇情節(jié)、悲劇英雄、悲劇死亡——看作悲悼劇的本質(zhì)因素,不管這些因素在缺乏理解力的模仿者手里受到多大的扭曲。另一方面——而這對(duì)于藝術(shù)哲學(xué)的批評(píng)史將尤為重要——悲劇,即古希臘悲劇,一直被看作早期的悲悼劇形式,以后來(lái)的悲悼劇密切相關(guān)。據(jù)此,悲劇哲學(xué)便作為世界的道德秩序理論在一個(gè)普遍化了的情感系統(tǒng)中發(fā)展起來(lái),而不涉及歷史內(nèi)容。”[6](P72)與本雅明在這里所說(shuō)的“評(píng)論家們”一樣,絕大多數(shù)“悲劇衰亡”者也都自覺(jué)地或不自覺(jué)地受到了以《詩(shī)學(xué)》為代表的悲劇理論“真正強(qiáng)大的意識(shí)形態(tài)”支配。威廉斯指出:“悲劇理論之所以有趣,主要是因?yàn)橐粋€(gè)具體文化的形態(tài)和結(jié)構(gòu)往往能夠通過(guò)它而得到深刻的體現(xiàn)。然而,如果我們把它看作對(duì)某個(gè)單一的永久事實(shí)的論述,那么,我們只能夠得出已經(jīng)包含在這一假定之中的形而上結(jié)論。這里最主要的假定涉及本質(zhì)永恒不變的普遍人性。”[7](P37)“悲劇衰亡”話語(yǔ)的論者們的失誤在于:沒(méi)有意識(shí)到《詩(shī)學(xué)》是與古希臘活生生的具體的文化形態(tài)和結(jié)構(gòu)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沒(méi)有意識(shí)到不同時(shí)代情感結(jié)構(gòu)的流動(dòng)性,靜止凝固地理解了《詩(shī)學(xué)》,錯(cuò)誤地將其當(dāng)作了衡量一切的永恒地普遍事實(shí)。
再次,就整體而言,現(xiàn)代戲劇理論家和批評(píng)家未能成功地建立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悲劇理論,也就是說(shuō),“未能成功地確定現(xiàn)代悲劇的性質(zhì)、主題內(nèi)容、表現(xiàn)形式、傳達(dá)方式、現(xiàn)實(shí)功能,也未能界定現(xiàn)代悲劇精神。”[8](P228)面對(duì)諸多的現(xiàn)代悲劇創(chuàng)作實(shí)踐,在比較有影響的悲劇理論文本缺席的情況之下,許多現(xiàn)代戲劇理論家和批評(píng)家頗為困惑。于是,有一部分學(xué)者嘗試重新闡釋《詩(shī)學(xué)》,使之成為現(xiàn)代版本。例如,批評(píng)家麥斯威爾·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試圖從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中抽出“突轉(zhuǎn)、有缺陷的英雄、卡塔西斯”三要素作為解釋現(xiàn)代悲劇的基石。然而,在JR·喬治·約斯特(JR.George Yost)看來(lái),麥斯威爾·安德森的做法并不成功,只是主觀的一廂情愿,并不符合亞里士多德的原意。[9](P147)更多的人則紛紛將目光直接投向了《詩(shī)學(xué)》,試圖從中尋找其理論依據(jù)。然而,這種做法在本雅明看來(lái),是“不涉及歷史內(nèi)容”,排斥“歷史哲學(xué)”的做法。同樣,在雷蒙·威廉斯看來(lái),這是忽略悲劇中的情感結(jié)構(gòu),以古論今的做法,“悲劇理論原創(chuàng)性的部分主要出自十九世紀(jì),它先于現(xiàn)代悲劇的創(chuàng)作,后來(lái)又被受過(guò)學(xué)術(shù)訓(xùn)練的人系統(tǒng)化了。這些學(xué)者習(xí)慣以古論今,并且將批評(píng)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shí)踐分離開來(lái)。”[7](P38)
最后,現(xiàn)代文化批判的一種策略。在分析悲劇(精神)滅亡的原因時(shí),尼采認(rèn)為,無(wú)論是歐里庇得斯還是瓦格納,充其量只是摧枯拉朽,急劇地加速了希臘悲劇(精神)的衰落,而真正揮起屠刀、砍殺希臘悲劇(精神)的罪魁禍?zhǔn)啄耸翘K格拉底、黑格爾等人所象征的理性。希臘悲劇(精神)的滅亡過(guò)程,實(shí)際上就是理性逐漸排擠希臘悲劇的酒神精神的過(guò)程。因而,悲劇是與理性及其文化形式是對(duì)立的。尼采論述悲劇的滅亡,內(nèi)在旨趣是為了抨擊蘇格拉底、黑格爾等人所象征的理性及其文化表征。尼采借談?wù)摫瘎∷劳鲈捳Z(yǔ)來(lái)批判、否定現(xiàn)代理性及其文化形式的策略在后續(xù)論者那里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延續(xù)。例如,格羅斯曼在分析現(xiàn)代人為何創(chuàng)作不出悲劇時(shí)認(rèn)為,現(xiàn)代社會(huì)是一個(gè)理性文明的時(shí)代,人們強(qiáng)烈的情感受到嚴(yán)格節(jié)制,甚至一言一行都受到社會(huì)法律的嚴(yán)格約束。由于理性文明的普遍節(jié)制與約束,現(xiàn)代人喪失了昔日的激情,情感變得更加理智與冷靜。由于理性文明的昌盛,悲劇失去了立足之地。同樣,克魯契也認(rèn)為,啟蒙運(yùn)動(dòng)之后,尤其是20世紀(jì)之交,人類生活在一個(gè)異質(zhì)的世界中,“上帝和人以及自然都以某種方式在世紀(jì)的轉(zhuǎn)換過(guò)程中退化了”。在這樣一個(gè)異質(zhì)的世界里,人類的高貴觀念已經(jīng)蕩然無(wú)存。即使我們能夠部分地想象高貴的觀念,但也無(wú)法理解它。由于缺乏高貴的觀念,我們只能閱讀悲劇但不能寫作悲劇。由此可見(jiàn),無(wú)論是格羅斯曼還是克魯契,在言說(shuō)現(xiàn)代語(yǔ)境中悲劇的可能性時(shí),都著重分析批判了悲劇賴以存在的現(xiàn)代文化。誠(chéng)如蘇珊·桑塔格所說(shuō):“現(xiàn)代對(duì)悲劇之可能性的探討,不以文學(xué)分析的面目出現(xiàn),而或多或少假以文化診斷學(xué)之名。直到文學(xué)這一學(xué)科遭到經(jīng)驗(yàn)主義者和邏輯主義者的清洗以前,該學(xué)科一直侵占著以前歸屬于哲學(xué)的那種活力。情感、行為和信仰的現(xiàn)代困境試圖通過(guò)文學(xué)杰作的討論得出一個(gè)所以然來(lái)。”[10](P142)論者們否認(rèn)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悲劇的可能性,進(jìn)而極力鼓吹“悲劇衰亡”,實(shí)際上就是策略性地批判甚至否定悲劇得以依存的現(xiàn)代文化。
不容置疑,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早就涉足了“悲劇衰亡”問(wèn)題并展開了較為集中的研究,但在論及現(xiàn)代西方“悲劇衰亡”話語(yǔ)興起的時(shí)間時(shí),學(xué)術(shù)界普遍認(rèn)為它興起于20世紀(jì)30年代或是二戰(zhàn)之后。例如,陳瘦竹先生說(shuō):“從本世紀(jì)30年代特別是60年代以來(lái),歐美一些理論家對(duì)悲劇的前途持有悲觀態(tài)度,甚至提出‘悲劇衰亡’的論調(diào)。”[11](P300)與之稍微有所不同,陳世雄先生認(rèn)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戲劇理論界提出了‘悲劇衰亡’論。”[12](P35)然而有足夠的事實(shí)可證明,這些觀點(diǎn)都是錯(cuò)誤的。準(zhǔn)確地說(shuō),20世紀(jì)初“悲劇衰亡”話語(yǔ)在西方學(xué)術(shù)界就已經(jīng)相當(dāng)?shù)亓餍辛恕D菚r(shí)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伊迪絲·瑟爾·格羅斯曼、弗蘭克·勞倫斯·盧卡斯、約瑟夫·伍德·克魯契。
1906年,伊迪絲·瑟爾·格羅斯曼在《悲劇的衰亡》一文中認(rèn)為,悲劇在希臘和伊麗莎白時(shí)期達(dá)到了頂峰,并且創(chuàng)造了唯一完美的悲劇形式。但是,在伊麗莎白時(shí)期頂峰之后,悲劇歷經(jīng)兩個(gè)世紀(jì)的激昂言辭與嘩眾取寵之后,最終作為一種戲劇形式幾乎滅絕了。她指出,“悲劇衰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gè):一是小說(shuō)排擠了悲劇的地位。二是現(xiàn)代人“情感的衰退”。格羅斯曼認(rèn)為,雖然在現(xiàn)代社會(huì)里悲劇藝術(shù)已經(jīng)衰亡了,但也有例外。例如,在一些文明程度相對(duì)較弱的國(guó)家和地區(qū),如挪威、匈牙利、波蘭、俄國(guó)、南部非洲、澳大利亞,悲劇藝術(shù)依然比較繁榮。
格羅斯曼認(rèn)為,現(xiàn)代社會(huì)不能創(chuàng)作出悲劇藝術(shù)。因?yàn)楝F(xiàn)代文明社會(huì)不贊成或禁止強(qiáng)烈情感地表達(dá)。我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社會(huì)法律的嚴(yán)格約束。盡管格羅斯曼認(rèn)為悲劇藝術(shù)已經(jīng)衰亡了,但她認(rèn)為我們的時(shí)代仍然需要悲劇精神。其理由是,“生活在它的深層意義上來(lái)說(shuō)仍然是悲劇的。因?yàn)槿绻覀儧](méi)有意識(shí)到我們自己的限度和宇宙的法則時(shí),我們的所思所感仍然是盲目的。”[13](P850)
格羅斯曼大概是20世紀(jì)最早專門探討“悲劇衰亡”問(wèn)題的西方學(xué)者,她的《悲劇的衰亡》一文也幾乎都涉及到了后來(lái)“悲劇衰亡”話語(yǔ)論者所談?wù)摰暮诵膯?wèn)題。盡管如此,她的一些觀點(diǎn)的確很難讓人茍同:其一,她明顯地將結(jié)局的好壞與否作為了判斷是否是悲劇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這是極其狹隘的。就她所崇拜的古希臘悲劇來(lái)說(shuō),真正結(jié)局是不幸的還是比較少。據(jù)伊格爾頓的說(shuō)法,三大悲劇詩(shī)人之一歐里彼得斯的悲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以歡樂(lè)為結(jié)局的。亞里士多德所喜愛(ài)的悲劇《伊菲革涅亞在陶里斯》結(jié)局也是歡快的。因此,悲劇與結(jié)局的不幸之間并沒(méi)有必然的一一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悲劇是對(duì)某一行動(dòng)的摹仿,“悲劇行動(dòng)涉及死亡,但不一定要以死亡告終,除非有某種情感結(jié)構(gòu)使然。”[7](P50)其二,她過(guò)于夸大社會(huì)上的法律條款對(duì)于悲劇情感表達(dá)的直接約束作用,僅僅依據(jù)大英帝國(guó)中心地區(qū)的局部事實(shí),推衍出了現(xiàn)代社會(huì)創(chuàng)作不出悲劇的武斷結(jié)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格羅斯曼承認(rèn)在她所處的時(shí)代,挪威、匈牙利、波蘭、俄國(guó)、南部非洲、澳大利亞等一些所謂文明程度相對(duì)較弱的國(guó)家和地區(qū),悲劇藝術(shù)依然比較繁榮。但是,在她眼里,這些國(guó)家和地區(qū)是邊緣地區(qū),是文明程度較弱蠻夷之地,即使取得的成就再高也不能代表悲劇藝術(shù)發(fā)展的主流趨向,真正代表這種主流趨向的是大英帝國(guó)這樣中心地區(qū)的悲劇藝術(shù)發(fā)展。格羅斯曼抱著大英帝國(guó)的心態(tài),其眼光無(wú)疑是極其傲慢的。也正是在這種大英帝國(guó)的優(yōu)越感支配下,格羅斯曼低估了挪威、瑞典、俄國(guó)等悲劇藝術(shù)的歷史成就。悲劇的歷史發(fā)展也證明,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挪威、瑞典、俄國(guó)等國(guó)家的悲劇藝術(shù)成就要比同時(shí)期的大英帝國(guó)成就高得多。格羅斯曼囿于帝國(guó)心態(tài),不顧文學(xué)的歷史事實(shí),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雖然她較早得出了“悲劇衰亡”的結(jié)論,但后來(lái)無(wú)論是在衰亡論者那里還是在質(zhì)疑者那里,幾乎沒(méi)有人提及她的真正原因了。
1927年,弗蘭克·勞倫斯·盧卡斯在《悲劇》一書中認(rèn)為,今天當(dāng)我們回顧過(guò)去,我們發(fā)現(xiàn)多少個(gè)世紀(jì)以來(lái),與大量涌現(xiàn)的杰出抒情詩(shī)和小說(shuō)相比,真正杰出的悲劇甚至所有種類的戲劇都顯得如此的稀少。悲劇的產(chǎn)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獨(dú)特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理想的觀眾、精湛的表演、優(yōu)秀的戲劇家及其廣泛的天賦。在談到悲劇的未來(lái)前景時(shí),他惋惜地說(shuō):“當(dāng)我們的社會(huì)依然如故,其前景看起來(lái)與其說(shuō)是燦爛的不如說(shuō)是有趣的。”[14](P156)他認(rèn)為,之所以現(xiàn)代小說(shuō)一直占據(jù)著長(zhǎng)期輝煌的統(tǒng)治地位,一個(gè)關(guān)鍵的原因在于小說(shuō)自身比較適合表達(dá)現(xiàn)代人的情感。盡管悲劇受到了小說(shuō)的嚴(yán)重?cái)D壓,但在盧卡斯看來(lái),悲劇仍然是必要的,“沒(méi)有什么能夠取代悲劇。如果說(shuō)它是一株幾乎不開花的植物,但是它的根扎得很深”。
不可否認(rèn),與格羅斯曼一樣,盧卡斯所認(rèn)為的,與悲劇相比現(xiàn)代小說(shuō)更適合表達(dá)現(xiàn)代人的內(nèi)在情感。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說(shuō):“悲劇由于長(zhǎng)度有限、情趣集中、人物理想化,已經(jīng)不能滿足現(xiàn)代人的要求。對(duì)于現(xiàn)代知識(shí)界讀者,長(zhǎng)篇小說(shuō)可以比悲劇更細(xì)致入微地描寫各種復(fù)雜變幻的感情。對(duì)一般人來(lái)說(shuō),高度理想化的悲劇不能滿足他們對(duì)強(qiáng)烈刺激的渴望;他們離開劇院,寧愿去看電影。曾經(jīng)被埃斯庫(kù)羅斯、索福克洛斯、歐里彼得斯、莎士比亞等等偉大悲劇詩(shī)人高踞的寶座,現(xiàn)在一方面被陀思妥耶夫斯基、D·H·勞倫斯、普魯斯特這樣的小說(shuō)家們占據(jù)著,另一方面被卓別林、雪瓦利埃(Chevalier)等人占據(jù)著。”[15](P21)但就總體而言,盧卡斯的悲劇觀還是比較保守的。他所謂的悲劇實(shí)際上是基于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的,正是在這種理解的基礎(chǔ)上,他認(rèn)為悲劇“是一株幾乎不開花的植物”似乎也沒(méi)有什么太大的問(wèn)題,因?yàn)椤皻v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guò)古希臘悲劇的再造,也沒(méi)有嚴(yán)格意義上的復(fù)制。這一現(xiàn)象并不奇怪,因?yàn)楣畔ED悲劇的獨(dú)特性是真正的,它在許多重要方面是不可移植的。”[7](P8)
他的問(wèn)題在于過(guò)于狹隘的理解悲劇,將古代的標(biāo)準(zhǔn)作為唯一的尺度來(lái)衡量一切,把后來(lái)的許多悲劇甚至是伊麗莎白時(shí)代的悲劇都統(tǒng)統(tǒng)排斥在悲劇的家族之外,以致妄自菲薄,對(duì)悲劇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現(xiàn)狀過(guò)于悲觀。盡管他在行文中沒(méi)有直接運(yùn)用“衰亡”、“死亡”之類的字眼,但在字里行間,他的“悲劇衰亡”調(diào)子還是極其明顯的。盧卡斯的觀點(diǎn)在學(xué)術(shù)界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悲劇》一書也于1962年由紐約的Collier Books再版。特別是他將悲劇比作“一株幾乎不開花的植物”的說(shuō)法時(shí)常被人提及,如1955年,加繆在《雅典講座:關(guān)于悲劇的未來(lái)》中說(shuō),“悲劇,畢竟是一株珍奇的鮮花,能在我們時(shí)代看到它盛開的機(jī)會(huì),也是微乎其微的。”1983年英國(guó)批評(píng)家海倫·加德納在《宗教與文學(xué)》中也有類似的提法,認(rèn)為“悲劇是一種極為罕見(jiàn)的植物”。
1929年,約瑟夫·伍德·克魯契在《現(xiàn)代傾向》第五章“悲劇謬誤”中說(shuō):“在現(xiàn)代和古代世界里,悲劇的死亡早于作家意識(shí)到這個(gè)事實(shí)。”[16](P136)將現(xiàn)代的文學(xué)作品稱為悲劇是用詞不當(dāng),因?yàn)樗鼈兣c古典的類型沒(méi)有相同之處,而且讀起來(lái)使人沮喪。克魯契指出,“我們閱讀但是不能寫悲劇”,其原因主要有兩個(gè):一是現(xiàn)代人缺乏必要的高貴的觀念。盡管我們可以部分地想象高貴的觀念,但是卻也無(wú)法理解它,因?yàn)槲覀儾皇巧钤诒瘎∷憩F(xiàn)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另一個(gè)異質(zhì)世界里。二是現(xiàn)代人誤解了悲劇的本質(zhì)。他認(rèn)為,悲劇本質(zhì)上不是絕望的表現(xiàn),而是戰(zhàn)勝絕望的表現(xiàn),通過(guò)戰(zhàn)勝絕望,確證了人生的價(jià)值。因此,在真正的悲劇中,災(zāi)難對(duì)于結(jié)局來(lái)說(shuō)僅僅只是一種手段而已,它實(shí)際上是對(duì)生活信仰的確認(rèn)。但是,現(xiàn)代所謂的“悲劇”作品只是一味地沉湎于悲傷,它的失誤在于將悲劇錯(cuò)誤地理解為令人沮喪與抑壓,將其與悲慘的、感傷的混為一談。克魯契比較了《哈姆萊特》與《群鬼》,他認(rèn)為:“莎士比亞證明了上帝對(duì)于人類的正當(dāng)性,但在易卜生那里沒(méi)有幸福的結(jié)局,他所謂的悲劇僅僅成為了在發(fā)現(xiàn)正義不再可能時(shí)我們絕望的表達(dá)。”[16](P132)因此,《群鬼》不僅是失敗的言說(shuō),而且是瑣碎和毫無(wú)意義的,因?yàn)樵谟^看時(shí),我們無(wú)法從中推斷出什么,也無(wú)法獲得凈化與和解。
克魯契的悲劇趣味是相當(dāng)古典的,以致完全否定了現(xiàn)代悲劇。針對(duì)他對(duì)悲劇狹隘凝固地理解,1932年,馬卡姆·哈里斯在《悲劇問(wèn)題》中主張悲劇理解的相對(duì)性,后來(lái)理查德·H·帕爾默將其對(duì)于悲劇的這種理解概括為“社會(huì)相對(duì)主義”(social relativism)。馬卡姆·哈里斯研究發(fā)現(xiàn),以前人們對(duì)悲劇的解釋主要依賴于三種系統(tǒng)價(jià)值,即“超自然主義”(SuPernaturalism)、“人文主義”(Humanism)和“自然主義”(Naturalism),與之對(duì)應(yīng),每一種對(duì)悲劇的理解都擔(dān)負(fù)不同的價(jià)值觀念:超自然的和解、人類精神的確認(rèn)、人們改變世界的愿望。由于先入之見(jiàn)的價(jià)值觀念不同,觀眾對(duì)于悲劇的理解存在著較大差異,導(dǎo)致彼此理解之間無(wú)法通約。于是,哈里斯試圖尋找一種悲劇的普遍定義,使得該定義能夠消弭由于價(jià)值觀念的不同而導(dǎo)致人們?cè)诒瘎±斫馍系母糸u。他所謂的普遍悲劇定義是:“悲劇是個(gè)人和集體價(jià)值的形象表現(xiàn),這些價(jià)值在悲劇行動(dòng)中潛在地或?qū)嶋H地出于危機(jī)之中;而同時(shí),由于觀眾忠于這些與之密切相關(guān)的價(jià)值,它們的危機(jī)喚醒了觀眾的反應(yīng),與之相稱的積極反應(yīng),但是這些價(jià)值的內(nèi)容隨著時(shí)代和個(gè)人存在著極大的差異。”[17](P182)不過(guò),在伊格爾頓看來(lái),哈里斯的嘗試似乎沒(méi)有達(dá)到預(yù)期的目的,并不算成功,甚至還顯得有點(diǎn)笨拙。
克魯契“眾所周知的文章”(well-known essay)“悲劇謬誤”在西方學(xué)術(shù)界影響很大,被收入多個(gè)悲劇理論讀本之中。他的觀點(diǎn)得到了不少人的響應(yīng)。例如,正如他認(rèn)為易卜生的《群鬼》不是悲劇一樣,約翰·D·赫里爾在他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指出,易卜生的《羅斯馬莊》也不是悲劇,他說(shuō):“在《羅斯馬莊》里,他給我們展現(xiàn)的不是悲劇性的死亡,而是用最近一本書的標(biāo)題來(lái)說(shuō),現(xiàn)代世界里悲劇之死亡。”[18](P124)洛厄爾·A·費(fèi)埃提指出,克魯契的觀點(diǎn)不僅影響了20世紀(jì)60年代幾部杰出的“悲劇衰亡”論著作,如喬治·斯坦納著名的《悲劇之死》,而且還影響了80年代的萊昂內(nèi)爾·艾貝爾盡管如此,克魯契的觀點(diǎn)還是遭到了肯尼斯·伯克、 羅伯特·W·里甘、艾德爾·奧爾森、雷蒙·威廉斯以及作家阿瑟·米勒等人一致地質(zhì)疑與反對(duì)。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數(shù)學(xué)者在批駁克魯契的觀點(diǎn)時(shí),似乎忽視了他的觀點(diǎn)背后隱藏著多個(gè)思想維度。也就是說(shuō),克魯契通過(guò)對(duì)悲劇的論述,夾雜著他對(duì)于現(xiàn)代社會(huì)諸多問(wèn)題的深層次思考。正如后來(lái)洛厄爾·A·費(fèi)埃提所認(rèn)為的,從歷史的角度來(lái)看,《悲劇謬誤》具有“幾種重要功能”,但是批評(píng)者們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致在相當(dāng)程度上誤解了克魯契。[19](P71)可以這樣認(rèn)為,也正是這些功能的多重疊合,造就了《悲劇謬誤》具有多維度的價(jià)值,使它區(qū)別于大多數(shù)“悲劇衰亡”論者就事論事單一維度的著述,獲得了較長(zhǎng)的學(xué)術(shù)生命力。
綜上所述,完全可以持之有據(jù)地表明:“悲劇衰亡”話語(yǔ)興起于20世紀(jì)早期,甚至可能會(huì)更早,但絕不是通常所認(rèn)為的30年代或是二戰(zhàn)之后。它的產(chǎn)生有其特定的機(jī)緣,除了與悲劇藝術(shù)自身的現(xiàn)狀有關(guān)之外,還與悲劇理論話語(yǔ)以及審美現(xiàn)代性有著深層次的邏輯牽連。因而在本質(zhì)上來(lái)講,“悲劇衰亡”話語(yǔ)有其自身的復(fù)雜性,這就需要研究者客觀冷靜地思索,認(rèn)真地檢視,才能減少認(rèn)識(shí)上的謬誤,避免步入誤區(qū)。
[1]《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大美百科全書(第27卷)[Z].北京、臺(tái)北:外文出版社、光復(fù)書局,1994.
[2]Howard Brenton.Freedom in chaos[N].The Guardian,21 September 2002.
[3]Walter Kaufmann.Tragedy and Philosophy [M].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4]George Steiner.The Death of Tragedy[M].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1996.
[5]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xué)論文選[M].繆靈珠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9.
[6]瓦爾特·本雅明.德國(guó)悲劇的起源[M].陳永國(guó)譯.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1.
[7]雷蒙·威廉斯.現(xiàn)代悲劇[M].丁爾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8]任生名.西方現(xiàn)代悲劇論稿[M].上海:上海外語(yǔ)教育出版社,1998.
[9]JR.George Yost.A Modern Version of Aristotle’s Poetics [J].Classical Weekly,Vol.37,No.13,1943.
[10]蘇珊·桑塔格.反對(duì)闡釋[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11]陳瘦竹.悲劇從何處來(lái)——50至80年代英美悲劇觀念述評(píng)[A].朱棟霖,周安華.陳瘦竹戲劇論集(上卷)[C].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12]陳世雄.悲劇衰亡之謎[J].戲劇,1996,(3).
[13]Edith Searle Grossmann.The Decadence of Tragedy [J].ContemPorary Review,89,1906.
[14]F.L.LUCAS.Tragedy [M].London: Leonard & Virginia Woolf Press,1927.
[15]朱光潛.悲劇心理學(xué)[M].張隆溪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
[16]JosePh Wood Kruttch.The Modern TemPer [M].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9.
[17]Markham Harris.The Case for Tragedy [M].New York,London,G.P.,1932.
[18]John D.Hurrell.Dilemma of Modern Tragedy [J].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1963.
[19]Lowell A.Fiet.“The Tragic Fallacy” Revisited [J].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Vol.10,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