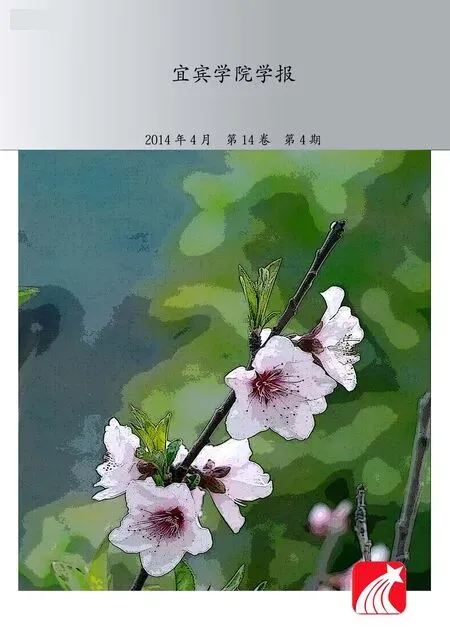新聞報道中情態的人際意義
——以順應論為視角
孫啟耀,樊紅梅
(哈爾濱工程大學 外語系,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關于新聞報道中的情態,很多學者作了相關研究。如高明強(2004年)認為,情態隱喻可以體現語篇中復雜的語義內涵,社會認知因素對情態隱喻的建構具有重要作用,新聞報道體裁的特殊性使其情態隱喻的體現系統更為復雜。李曙光(2006年)指出,情態是實現新聞語篇對話性的重要資源。朱惠華(2010年)從情態角度對《中國日報》和《紐約時報》中的新聞評論語篇進行量化分析,發現二者均采用情態動詞及情態附加語,隱性地表達意見,對所表達的意見該負的責任比較謹慎,由情態折射出語篇的人際意義。關于情態的順應性,僅有少數學者進行了探討。如湯敬安(2008年)對情態動詞語義的語用蘊涵、語境順應性和情態動詞間接言語行為和情態動詞隱含的言語行為類別進行分析,闡明了情態動詞的語用實質和語用綜觀性。宋改榮和孫淑芹(2013年)分析了情態動詞在科技論文英文摘要中的使用傾向,揭示了情態動詞的使用在促使學術語言的表達更含蓄、委婉的情形下,是作者運用適度推測、緩和語氣滿足科技語篇客觀性、準確性的要求,最終達到與讀者互動的語用目的。而關于新聞報道中情態的順應性研究還鮮有出現。
一 相關理論
(一)情態。情態(modality)最初作為一種對現實性、必須性和可能性的判斷被語言學借用。語言學家從傳統語法、語義學、轉換生成語法、符號學、語用學、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多個角度對情態進行了研究,使情態的概念界定、語義劃分、語用價值和運作機制越來越清晰全面。在萊昂斯看來,情態表達了說話人對語句或語句描述情景的看法和態度,情態不僅局限于情態動詞,像詞語frankly、fortunately、possibly、wisely 等都具有情態意義,情態的理解與語言的主觀性關系重大。[1]類似的,帕爾默認為情態是說話人主觀態度和看法的語法化。[2]16語用學從含義和預設的角度對情態進行了闡釋,并提到了級差(scale)的概念,認為在級差階上位置較低的成為較高位置的含義子項,或是從高的項可以推出較低的子項。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情態是人際功能的重要部分,表示語言使用者本人對事物認識的估量和不確定性。[3]24韓禮德認為,情態與歸一度有關,它表示介于“是”與“否”之間的不確定概念,根據其不確定程度的高低,韓禮德賦予其“高”、“中”、“低”三種不同的量值(value),并將情態劃分為情態(modality)和意態(modulation)。情態意義的表達還可以通過情態隱喻實現。根據語言使用者交換的是信息還是物品或服務,前者可以細分為概率和頻率,后者可以細分為義務和意愿。這與普通語義學將情態劃分為認識情態(epistemic)和道義情態(deontic)異曲同工。認知語言學認為,情態是真實世界領域對理性世界領域和言語行為領域的投射,當外部的演變沖力(volutionary momentum)足夠大的時候,那些可能性很大的“潛在現實”就被投射出來,形成“投射現實”。
(二)順應理論。 比利時國際語用學學會秘書長維索爾倫(Verschueren)在《語用學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2000年)中提出,語用學是對語言的一種綜觀(a perspective on language)觀點,并提出順應論(theory of adaptation),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對語用學進行了詮釋。順應理論的核心概念是順應(adaptation)和順應性(adaptability)。語言順應論強調語言“必須始終不斷地順應不同的交際意圖和使用環境”[4]39-50,其核心概念包括語言的變異性(variability)、商討性(negotiability)和順應性(adaptability)。變異性指語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商討性指語言選擇不是機械地嚴格按照規則,或固定地按照形式—功能關系作出,而是在高度靈活的語用原則和語用策略的基礎上來完成;順應性是指語言使用者能從可供選擇的不同語言項目中作出靈活的選擇,從而盡量滿足交際的需要。此外,對語言的順應還需要考慮四個方面的分析維度,即語境關系(contextual correlates)、語言結構(structural objects)、動態過程(dynamics)和意識程度(salience)。語境包括交際語境和語言語境,前者包括交際雙方、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后者包括篇內銜接(cohesion)、篇際制約(intertextuality)和線性序列(sequencing)。語言結構的順應指從語言選擇、語碼、語體、話語構建成分等多方面對語言進行選擇。動態順應指“語言過程在時間維度上發生、展開、結束”。[4]39-50意識程度指在不同的社會和心理認知因素的影響下,語言的選擇與信息傳遞的實際效果密切相關,語言使用者的意識程度越低,信息的理解就越困難。
二 新聞報道中情態的順應性分析
(一)新聞報道中情態的語用特征
1.事件真相的模糊性
由于其本身的“不確定性”本質,在對事件的真實性具有嚴格要求的新聞報道中,情態的使用不可避免地為其披上了一層“朦朧的面紗”。
(1)President Barack Obama later confirmed the death of Bin Laden, but did not directly mention the involvement of Navy SEALs, saying only that a “small team” of Americans undertook the operation to bring down Bin Laden.
例(1)中not directly和only均為具有情態意義的副詞,反映了奧巴馬不愿透漏本次突擊行動的細節,但又不能完全回避,故采用迂回戰術,委婉地作出回應。通過only這一排他性很強的頻度副詞,反映了奧巴馬謹小慎微的行事作風。a “small team”中低量值small一詞的使用與本次突擊行動的影響之“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盡管如此,不論媒體還是普通民眾,誰也不會小覷這一“小”分隊。通過Americans這一極度泛化的人稱指示語的使用,一方面暗示了此次行動是代表美國人民利益的正義的愛國主義行為,另一方面也較好地將這一小分隊的實際身份掩飾了起來。以上情態詞的使用,使整個事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讓人難免對這一小分隊的人員組成、作戰能力和突擊經過產生極大的好奇心,既完成了新聞事實的報道,又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引導讀者繼續了解更多的細節報道。
2.責任歸屬的商討性
例(1)中,a “small team” of Americans 的使用巧妙地將本次突擊行動的責任轉移到美國民眾身上。雖然美國政府一直以來都將本拉登定性為全球恐怖主義的罪魁禍首,對此,別的國家也鮮有異見,但畢竟這種世界警察似的“專制”行為在道義上多少有點站不住腳。因此,奧巴馬代表美國政府宣布此次突擊行動,肯定不能以個人名義享受本次成功消滅恐怖大亨的“功勞”,也不能以政府的名義這樣做。Americans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稱指示語。將本次突擊行動的責任歸于美國人民,暗示了本次行動是順應民意、民心所向的。用“small team”修飾Americans,既從側面肯定了美國軍隊的超強戰斗力,又考慮到本次突擊行動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如其他國家的道德譴責、反美勢力的武裝襲擊等),萬一矛盾沖突激化到難以化解的程度,可以將這一責任推卸到這一小部分“缺乏大局意識的普通民眾”身上而不是由美國政府來承擔。而對于親美勢力而言,這一突擊行動的功勞無疑要歸于美國政府,因為同樣作為統治者,他們不會將自己的既得利益拱手相讓。因此,這一富含情態意義的詞組的使用,既有利于美國軍事機密的嚴密保守,也有利于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游刃有余,時刻占有發言先機。
3.情態的順應性模式
語言的順應性涉及到語境因素、結構對象、動態過程和意識程度四個方面,下面就以摘自TheWashingtonPost的題為WhatwereallyneedtofearaboutChina的一段評論為例,對其中涉及到的情態進行順應性分析。
(2)China’s real advantage lies in its next generation — the students who graduate from its top colleges and become entrepreneurs. These kids are very similar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 They are smart, motivated, and ambitious. Whereas the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who now work in government research labs and lead the State enterprises that dominate industry learned not to challenge authority and to play strictly by government rules, the new generation knows no bounds. They are not even aware of the atrocities of the previous era. They don’t hesitat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to take risks, or to have ambition. Unlike their parents, this new generation can innovate.
(二)語言選擇的現實基礎:語境因素
whatwereallyneedtofearaboutchina的評論發表于2011年9月27日,作者為Vivek Wadhwa,是哈佛大學勞動與職業項目的高級研究助理,他幫助學生如何適應現實世界,進行課堂講座,領導完成了很多具有突破性意義的研究項目。基于語言使用者的現實背景,他本人對中西方青年一代都較為了解。當美國決策者對中國研究人員發表的學術論文和申請的專利數量大幅增加感到擔心的時候,Vivek Wadhwa卻不以為然。在他看來,“中國的學術論文多是無關痛癢或剽竊之作。它們除了提升國家自豪感之外并無裨益。國家資助的研究所基本上沒有出現任何創新。同時,中國的專利數量并非創新的指標,只不過是為了向到中國的外國公司課稅的收費站而已。”基于此種社會因素,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例(2)中,作者使用了對比的手法對自己的觀點進行闡釋。將中西方青年學生對比時,用了similar一詞,后用smart、 motivatedand ambitious修飾。作者一方面對自己國家的青年學生具有的優秀品質表示了肯定和贊揚,另一方面雖然很欣賞中國新一代青年學生的這一品質,但只是similar而非same,因此作者進行了第二項對比分析:中國青年一代與文革一代。whereas這一轉折詞的使用,為讀者設置了一個明顯的情感逆轉信號。用the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指稱文革一代,用atrocities指稱文革,children結合后面的learn和play的使用,暗示了作者對這代人的成熟度的質疑和對文革對當代人的影響之深遠的肯定;atrocities 明確了作者對文革的否定態度。正是由于中國新一代青年人能夠打破傳統的枷鎖(box)束縛,才能擁有與西方青年人相似的品質。相似而非相同,與中西方歷史發展、文化價值觀、國家體制、教育制度等社會因素的差異是緊密相連的。
由上可知,受語言使用者本人的社會地位和知識文化背景的影響,對存在于物理世界中的人和事,語言使用者就會作出符合自己知識水平的評論高度和深度,表現出符合自己文化背景的心理認知和態度傾向,從而通過具體的語言形式將這一態度傾向和情感認知呈現出來,這一過程即為語言使用者在進行語言選擇時對語境的順應過程。
(三)語言選擇的順應層次:對象凸顯
語言結構對象的順應性可以發生在語言的各個層次,不同選擇表現出的意識程度是不同的。
例(2)屬于新聞評論,帶有較強的主觀色彩,其正式程度較政治、經濟類報道略低。但是,相同場合下話題的選擇也會影響語體的選擇。例(2)是對中西方文化的評論,作者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力,而且其中牽涉到對中國人而言較為敏感的歷史事件和當代政府官員的評論,這一言語事件就決定了其語體選擇的正式性。另外,該評論屬于獨白類語篇,這決定了其論述觀點的鮮明性和論據的充分性,在語篇宏觀布局上必須嚴謹,如選段中通過兩項對比論證了中國新一代青年人的積極進取和勃勃生機。在句法和詞匯層面,例(2)使用了一般現在時態,反映了對現實的客觀描述和立足現在對歷史的總結與評介;對具有鮮明情態意義的指稱名詞(如kids、children、atrocities等)、情態形容詞(如next、top、new等)和副詞(如strictly、even等)、轉折連詞(如whereas)等的使用,表達了作者鮮明的現實判斷和情感傾向。
例(2)中,作者在作不同的語言選擇時其意識的凸顯程度還是有所區別的。由于作者與中國當代青年人接觸較多,因此當作者對其進行評論時,處于一種積極贊揚的較為平靜愉悅的心理狀態,其褒獎之詞便自然而然地脫口而出,意識程度較低。當談到中國的文革一代時,作者一面要努力回顧當年的歷史,一面要根據歷史作出相應的評論。尤其是那段歷史對知識分子造成的負面影響,作者不免義憤填膺,這種心理認知反映到語言選擇上,就有了具有強調作用大寫的Cultural Revolution和具有鮮明否定色彩的atrocities的使用。其意識程度相對較高。
(四)語言選擇的變化維度:動態過程
動態過程的順應性與時間具有密切聯系,由于語言使用者對信息的處理能力受記憶力的限制,所以為了突出語言的核心概念或思想,語言使用者通常選擇將最重要的信息內容盡量前置。這一方面通過設置中心句避免了“跑題”現象的出現,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了讀者的心理認知的時間動態性(即常說的“先入為主”),讓讀者在無其他“雜念”的影響下“純粹”地接受作者的觀點。例(2)中,作者想要強調中國新一代青年人的優秀品質,就把這一信息內容放在了段首。
動態過程的順應性也與語言結構緊密相連。語言結構本身的線性特征,雖然并不能決定語言的最終表現形式,但語言使用者可以通過對語言結構的安排和調整來達到特定的交際目的。
a.Unlike their parents, this new generation can innovate.
b.This new generation can innovate, unlike their parents.
(2)a、(2)b在語義上沒有任何區別,但其語用效果差別很大。人們接受語言的過程就是接受和理解信息的過程,因此語言的線性特征決定了信息理解的順應層次。(2)a中,首先是對文革一代的否定,然后指出新一代青年的創新精神。從歷時角度來看,這符合人們以史為鑒、吐故納新、不斷超越的歷史發展規律,給人一種社會日益發展、欣欣向榮的催人振奮之感。(2)b中,先褒后貶,首先將核心思想呈現出來,雖然簡潔明了,但這與全段的先貶后褒的對比手法的序列安排不協調,將unlike their parents放在句末,有“畫蛇添足”之感。
三 新聞報道中情態的人際功能
(一)尋求報道中的主客觀平衡。多里斯·格拉博爾認為,新聞所包含的信息更多是適時的,經常是煽動的和人們所熟悉的。信息中的傾向性掩蓋了日常事件發生的真實背景,從而使新聞無法為公眾提供指南[5]51。但是,“新聞的客觀真實性要求決定了新聞敘述者在敘事中著力規避自我,不發表評論,以營造客觀記錄事件的假象,營造新聞的客觀真實感”。因此,為了尋求新聞報道中主觀傾向性與客觀真實性的平衡,新聞報道者不得不采用一定的語用策略,情態的使用即為其中之一。例如,認知情態中通過對頻率副詞occasionally、sometimes、often、always等和概率副詞possibly、probably、surly等的使用,責任情態中通過對意愿副詞willingly、reluctantly、barely等和義務副詞should、 shall等的使用,都在“是”與“否”之間的“灰色地帶”找到了棲息之地。
(二)建構語篇層面的多聲協商。李戰子從多聲(heteroglossic)角度把言語看成是“必然引起承認、回應、期待、修正或挑戰一系列或多或少不同的立場或觀點”。[6]因此,包含有情態動詞、情態副詞等具有情態意義的表達就是由于語言使用者“對事物或觀點的不確信或者故意避免一種絕對表達”[7]61構建了具有多聲協商功能的話語空間。Hoey (2001)認為,任何一個語篇都是對話性的,都可以看成是問題與回答的模式。因此,新聞報道中的情態可以理解為作者與潛在讀者之間對話的一種語用策略。在這一過程中,作者力圖用較為客觀的表述論述自己的觀點,并時刻刺探著讀者可能產生的積極或者消極的回應,并實時對自己的語言選擇進行調整和商討,以贏得讀者最大程度的共鳴與認可和最小程度的反對與挑戰,實現語言選擇的順應。
(三)順應文化規約的心理認知。新聞報道作為較為正式的書面語篇,無法脫離其所處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和制約。這一點在西方媒體的涉華報道中可以找到依據。例如,“3·14”拉薩打砸搶燒事件被稱為“西藏起義”,否定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稱中國“入侵”( invade)西藏,中國軍隊“鎮壓”(crackdown)、“控制”(control)、“恐嚇”(terrorize),西藏人民“反抗”(protest)等。[8]西方媒體對中國形象的惡意塑造,一方面,受其全球化戰略利益的驅使——近年來中國的日漸強大讓他們感到了恐慌與不安,于是“中國威脅論”在西方流行;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經歷了“天朝上國”到“山河破碎”的歷史轉變,給不少西方“文化精英”留下了中華民族“懦弱”、“野蠻”、“殘忍”的負面印象,因此這一舉動也具有鮮明的文化意識形態根源。中國的媒體在涉外報道中也很難做到絕對的客觀、公正,如天災、槍殺、暴亂、搶劫之類的涉外報道在中央新聞聯播中并不少見,這也與中華民族特有的“自我保護主義”文化息息相關。
結語
新聞報道中情態的選擇過程與語言順應理論的選擇、商討并順應的過程相符,其目的是為了滿足主觀報道中的客觀性要求、構建可供多聲協商的話語空間和順應文化意識形態的心理認知。此外,對情態的順應性探討還不夠深入,新聞報道中不同情態類型的選擇又有什么不同?它們又是以怎樣的模式在語言使用者的心理認知和社會大腦中進行選擇的?不同類型的語篇對情態的選擇依據是什么?是否仍然可以用順應理論來解釋?以上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萊昂斯.語義學引論:第2卷[M].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
[2] 帕爾默.語氣與情態[M].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6.
[3] 韓禮德.功能語法導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4] 張艷君,毛延生.語言變異的語用順應論研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5] 班納特.新聞:政治的幻覺[M].楊曉紅,王家全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
[6] 李戰子.學術話語中認知型情態的多重人際意義[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5):353-358.
[7] 劉立華.評價理論研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
[8] 劉瑞生.涉藏報道與美國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6):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