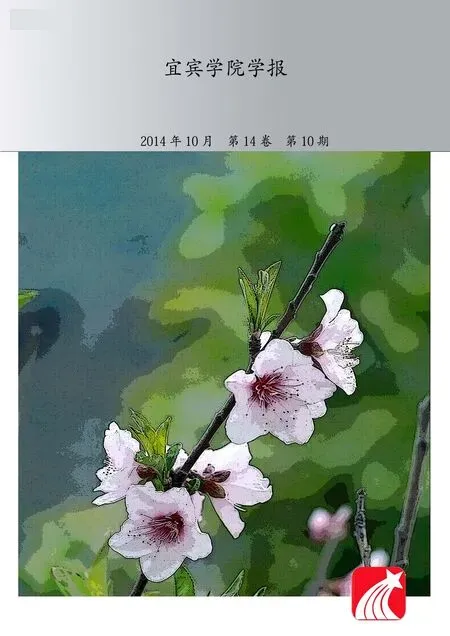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考論
楊小平,唐樹梅
(西華師范大學 a.文學院;b.外國語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9)
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與舊詞舊語相對,是按照出現時間進行劃分的,新是強調1912年以前沒有出現。實際上,民眾往往根據感覺判斷新詞新語,并不會檢索詞語的文獻用例,再嚴格根據文獻用例來判斷是否屬于新詞新語,新僅僅是人們對詞語的感受和感覺。個別新詞新語并不嚴格是語言學和文獻學的新詞新語,出現時間太早,以致人們不知道該詞語,而被感覺認為是新詞新語,有學者稱之為潛顯詞語。
漢語詞語研究往往重兩頭輕中間:重古代詞語,重當代詞語,輕現代詞語。呂叔湘1984年在《大家來關心新詞新義》上發文指出:“唯獨現代語詞,應該最受重視,可是最不受重視。”[1]現代詞與歷史詞相比,現代詞更重要。
哪些詞語屬于1912-1949年出現的新詞新語呢?怎么判斷1912-1949年新詞新語?如何結合文獻例證釋義?怎樣羅列新詞新語的文獻例證?這些新詞新語還有哪些是我們不太清楚的?本文擬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一 確定詞目
新詞新語詞目的確定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前人已經做了不少相關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們編輯了《百年漢語新詞新語大辭典》,其中1912-1949年卷收錄了3 000多條新詞新語。
那么。我們所收錄的這些詞語是不是就一定是1912-1949年的新詞新語呢?1912-1949年只有這些新詞新語嗎?我們的答案是無法肯定,這些詞語也不一定都是1912-1949年的新詞新語,1912-1949年也并不限于這些詞語。因為判斷新詞新語在1912-1949年產生的難度很大,1912年前的文獻我們并無法全部看到,也不可能全部檢索。不論是古代文獻,還是現當代文獻,即使利用了先進的計算機和網絡數據庫,也仍然無法窮盡所有的文獻。就現在的情況,甲骨文、金文、簡帛文獻、敦煌文獻、檔案文獻、地方縣志、新出土文獻等都無法進行檢索,其中可能就會有我們收錄的新詞新語。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會否定這些詞語作為1912-1949年的新詞新語的資格。我們只能夠無限接近新詞新語的出現時間并不斷提前,這也是《辭源》《漢語大詞典》出版后不斷發現例證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的詞目,國內目前就研究所涉范圍,沒有可供參考的詞目。河北大學楊霞博士論文《初期現代漢語新詞語研究——以〈東方雜志〉(1911-1921)為語料》以1911-1921年的《東方雜志》為語料,研究這段時期的新詞語,該博士論文根據《東方雜志》的語料(近3 000萬字的報刊語料),采用比對《漢語大詞典》收錄詞語的文獻例證(所選詞語均未見于《漢語大詞典》,或者是《漢語大詞典》收錄了,但只有詞條而無例證,或者例證滯后),還比對了兩部專門收錄近現代漢語新詞語的專著——《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和《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來判斷1912-1921年漢語新詞新語詞目,附錄《東方雜志》詞匯表,詞語數量達到11 951條(這個數字與我們推斷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總數在3萬左右基本吻合,因為十年1萬條左右,四十年左右應該是3萬到4萬條),每個詞條后面標明出現年份,似乎給我們列出了一個詳盡的詞目(這個詞目可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作為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的候選詞目)[2]。但該詞目中不少詞語并不可靠,難以斷定就是1912-1921年漢語的新詞新語,詞目中出現了不少地名(阿喀蘭疴馬州、安達斯山、奧大利)、人名(戴維各伯菲爾)等,也是不能夠作為1912-1921年漢語的新詞新語的。尤其是作者并未看到黃河清2010年出版的《近現代辭源》一書[3]。
(一)排除法
1.查閱工具書排除
判斷詞語為1912-1949年新詞新語可以分三步:第一步,以《現代漢語詞典》為基礎(因為該詞典收錄現代漢語的詞語,可以直接提供1912-1949年的漢語新詞新語參考詞目),提取了該詞典的全部詞目五萬多條,作為新詞新語的最初候選詞目;并翻閱《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現代漢語大詞典》《新名詞辭典》等類似的工具書,從中增補候選詞目。
第二步,以《辭源》《漢語大詞典》為否定詞條的基礎。如果該詞條出現了古代文獻例證,意思與現代漢語意思也一樣,就可以將其直接排除。因為《辭源》收詞截至于1840年,《辭源》收錄,就意味該詞語產生于1840年前。這樣,我們通過查閱,直接排除了三分之二的詞目,還剩下一萬多條詞語。
第三步,在《中文大辭典》《辭海》《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近現代辭源》中繼續查閱這些詞語,如果它們的文獻例證有出現在1912年前的,就加以淘汰。
2.查閱學術論著排除
學術論著也可以用于排除詞語,如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郭伏良《新中國成立以來漢語詞匯發展變化研究》等。這些論著明確研討的詞語中有不少不屬于1912-1949年的漢語新詞新語,而是1912年以前的或者是1949年以后的詞語。
3.查閱數據庫排除
將新詞新語候選的這些詞語放到四庫全書、四部叢刊、中國基本古籍庫、國學寶典、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漢籍檢索等古籍全文檢索數據庫中進行檢索。如果一個詞語在這些數據庫中能夠檢索到文獻例證,也可以將其排除。
這樣排除的結果,也僅僅只能說明這些詞語可能是1912年后出現的。還需要進一步進行選擇和淘汰。可繼續檢索《人民日報》(1946-2003)等圖文數據光盤,排除建國后出現的新詞新語,留下的方才可能是1912-1949年的新詞新語。這其中還要排除比較生僻的專業術語等。
(二)借鑒參考法
除了用排除法排除舊詞舊語,我們也借鑒參考工具書、學術論著和語料庫來確定新詞新語詞目。
1.借鑒參考工具書
工具書是研究判斷確定漢語新詞新語時的第一選擇,這種方法遠比閱讀文獻、依靠語感可靠得多。新詞新語條目的收錄不能僅憑借個人的語感,依靠人工,根據感覺進行收集。《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近現代辭源》等工具書收錄的詞語并不都是1912-1949年的漢語新詞新語,但其收錄的詞語為我們間接提供了1912-1949年的漢語新詞新語參考詞目,如這些工具書中文獻例證為1912年后的詞語,它們自然成為研究的參考詞目。我們對這些待選詞目也進行了判斷選擇。同時,《〈辭源〉續編》《辭海》《漢語大詞典》等工具書中文獻例證為1912年后的詞語,它們也能夠成為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的參考詞目。如《〈辭源〉續編》明確提及到的“第三國際”“不合作運動”等。
比較詞典不同版本的差異,也能夠幫助我們確定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的詞目。由于《辭源》合訂本的方便和修訂本的流行,老版《辭源》《〈辭源〉續編》的價值長期被忽視,比較《〈辭源〉續編》與《辭源》的差異部分,正好能夠發現1912-1949年漢語產生的新詞新語。老版《辭海》也存在類似情況。《現代漢語詞典》各版增刪并不為人注意,其實,刪除的舊詞舊語往往可能就是1912-1949年的新詞新語,反映詞語的顯現和隱退,值得調查研究。
新詞新語的確定以《漢語大詞典》紙質版、電子版和網絡版作為參考。《漢語大詞典》的附錄有音序索引,網絡版、電子版等電子檢索軟件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檢索詞語,比翻閱紙質版快得多,不過,紙質版更可靠,因為電子版與紙質版并不完全一樣。
2.借鑒參考學術論著
學術論著直接提供了1912-1949年的漢語新詞新語,為我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彭文祖《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由東京秀光社于1915年出版,當中收錄不少新詞,絕大多數專家學者無由得見,無從參考。該書提及“哀啼每吞書”“支那”“取締”“引渡”“第三者”“強制執行”“奸非罪”“文憑”“機關”等新詞新語[4]。
馮天瑜《新語探源》提及“漢字文化圈”“愛智之士”“宗教改萌”“元質”“水道”“靈糧”“圣覺”“政黨”“警察”“借用語”“勞動組合”“勞農政府”等[5];黃濤《流行語與社會時尚文化》在第一章《20世紀20-30年代流行語》中言及“那摩溫”“十三點”“黑漆板凳”“打無線電”“拆姘頭”“吊膀子”“釣蚌珠”“尖先生”“仙人跳”“花瓶”等[6];《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也涉及到“立場”“情報”“左翼”“干部”“重工業”“多數黨”“青年團”“兒童團”“邊區”“解放區”“蔣管區”“白區”“紅區”“紅軍”等[7]。類似的還有劉禾、方維規、陳力衛等對新詞探索的學術專著。
期刊論文在論述時會提及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有助于對新詞新語進行判讀,如崔軍民《中國近代法律新詞對古語詞的改造》、沈國威《漢語的近代新詞與中日詞匯交流》、楊端志《從清末民初科學小說新詞語看“現代性”新詞語的來源和發展》、楊霞《〈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若干條目釋源補正——以〈東方雜志〉(1904-1948)為語料來源》等。如楊端志提及“學界”“電鈴”“德律風管”“風扇”“社會腐敗”“咖館”等,同時他指出:“往往被認為是某個時代‘新詞語’的東西,一查書,早就有,甚至先秦就有。”又如楊霞提及“背景”“啟羅瓦特”“打字機”“風扇”“注射”等,沈國威言及“工事”“番號”等,崔軍民提及“緩刑”“假釋”“分權制衡”等。
學位論文雖然沒有直接以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為研究對象,但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部分1912-1949年漢語的新詞新語,可以從中進行提煉。其中,博士論文如崔軍民《萌芽期的現代法律新詞研究》、劉吉艷《漢語新詞語詞群現象研究》、劉曉梅《當代漢語新詞語研究》等。碩士論文如申雅輝《舊詞新義研究》、宋培杰《新時期舊詞新義研究》、李科《現代漢語新詞研究》等。
3.檢索參考數據庫
計算機數據庫的產生為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的判斷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人民日報》(1946-2003)、《東方雜志》(1912-1948)、《新青年》等語料庫,都幫助我們對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進行確定。
網絡數據庫和搜索引擎也為我們確定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提供了方便,網絡數據庫如大成老舊刊數據庫、翰堂典藏數據庫等,搜索引擎如讀秀、超星、萬方、中國知網、人民網、新華網、廈門網、新浪、搜狐、百度、谷歌、網易、搜狗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義新用特別難以判斷確定。例如“大革命”一詞本指大規模的革命,如俄羅斯十月革命、法國大革命等,特指1924年至1927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合作領導下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現代漢語詞典》收錄,解釋為“特指我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文獻用例有王任叔《非甲即乙》(1936年)、《學習》(1941年第3卷第11期)、李廣田《禮物》(1942年)、《新華周報》(1949年第2卷第1期)等。“大革命”一詞,《近現代辭源》未收。《漢語大詞典》例證孤引朱德《回憶我的母親》,朱德《回憶我的母親》一文原載1944年4月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原名《母親的回憶》,例證時間滯后。在語料庫中檢索“大革命”,往往可能會“大革命”三字連用進行檢索。如果直接使用檢索結果來簡單判斷詞語的使用頻率,就勢必會導致統計數據出現誤差,甚至與實際使用頻率情況背離。這也說明新義判斷特別容易誤解,這也可能是新義研究較少,滯后于新詞新語研究的因素之一。
二 釋義
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確定詞目后,如何準確釋義,就成為我們的首要任務。
(一)借鑒參考。釋義難,準確釋義更難。雖然有《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等權威工具書作參考,但并不意味我們可以直接照搬這些工具書的釋義,還必須結合文獻用例,歸納這些新詞新語的意義,按照統一的體例進行釋義,避免義例不符,自相矛盾。
(二)自編釋義。同時,還有不少1912-1949年新詞新語并未被《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等權威工具書收錄,沒有釋義,只有自己根據1912-1949年新詞新語的文獻用例來闡釋其意義。這些詞語的釋義并非易事。
最簡單的釋義方式就是找一個同義詞。用同義詞進行解釋,簡明清楚。同義詞最理想的就是等義詞,這種情況并不多,往往出現的是已經成為漢語新詞新語的外來詞、方言詞等的釋義。但更多的新詞新語無法找到合適的同義詞。針對這些新詞新語,釋義時,應盡可能地采用下定義的方式,用本質特征加中心語的格式解釋1912-1949年的新詞新語。而要找到詞語的本質特征并非易事,需要仔細玩味詞語的文獻用例,推敲其意義和用法,盡量避免以點帶面,或者以偏概全。除以上方法外,我們還使用由反知正、描寫、比較等訓詁學的傳統釋義方法。
三 收集文獻用例
研究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確定詞目后,搜集文獻例證就成為基礎工作,文獻例證的多少直接影響研究的質量。1912-1949年新詞新語的確定和釋義都必須依靠文獻用例,沒有文獻用例,容易讓人懷疑這些詞語并非1912-1949年新詞新語,釋義也無法讓人信服。新詞新語文獻用例為深入討論“文明戲”“白話文”“普通話”“紙老虎”等新詞新語提供了材料基礎。
1912-1949年新詞新語通過報刊、廣播、現代文學作品等傳播而普及,而1912-1949年漢語文獻資料浩瀚,報刊、現代文學作品等分布零散,受研究條件、個人學力的限制,全部搜集、逐一閱讀并不現實,存在疏漏自然難免,從中得出的結論可能有誤,始見文獻往往不明或亡佚,新詞新語的文獻用例根本無法收集。1912-1949年的漢語新詞新語文獻用例難以收集,出現有詞無例或者有詞證孤的情況。
(一)從字典辭書中收集文獻用例
《漢語大詞典》引有現代文學作品文獻用例,能夠提供部分詞語的文獻用例,但沒有明確寫明報刊、現代文學作品等文獻用例的時間。我們對報刊、現代文學作品等文獻進行查證,標注年份并核對原始文獻,再作為新詞新語的文獻用例進行收集。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近現代辭源》直接提供了1912-1949年漢語新詞新語的文獻例證,雖然并不一定是最早的文獻例證,但畢竟提供了文獻例證,可以直接引用或者作為參考。
(二)從論著中收集文獻用例
專著和論文會提及新詞新語的文獻用例,或者涉及新詞新語的相關線索。我們還檢索原始文獻,逐字核對。實在沒有原始文獻的情況下,我們才使用這些論著提及的文獻用例。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收詞5 000多條)[8]和《近現代辭源》(收詞9 500多條),1912年后引用文獻28種,可以從中收集新詞新語的文獻用例。類似的論著還有不少,前面已經提及的,如《流行語與社會時尚文化》《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等。
(三)從數據庫中收集文獻用例
計算機語料庫有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東方雜志》(1912-1948)等語料庫、《人民日報》(1946-2003)數據庫、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大成老舊刊數據庫、翰堂典藏數據庫,以及自建語料庫(1912-1949年的報刊、檔案、游記、日記、手稿、個人文集、文學作品等),可以用來收集新詞新語的文獻用例。
利用民國時期報刊全文檢索數據庫,檢索1912-1949年漢語已出現的字母詞“AB團”,僅僅需要幾秒就能夠查閱到《策進》(1928年第2卷第34期)、《文藝新聞》(1932年第44期)等文獻用例。但該數據庫還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命名能夠檢索,還不能夠復制,還需要檢索者自己打開原文,逐字輸入,同時,明明有這個詞語,卻無法檢索。
我們還可以利用百鏈、讀秀、萬方、中國知網,以及人民網、新華網、新浪、搜狐、百度、谷歌、網易、搜狗等搜索引擎,尋找新詞新語文獻用例的線索。但還有《新青年》《向導》等大量未能夠數字化的文獻,這些文獻不能夠利用數據庫進行檢索,需要人工翻閱。
四 羅列文獻用例
收集足夠的文獻用例后,需要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排列,以此為基礎,給新詞新語標注始見年份,并不斷根據收集到的文獻用例更新修改。這有助于復雜、繁難的考源。而選擇、編輯、羅列新詞新語的文獻用例,就成為十分重要的工作了。文獻用例收集完成后,選擇典型、規范的文獻用例作為新詞新語的書證,并按時間順序進行排列,時間早的排在前面,晚的排在后面。羅列文獻用例,實際上是為詞源考證奠定基礎,許多學者為一詞的溯源而上窮碧落下黃泉。新詞新語成千上萬,每個詞都需要窮其源流,追其本原,由于材料有限、時間有限等,只能憑收集文獻所及,把詞語在漢語文獻中的早期用例列舉出來。
羅列文獻用例時,需要給文獻定年。給文獻定年份有兩種方法:一是按文獻的寫作時間定,一是按文獻的刊行時間定,但有些文獻寫成后,并沒有馬上刊行,要在若干年以后才付印,中間相隔許多年。追憶性文獻(如回憶錄等)以發表時間或者寫作時間為準,不以回憶事情所在時間為準,即時性的文獻(如日記、游記之類)以寫作時間或發表時間為準。
參考文獻:
[1] 呂叔湘.大家來關心新詞新義[J].辭書研究,1984(1).
[2] 楊霞.初期現代漢語新詞語研究:以《東方雜志》(1911-1921)為語料[D].石家莊:河北大學,2011.
[3] 黃河清.近現代辭源[K].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4] 彭文祖.盲人瞎馬之新名詞[M].東京:秀光社,1915.
[5] 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M].北京:中華書局,2004.
[6] 黃濤.流行語與社會時尚文化[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7] 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化和發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8]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K].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